不愿意生了 中国的出生率已经跌过了日本

年轻人不愿意生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个数字跌破了警戒线1.5,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生育率的担忧。有声音认为,中国也跌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41,而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0),甚至比“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低。
不愿意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过渡到父母的身份。其背后的障碍,也许事关经济压力,也许出于个人价值判断,也许是一些更细碎的个人顾虑,听上去似乎无解。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吊诡现象。为什么社会经济越发展,育龄的年轻男女,越不愿意生养小孩了?站在人口转型的宏观角度,也许就能发现藏匿其中的惊人逻辑。
两种个案
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验孕棒上出现两条线,都很清晰,加之两个月不来的生理期,忐忑多日的念头得到了应验—“我怀孕了”。
尽管沈梦婷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但那一刻,一阵恐慌还是瞬间淹没了她。脑海浮现一些从未曾想过的画面:变形的身体、半夜哄睡婴儿的苦恼、与丈夫在育儿方面发生日复一日的争吵。还有最重要的,她也从未想过:她可以做出怎样的牺牲。

《坡道上的家》剧照
沈梦婷今年30岁,所谓的生育黄金年龄,“按理来说,我应该坦然甚至欣然面对。但恐慌是实实在在的。”
她在上海有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今年已经把朋友和同学的婚礼、满月酒参加个遍,每到这种场合里,人们会调转枪口,对她发出一句句灵魂拷问:“什么时候才轮到你?”还有贴心的忠告“再不要个小孩就晚了”。母亲见她如此“不思进取”,更是大骂不孝。
沈梦婷此前换过三任男友,都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婚姻因生活方式和三观的迥异,不了了之。现在,她要审视的是,肚子里的胚胎和眼前这个男人,值得吗?
男友思想简单,只道,“我喜欢孩子,生下来吧。”但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她在上海买不起房,孩子教育怎么办?每个月所剩无几的工资怎么养得好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如果去另一个城市,是否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她热爱(电视剧)的职业?
更重要的是,眼前这个人,能做好一个合格的父亲吗?是她理想的人生伴侣吗?这些都没有答案。

“我不想为了一枚胚胎将就自己的人生。”
一个星期后,她下定了堕胎的决心。
与沈梦婷不同,长沙的赵新竹作出了她最激烈的反抗。婆婆和母亲双管齐下,给她下最后通牒,她喊出了离婚予以还击。
今年春节期间,婆婆和母亲一如往常,开始试探赵新竹丈夫,问他喜欢不喜欢孩子。大年初二,俩亲家还去求了送子观音。

综艺《我家那闺女》中,几位父亲在女儿的下一代问题上一致表示:还是要结婚生孩子
大年初四,趁着一家人围桌聚餐,她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我今天就明说了,我是不会要小孩的,你们别费劲了。母亲骂她自私,从不为家庭考虑,并放了狠话,如果今年再不生,他们死了遗产一分钱不留给她。赵新竹无所畏惧,当场说出离婚来还击。
赵新竹31岁,丈夫32岁,两人是硕士研究生同学,毕业两年后才谈起了恋爱。4年前两人结婚时,他们就约定,不要小孩,一起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丈夫很快倒戈,他不能理解:“大家都生了小孩,你为什么不生。”最近,他又戒起了烟。
越是如此,她越抗拒。婚后她才发现,丈夫并不是那种能跟她感同身受的人,而且经常不着家。“如果生了小孩,我注定是孤军奋战。”

《我要准时下班》剧照
赵新竹恐惧分娩的痛苦,她自认为不是一个母爱泛滥的人,做不到一个贤妻良母的本分。她知道,人的心境可能会变,也许40岁她会想要一个小孩,但她眼下没法克服自己。在母亲看来,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简直有病”。
对沈梦婷和赵新竹来说,生育意味着什么,似乎并不为旁人所理解。而对生育率持续低迷甚至跌破警戒线的中国社会来说,作为个案的沈梦婷和赵新竹,似乎又成了一种综合样本。
那些抗拒生育的男男女女,他们真正恐慌的是什么?这需要被听见。
社会宿命
从任何层面来看,“不愿意生小孩”,都成了一种既定的现实,而且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趋势。
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这是中国生育率首次跌破1.5的警戒线。这一度引起学界和公众的担忧,中国是否落入了“低生育陷阱”?

历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及年均增长率(图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这并非一个新的现象。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走势持续下滑。直到2016年,二孩政策开放,效应是显著的,当年出生人口数猛然回升,为1786万人。
但二孩政策并没有带来长期效应,短暂的刺激后,从2018年开始,迅猛的下跌势态便出现了,出生人口和出生率一度跌破历史水平。最不容乐观的,便是2020年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综艺《奇葩说》中傅首尔提到自己的孩子破坏力惊人
要知道,低生育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至于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不可小觑的是,低生育率如今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应了那句话——“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超低生育率,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
需要阐述一个概念,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它反映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由于婴儿夭折、疾病等因素,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否则,后果便是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劳动力规模下降,总人口规模减少。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引起了人类对自身物种存亡的担忧。牛津大学人口学家曾对韩国做出预警:称其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国家”。2018年,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只有0.98,属全球最低,意味着平均每位育龄女性生了不到1个孩子。

中国、日本、韩国历年总和生育率(图源:快易财经网)
2018年,《柳叶刀》刊发一份研究报告称,全世界近半数国家现在都面临”婴儿荒”,没有足够的儿童人数来维持其人口规模。学界认为,这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很快将“过渡到各个社会努力应对人口下降产生问题的地步”。
不要小看了人口这件事,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驱动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房屋,交通,消费,经济。一个白发人远多于黑发人的社会,更是难以想象的。
只是大部分国家还没有正面迎接它的冲击。
静悄悄的革命
“不愿生”,是一个看似简单,又极其微妙、复杂的问题,它意味着青年男女过渡到父母身份的一切障碍。
不仅关乎社会经济,也受婚姻、家庭和社会文化的潜在影响,更直接关系到女性的生育环境是否友好。这种整体性的生育率趋势变化,被人口学理论称作人口转变。

焦俊艳与父母彻谈对于婚姻的看法
前现代社会的特征是高死亡率、高生育率。战争、疾病等因素带来的超高死亡率,如果不是高生育率填补空缺,人类的灭亡就成了必然。现代化过程消解了这种特征,伴随着弱家庭社会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城市工业社会带来了第一次人口转型,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低生育率、低死亡率。
人口学家乐观地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路径,等到生育率降到更低水平,社会的人口规模将会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
但到了1980年代,事实超出了研究者的认知,生育率不仅没有稳住,反而一跌再跌,有的国家甚至直线跌破1.5的敏感红线。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人口的第二次转变,以试图解释这种趋势的内在奥秘。
这一次,人口学家发现了全然不同的驱动力。
1977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提到,当社会变得富裕之后,人们的需求从生理和安全提升到自我实现层面。年轻一代对权威和传统的社会规则提出了挑战,性解放运动使得性行为不再局限在婚姻以内,婚前性行为得到了认可。
这种现象带来的变化是,教育普及和广泛的就业参与,带来了初婚年龄的推迟,以及结婚率的下降、同居率和离婚率的上升。所以,生育率持续降低,成了一种必然的结果。

《我家那闺女》蒋梦婕爸爸婚姻观:婚姻是一种选择,主要享受过程
人口学家谢宇在研究中表示:第一次人口转变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但眼下的转变,冲击甚至瓦解着传统的婚姻、家庭的制度构建和组织形式,家庭的古老功能,也得到了更新。
传统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的存在,是培养子女,使其向社会上层流动,以谋取家庭福利。但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里,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中心,某种程度上,自我实现凌驾于传宗接代,女性走出了私人空间,公共价值凌驾于私域价值。
总而言之,这种观念变化的背后,正如谢宇所言:“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性观念与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自我实现的重视。”这是一个喜闻乐见的趋势:女性开始掌握更多的自主生育权利。

综艺《我家那闺女》中,papi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独立女性的人生中自己是最重要的
那问题是否在于,性别平等带来了低生育率?女性觉醒是否跟母职天然冲突?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若真把生育率降低的因素,归结为女性教育的提升和就业参与,那就谬之千里了。
东亚顽疾
青年学者黄微子身为人母后,曾在《读书》撰文称:“嘲笑为生育付出大代价的失败母亲,主张‘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靠自己的’道德进步主义,跟那种歧视‘大龄剩女’、谴责不育女性的道德保守主义,至此殊途同归,造成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敌意和倾轧。”
我们很容易走进一个二元对立的死胡同。
一时间,我们似乎难以解释性别革命是否、以及如何阻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新世纪后,人口学家开始留意到就业参与和生育率之间的异常关联。研究者发现,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的关系,最初是负相关的,但是如今在一些欧洲国家中,这种关系发生了逆转。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人口转型的阶段性:事实上,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生育率降低,是这次人口转型的初始阶段。
在第二阶段里,男性开始回归私人空间,转变了家庭分工角色和定位,分摊更多家务和育儿。这才是一场完整的性别革命,也唯其如此,生育率才会出现随之上升。

贴吧上关于房贷压力而对婚姻产生的担忧和不安全感。来源/百度贴吧
如果说,早期的人口转型是经济发展所驱动的,那么如今人口转型的出路,恐怕集中于婚姻、家庭内部的性别文化的革命。
在北欧、法国、美国等国家,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带来了生育率和更替水平的平衡:女性承担了较少的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单从养育时间来看,女性之于男性的比例是低于2的,表明了男女家庭分工上也接近了平衡。
法国是这方面的楷模,半个世纪以来,该国始终维持着接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根据2005年一项统计,法国妈妈一胎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是84%,即便三胎妈妈,仍有63%会重回劳动市场。另一项数据更为关键。2016年,法国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其非婚子女比例高达60%,这些婴儿来自稳定的同居关系,且受法律保护。
高比例非婚生子的背后,是一个性别更开放的社会,社会规范没有对女性的生育和发展形成钳制,也无需花费生命中的更多时间来择偶(那会导致晚婚或者不婚,降低生育率),也无需在生育问题上手足无措。
而在更具有父权特征的国家,诸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生育率下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无法维持正常的人口更替。

各国自上世纪50年代末的总和生育率走势图(图源:快易财经网)
东亚社会有一些直观的例证。日本记者小林美希曾撰写一本探讨日本女性困境的著作《不让生育的社会》。书中,她跟踪采访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如何面对生育困境,让人们看到了被人忽略的日常现实—育儿的责任被强加于女性。
结婚变得困难。结了婚的,不想要小孩,要了小孩的,也有放弃养育的案例。近7成的女性在初次生育后面临失业。与此同时,社会托育制度也是一片空白。不是不能生育,是整个社会环境不让她们生育。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便开始了工业化,一百多年来,生育率下降比东亚邻国都早,进程也缓慢渐进。但充裕的时间并未带来足够的自我纠正机会,僵固的家庭制度和性别关系,注定使其落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韩国同样是一种典型:女性的薪资水平为男性的65%,很多女性而立之年便走进家庭,这种从公共空间回流的现象,并未带来生育率的提高,反而加速了其崩盘。

韩剧《今生是第一次》剧照
“全球老龄化学会” 的执行长理查德·杰克森(Richard Jackson)曾表示,1990年代之后,女性意识抬头,全职妈妈不再是主流价值,反倒是一个社会无法提供妇女得以兼顾工作与家庭的环境,势必会降低生育的意愿。所以,可以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性别观念越保守的文化,人们越不愿意生养孩子。
事关就业参与,又不完全如此。东亚诸国的顽疾在于,男男女女仍受传统婚姻家庭规范的束缚,女性择偶、生育变得更谨慎,以致婚育停滞,男性承担的家庭分工过于刻板僵固,从而造就了责任撕裂,阻滞了生育率。
低生育陷阱的出路,不仅在于如何完善社会制度,更在于社会文化的规范该如何变革,以回应观念的变迁、性别角色的新定位。




![[二手好物]轻奢带盖果盘小熊款](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a354d8e1-8ebf-4bd9-9ae1-7ea0ed5dd4f6.800x8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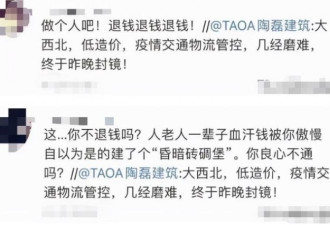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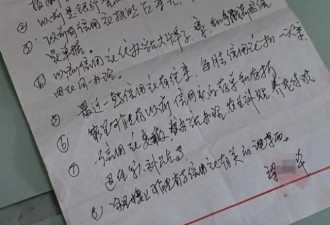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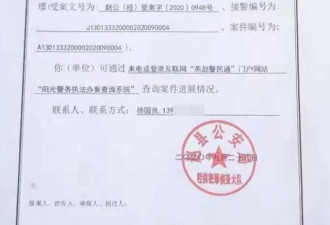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