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自述:在黎巴嫩难民营的一个月
五月中旬的一个正午,阳光晃眼。在贝鲁特城南夏蒂拉(Shatila)难民营的市集里,驾驶摩托的年轻小伙在人流里横冲直撞,我提心掉胆的往前走,额头上冒出层层密密的细汗。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垃圾场,突兀地伫立在卖假货的服装店和杂货铺之间。

一个面容削瘦黝黑的男人手里拿着鞭子,在垃圾场一侧等待,他等待的是正在腐烂酸臭的垃圾堆里缓慢翻找食物的奶牛和羊群。一只泛黄发黑的奶牛,眼睑泛红充血外翻出来,看不出颜色的乳头快要垂到地上。

贝鲁特城市街景
我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向和我一同注视着这一幕的叙利亚女孩儿 Esraa。
“这就是我不喜欢吃肉的原因,”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惊讶,她耸了耸肩,淡定地和我说。
Esraa 今年 14 岁,从小生活在这里,是我在这座难民营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此后好几周里,难民营成为我不断往返的地点之一。在共同未来项目的支持下,整个五月,我都在黎巴嫩贝鲁特城的夏蒂拉难民营与北部贝卡谷地的公益组织 Lighthouse Peace Initiative(LPI)进行采访与拍摄。
正式进入难民营以前,我花了两天时间才习惯这个国家在经济崩溃、港口大爆炸等一系列灾难事件发生后的混乱。全国四分之三的人陷入了贫困,黎巴嫩磅贬值超过90%,这不仅意味着大部分人放在银行的存款几乎蒸发,同时也导致了进口能源的短缺,许多家庭要支付昂贵的电费,每天还要经历好几次断电。
前往海岸风光线巴黎大道的路上,汽车经过了好几次由军队把守的岗哨,士兵手举长枪的枪托在阳光下异常耀眼。废旧的老车直接被扔在了道路两边,无人照管,堵车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随时发生。

坐在前往地中海沿岸巴黎大道的巴士上
但与此同时,黎巴嫩还是是如今世界上收容难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难民占据了超过全国 20% 的人口。我的第一站目的地是前往首都贝鲁特城南最大的夏蒂拉难民营。这座难民营始建于1949 年,最早是国际红十字会为巴勒斯坦难民在此搭建的“临时”居所,却一直延续至今。我好几次被熟悉当地情况的朋友告知:“女生最好不要单独前往。” 难民营坐落在贝鲁特的 Ghobeiri 街区,这里常被外国大使馆定义为是最不宜出行的危险区域,原因是“可能存在火箭弹和汽车炸弹的袭击”。
第一次拜访时,我尝试打车抵达。最终汽车却把我载到一座老远就能闻到恶臭味的垃圾场前方,拐了个弯后,司机拒绝我再继续往巷子深处难民营前行的请求。下车后,我顺着街道找到一条两米长的甬道。按照指引,通过这后我就算正式进入了夏蒂拉难民营。
入口甬道像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随意门,我惴惴不安地走了进去,甚至下意识握紧了手里的手机。走进甬道后却觉得这里的景象比我想象中“正常”不少,除了更为拥挤和嘈杂。最近十年间,受战争影响的叙利亚难民开始成倍增长,原本为 3000 多个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住所的夏蒂拉难民营里如今挤满了四万多人。

夏蒂拉难民营中骑摩托的小哥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悬在半空中,交织密布的电缆光纤。它们构成了一张张笼罩在头顶的天幕,有时就垂在距离人们半米高的头顶。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走在这些电缆下,一旦冬天下雨漏电,它们就能直接杀人。街道虽然狭窄,但两边的商店几乎能满足人们所有基本需求:咖啡、理发店、杂货铺甚至网络服务……只是垃圾堆和早餐店有时在不到五米的对角线上存在,让人瞬间丧失食欲。
绣娘们
经过热闹市集,拐进僻静小巷后是一个停车和堆积建筑废料的小广场。我要拜访的 Alsama 工作室就在这片空地上一栋七层楼高的破败建筑里,沿着楼梯走上四楼,原本单调的白墙上多了 Alsama 的标识和插画。六个叙利亚绣娘们正面对面坐在一间不到十平米房间的书桌前,认真地在手上一块巴掌大的白布上穿针引线,绣制手工书签和靠枕上的花纹,墙壁上的风扇机械声嗡嗡作响。

夏蒂拉难民营的中央市场
我用蹩脚的阿拉伯语大声和大家打招呼,见到什么都情绪饱满地夸 Halo(阿拉伯语:可爱、漂亮的意思)引得原本有些害羞的叙利亚女人们发出阵阵笑声。Jouhayna 是如今工作室的负责人,她起身从正中间的位置走过来,笑脸盈盈地出来迎接我们。
我和叙利亚女孩儿 Esraa 就是这么相识的。她当时正坐在绣娘中间,穿着一身深灰色长到小腿肚的运动长衫,头上包裹着黑色头巾,清秀的脸庞上冒着几颗青春期特有的小痘痘。她时不时抬头好奇的看看我,浓密的睫毛在大眼睛上扑闪。但外人的出现没有中断她手头的工作,直到我试图用英语试图询问她的情况,她才终于停下了手上的活。
“我七岁那年来到这里,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都结婚了。” Esraa 用清晰的英语回答我。
我宛如找到救星一般,请 Esraa 帮我翻译并夸她英语说得很好,她欣然答应,并且得意地把我对她的赞扬用阿拉伯语又给 Jouhayna 转述了一遍。此后,我来到工作室的交流大部分都通过 Esraa 完成,也多亏了她才稍稍缓解了一些我像咿呀学语的孩子一样,用仅知道的两个阿拉伯语词汇,手舞足蹈和大家对话的尴尬局面。
大概是为了熟络感情,绣娘们热情地向我介绍 Esraa 旁边的年轻女孩 Ahed 刚刚生了小孩儿,并且拿出手机给我展示孩子的照片。Ahed 今年才 24 岁,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大家接着把好奇的目光转向我,我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地说到自己今年 28了,但还没有结婚也暂时不准备要孩子。听完我的回答,女人们安静了半晌,似乎是不知该如何接话。
“那你们出来工作一整天,结束后做什么呢?”我试图转移话题。
“下午五点多离开工作室,买菜做饭,回家打扫清洁还有照顾孩子。” 坐在中间的 Jouhayna 告诉我。我惊讶地问到:“所以事情都要自己做,丈夫不帮你们吗?”

Alsama Studio 中正在工作的绣娘们
大家相视一笑地摇了摇头,许多在这工作的绣娘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全职工作的绣娘每个月通过制作手工艺品能带回家大概 100 美元,在难民营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大概需要 220 美元,其中电费通常高达每月 50 美元,还是在每天来电一两小时的情况下。受到最近几年黎巴嫩经济崩溃和疫情的影响,许多本地人都面临大量失业。而这些寄居在城市一角的难民只能不断的通过零工来赚取微薄收入,他们大部分在做水泥工、摩托司机等无需合法文件的工作,更多人则闲在家中,无所事事。
”如果他们不工作,就该帮忙做饭,打扫。“我试图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这些女人们承担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我的心有时候也很受伤。” 其中一个女人给我指了指心的位置无奈地说。”但没有办法,情况就是这样。
到这里谈话再度陷入了僵局。我转头问一直在旁边认真翻译的 Esraa:“你呢?你也想早早结婚生孩子吗?我知道她有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刚满 20 岁,肚子里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Esraa 用坚定的语气回答到:“不,我不想结婚。我想去大学当医生,还想继续做好刺绣工作,我想先实现我的梦想。”
Esraa家
多拜访了几次 Alsama 之后,我把 Esraa 那天给我的回答归结为教育的力量。Alsama 机构的创始人 Meika 告诉我,四年前她在难民营里尝试提供教育项目时,是大家对知识如饥似渴的热情鼓舞她坚持了下来。
“她们总是想学得更多,然后有一天她们就发现自己不想再重复上一代女性的命运了。”
Esraa 的英语技能则来自在 Alsama Project 的学习,这是一个针对 12-24 岁难民的初中教育项目,学校采用基于社区的转型学习(CBTL)方式,每周为不同等级的学生提供英语、阿拉伯语和数学课程,同时还有自我意识/赋能、诗歌等辅助课。如今 Esraa 正在学习等级 8 的所有课程(最高级别是 10)。绣娘工作室和 Alsama 的教育项目来自同一个 NGO 的支持,甚至在同一栋楼里。不过如今前者已经逐渐由叙利亚的女人们作为社会企业独立运营,自负盈亏。

在 Alsama Studio 里上英语课的 Esraa 和同学们
和 Esraa 熟络了一周,某天下课之后,她突然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对她在学校和刺绣以外的生活非常好奇,于是欣然答应。周五中午,我和 Esraa 穿过了大半个难民营街区,路遇“主麻拜”的教徒们虔诚地匍匐在街区一角,伊斯兰教的宗教音乐混杂着马路上的车流和人流声,衬托出周五的热闹非凡。Esraa 家在拐过市集后的一个僻静街巷里,在低矮的水泥砖墙房的一层楼房中,街巷边站着的孩子冲我大声嚷嚷着阿拉伯语,她面无表情的走在我身前,试图护住了想要凑近的男孩。
在家中我陆续见到了 Esraa 的两个姐姐和姨妈们,接着又有住在附近的邻居跑来打招呼。大家热情又有点羞涩的像我问好,我则故技重施地用两三个阿拉伯语词汇努力示好,试图打破面面相觑的尴尬,大家则总是非常友善地表示要把我称赞好看的衣服直接脱下来送我,吓得我连忙拒绝,只好老实地通过 Esraa 翻译,有一搭没一搭聊着闲天。
我环顾这个房间,空间不算小,能容纳上十几人的大家庭坐在一起,平常它们也将这个空间作为餐厅和卧室,吃睡休闲都在一起。再往里屋是一个同样格局但面积更小的房间,为家里已经结婚的夫妇准备,灯光和凉风都透不进来,除了铺在地上的软垫和墙边的小桌之外,家里没有多余的家具。房间里亮眼的是墙壁玻璃板上摆放的手工小彩灯,是 Esraa 的妈妈亲手为迎接家里即将出生的孩子叠的。
女人们分头准备着制作 Yanlanji 的午餐食材,这是一道叙利亚传统食物,一种由葡萄叶包裹着大米,在酱汁里混合煮熟的开胃前菜,也是中午全家人的主食。
不久后,妈妈回到家中,取掉头巾后长长的头发盘在头顶。她刚从联合国难民署回来,因为 Esraa 的大哥前段时间在路上被黎巴嫩人抢走了钱和手机,最后还被暴打了一顿。但申报结果似乎不太好,对方也没给予任何解决方案。如今黎巴嫩境内有 150 万叙利亚人,除了经济贫困,复杂的教派利益也加剧了叙利亚人的生存危机。逊尼派叙利亚人占黎巴嫩人口的 20%以上,他们的存在被视为威胁到该国的教派治理和稳定,危机加剧了人们的负面看法,从指责他们从本地人手中抢走工作到犯罪。
午饭结束后已经是下午四点,家里的男人在中途走进房间吃了午饭但又很快离开。大家继续围坐在一起聊天,我小心翼翼地询问起 Esraa 一家过去在叙利亚的状况,大部分人却不愿谈起残酷的战争记忆,只有一位坐在旁边的邻居和我比划着手,神情严肃地说:“ 战争杀死了我家里一半的男人,他们冲进家门,直接枪毙了所有人。”
为了缓和我发起的沉重话题。Esraa 妈妈提议要一起跳舞唱歌,起身教我跳了一个手挽手,脚步前后挪动的叙利亚传统舞步;又唱起一首民谣,讲的是战争时被迫和爱人分别却又依依不舍的故事。
这时房间里孩子此起彼伏的哭闹打断了我们的舞蹈。年轻的,怀着身孕的妈妈疲惫地侧躺在中间拍打孩子入睡,与此同时 Esraa 的另一个姐姐则待在昏暗的里屋试图哄睡另一个男孩。
“你现在住在哪里?在做什么呢?” Esraa 突然在一旁主动问起我的生活。
“我在丹麦一所大学念书。”
“你想读大学吗?” 我接着反问。
“我想试试,但我没有文件,没有文件就无法申请高中。” 她的语气略带失落。我还想再多追问一些,但马上又觉得该追问的不是眼前这个只有 14 岁的孩子。
黎巴嫩只有 3% 的叙利亚难民最终有机会进入大学接受教育。黎巴嫩的公立教育系统将黎巴嫩人和难民小孩分为上午和下午班,教授同样的内容但进行物理区隔。与此同时,公立学校老师的工资少到只剩可怜的每月 50 美元,她们没有任何物质保障去提供优质的教育内容;更多的难民孩子,因为没有合法的文件甚至无法注册学校,像 Alsama 这样的公益组织提供的教育成为了叙利亚孩子“上学”的主要途径。

在 Alsama 课间帮助摇响下课铃的女人
大部分在 Alsama 学习的孩子,在完成这里提供的初中教育后就将止步于此。如果不是有一天足够幸运地抽中联合国发放的移民签证前往下个国家,她们将在这座难民营里一直过着没有合法身份,无法自由移动,难以合法就业甚至无法拥有私人财产等一切权利的生活。据统计一个难民一生在难民营里生存的平均时间是 17 年。
“那这一切还有意义吗?” 我把问题抛给了 Alsama 机构的创始人之一 Meika。她是一名德国人,她把对难民问题的关注归因于小时候被迫成为”难民“的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她的祖父母被迫从原东普鲁士(现在的波兰区域)撤退到西德的难民营里安置。后来,Meika 成为家中第一个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女性,后来在英国开了家成功的出版公司。这让她对教育的力量深信不疑。
“即使她们一生都无法走出这里,但至少我们希望提供一种思考的工具,让她们能在夏蒂拉这个环境中重新思考并创造改变,即使改变只是一点点。” Meika 这样回答我。
离开或者留下
抽中联合国难民署每年提供的有限移民签证,前往其他欧洲国家重新安置,看似是对这些难民来说改变生活的唯一希望,但也有人选择了拒绝。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凭自己的能力和个性获得自由移动的权利,而不是因为我是某人的妻子。”住在黎巴嫩北部贝卡谷地的 Nadia 倚靠在自己创办的学校教室阳台边,逆着阳光半眯着双眼告诉我她在办理一场离婚手续。阳台远处是连绵起伏,山顶尚有积雪的黎巴嫩山。五月的阳光里伴着微风,吹起了穆斯林女人希贾布(Hijab)的一角。
Nadia 是 Lighthouse Peace Initiative(LPI)的创始人,是第三代巴勒斯坦难民,准确来说她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是黎巴嫩人。她出生成长于黎巴嫩,接受了良好的大学教育,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根据法律,她仍然必须保留父辈的难民身份。
最近唯一一次改变身份的契机是她的叙利亚丈夫拿到移民英国的签证,一年多年已经移居。他当年也在 LPI 接受教育,如今却不喜欢 Nadia 从事的工作,多次催促她一起办理移民手续。
Nadia 思考了很久,决定留下工作并决心和丈夫离婚。
在贝卡谷地拜访 Nadia 期间,我恰好赶上了她的机构所开设的一堂戏剧表演课程。剧本由原本机构的学生,现在被重新招聘为戏剧课老师的 Ahmad 所写,它讲述了一个在贫穷的社会下,每个人如何伪装成骗子互相骗取钱财的故事。
“这部剧再过半个月就要在贝鲁特城中心的剧院上演了。” Nadia 满脸骄傲地说。见我十分惊喜,她又给我播放了去年学生在舞台上的演出作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一定以为自己在看某个专业剧团的演出,但这些学生两年前报名来到这里时,还不知道“表演”是什么。如今,我坐在教室沙发上看他们用阿拉伯语一幕剧一幕剧的排演,在不知道一句对白的情况下,彻底看入了迷。
和寻常教育机构不同,LPI 最大的特色是为成年人提供影视制作、表演和音乐课程,也有为孩子提供的基本读写课程。4 年多前,Nadia 在贝卡谷地遇到了来这边拍摄难民题材电影的美国导演 Elias Matar,后来俩人打算合作,为居住在附近不远处安置棚里的难民提供影视培训课程。他们的生存境遇比夏蒂拉更恶劣一些,“家”是一个又一个的临时安置帐篷,冬天漏雨夏天蚊虫,吃喝拉撒都在一个棚里解决。

黎巴嫩北部贝卡谷地难民营的远景
Nadia 还想在这里做更多的事情,尤其是针对女性的。“我的机构过去有个孩子,在一个叙利亚男人家做保洁时被不断侵犯。”
“后来我们帮她打赢了官司,她的父母却再也不愿意把她送来学校。” 和我聊起未来打算时,Nadia 给我讲述了一个充满遗憾和辜负的故事。辜负她们的不仅来自现在这个不欢迎她们的国度,过去那个充满战争的家园,更来自伴随一生的无情的家庭。
在准备自己的离婚官司时, Nadia 盘算着再租下另外一间空旷的教室,专门为女性和女童提供庇护场所。

黎巴嫩北部贝卡谷地难民营的孩子
“许多女性在遭受性侵或者家暴,人们想要离开原本的环境去寻找自由,却没有能力。我想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给她们。” Nadia 的声音轻柔,语气却非常坚定。
尾声
离开黎巴嫩前一周,我邀请 Esraa 和她的好朋友们一起到距离难民营大概五公里远的海边散步。黎巴嫩没有像样的公共交通,出门需要打车,平时她们很少离开夏蒂拉难民营,这是 Esraa 来到黎巴嫩的七年间第一次到这座城市的海滩边散步。
海边有许多难民小孩在贩售一束束的玫瑰花,当地朋友总是提醒我不要接受。原因是背后的结构困境——很多孩子被不敢抛头露面,没有合法证件的成年人威胁出来赚钱,在本应去学校的年纪选择了辍学。
那天,和我一同走在海边的 Esraa 却径直走向了一个卖花的男人,买下了一束玫瑰递给我,那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收到玫瑰花。
黎巴嫩当地最好的大学之一贝鲁特美国大学(AUB)恰好就在我们散步的海边,通常校园环境都很好,我提议进去走一走。走进校园之后,我第一次看到 Esraa 的眼神里散发出那么喜悦和惊喜的光芒,我带着一点点莫名愧疚的感觉告诉她,我的大学也在类似这样的校园里。
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是,希望她明年争取一下 Alsama 机构每年给最为优异的一两个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后她们就能去往本地一所优秀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离大学梦也就更近一点。
最后几天,Esraa 再次叫我到她家喝咖啡。走去她家的路上,她突然说家人想过阵子一起回到叙利亚。
”那里不危险吗?“ 我惊讶地问。
“我们的房子都在,没有被战争炸毁。我还记得那里的家,我的房间是粉红色的,床上摆着公仔和娃娃。” Esraa 笑着告诉我,我突然好像在她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个女孩原本应有的普通安稳的生活。
知道我即将离开,她反问我是不是要回到中国。
“不,我暑假得回到丹麦。”
“为什么呢,你不是来自中国吗?”
我想告诉她一时半会儿我也难以返回中国,却不知道从何开始解释——我无法返回祖国,而她却只能返回家园,一个仍未休战的家园背后这一长串漫长而复杂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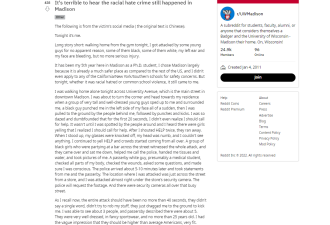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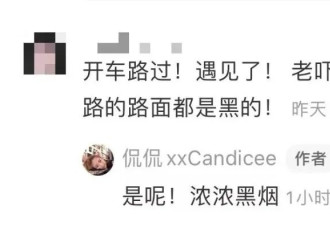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