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被报废一代人——弄虚作假五十年
思想怎么可以定于一尊呢? 一个人怎么可能字字都是真理?如果理论到某某人就是顶峰了,别人说的都不对,唯有他是正确的,别人都得听他的。那么,人类思想、人类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了。 https://t.co/hRyJHdPaWT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ne 25, 2022
“反浪费”是解放以后最先开始的运动之一,我们讲节约,物力不能浪费,但人才的浪费不是浪费吗?实际上,人才的浪费才是最大的浪费。而且,是不是送两年信思想就能改造好?我表示怀疑。
本文选自何兆武先生《上班记》第六章·被报废的一代人
从1956到86年,我在历史所工作了整整三十年。按理说,如果真正做点什么工作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的。可是这三十年,特别是“反右”以后强调了政治挂帅,整天搞运动,都是不务正业。只能在夹缝里做些正经事,根本没时间安下心来读书,其他人也一样。
历史所到今天成立五十年了,前后总得两百多人,其中不乏非常有才华、有水平的学者。如果能够创造条件让他们好好工作,成果会远远超出现在,但似乎并不是这样。比如,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历史所最大的重点任务就是写《中国史稿》,主编郭沫若。虽然他几次推辞,但仍一定要挂他的名字。这个工作做了四五十年,经常抽调二三十位骨干参加,都是领导看中的精英。到今天写完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就我所知,这套书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评价,倒是有不少人反对。有时候我就想:
“这些年来,我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呢?”

《上班记》书影
1977年5月,社会科学院独立出来,但在此之前,它名义上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分支机构。中国科学院一共分成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植;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主任郭沫若。“学部”包括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法学等等研究所,接手原来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的班底。其中,关于历史的研究所有五个:建国门的历史所,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还有世界史所、自然科学史所、考古所。历史所实际上是中国历史研究所,我所在的思想研究室就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室。
如此看来,专业划分也很细密了,不过那时候根本没有专业——不但我们没有,哪个室的人都没有。一说今天劳动,好,我们去劳动,西直门就是我们历史所拆的。明天麦收了,大家就去拔麦子。后天炼钢铁,院子里支个土炉,把家里的炒菜锅、门把手都拿出来,一天三班倒,晚上也不歇着。还有那些迎来送往的任务,早上起来揣俩馒头到所里集合,排队按照指定路线走。贵宾一般要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能来,上百万人夹道欢呼,又打标语又摇旗子,大家一起喊“万岁,万岁!”“欢迎,欢迎!”过去之后,这上百万人再按照指定路线走回单位。人山人海的,连公交车都没有了,人挨人、人挤人。那时候,如果我坐车回家只需要二十分钟,要是走的话,得走上一个多小时。进门就想睡大觉,这一天算是又报销了。
有的青年很苦闷,说:“我们究竟是干什么的,怎么净干这些?”后来,党委书记尹达传达上面的精神,说:“现在明确吿诉你们,“革命的需要”就是你们的专业。”革命需要你去“四清”,你们就得去 “四清”,需要你拔麦子,你们就得去拔麦子。
其实,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我们挂的牌子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是不是“革命的需要”?为什么不让研究历史呢?比如炼钢,当然我们可以从头学,学个三五年,或许也能出师,可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结果学历史的去炼钢,钢铁厂的工人批海瑞,把每个人都向着万能型培养,其实是“万不能”。什么都干不好,而且是效率最低下的。困难期间,据说有一种“小球藻”最有营养,培养出来可以吃,于是历史所里弄了好几个玻璃罐子做培养。我不懂那是个什么东西,不过,那本来应该是生物研究所或者农业研究所做的事,我们能研究出什么来呢?
最后不知道弄出了什么结果,反正我没吃过。
运动是多年不间断的,而且不断升级,规模越搞越大。刘少奇曾有一段话,说:“有的人不喜欢运动,怕运动,我们就是要靠运动一波一波地前进。”
就是说:运动是正常的,不运动倒不正常,所以整天就是运动。学习的任务也非常之重,往往一个重要的文件下来了,一学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整天学习。
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吿,那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不但波兰、匈牙利闹事,西欧的GC党也受到影响。二战以后在西欧,特别在法国和意大利,GC党都是第二大党,完全有可能经过选举掌握政权。可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吿一出来,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很多人退D。包括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E. P. Thompson (汤普森),就在那时候退的党。
当然这件事对中国的震动也很大,不过国内封锁得很严。大概过了一年以后,报纸上还刊出了一小块文字“辟谣”,说根本没有什么秘密报吿,大家当 然也就相信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我在美国才看到了这份秘密报吿的英文版,非常地震惊,而对于世界来讲,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是当时在国内,秘密报吿的消息一般人都不知道。正式传达的文件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是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作为正式文件传达,天天让大家学习、讨论。直到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和赫鲁晓夫有了正面的交锋,有了“九评”。每篇文章都是一学就一两个月,九篇文章学了一年多。
WG的时候更是这样。比如晚上八点钟,电台里宣布了最高指示。于是大家就九点钟集合,背最新的最高指示,然后敲锣打鼓放鞭炮,到天安门游行。回来以后都夜里一两点钟了,还不让回家,每个人都要表态,“坚决拥护……”一圈轮下来,天也快亮了,再回家睡觉。总是这样折腾,还能干什幺正事呢?
我在历史所三十年,仔细算来,真正放在专业上的,加起来不过两三年,其他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跟历史研究无关。比如文件传达,来不来就好几个小时。其实要把它印出来的话,有个一二十分钟就看完了,而且印象还深刻得多。我想在这一点上,恐怕和当年的背景有关。当年在山沟里打游击,群众都是没什么文化的老乡,又没有条件全部印出来,于是就把他们召集起来,翻来覆去的讲。可是解放后还用这个办法,何必呢?一篇大文章,念就得用一个多小时,难道大家都不识字?

钱锺书晚年伏案工作
再比如下干校,有好几位大名人,让他们做什么呢?钱锺书那时候六十岁了,算是照顾他,就让他送信。每天背一个大口袋满处跑,上坡、下坡一跑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实这种活儿随便哪个人都能干,何必一定要找个大学问家?“反浪费”是解放以后最先开始的运动之一,我们讲节约,物力不能浪费,但人才的浪费不是浪费吗?实际上,人才的浪费才是最大的浪费。而且,是不是送两年信思想就能改造好?我表示怀疑。
上面说的都是和业务无关的活动,也是最花时间、最费精力的部分,下面再说说业务上的事。2004年,历史所出了一本回忆录,叫作《求真务实五十 载》,纪念建所五十年来的种种成绩。不过我以为,实在应该再出一本,就叫《弄虚作假五十载》,讲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不过现在,那些都没人提了。
先说学术上的虚夸风。
“大跃进”的时候,社科院各个所都要上去讲成绩,听起来一个比一个的成绩大,就像打擂台一样。记得有个所上去,说:“我们所翻译的资料,一个人一天译十万字。”不要说翻译,就是让我抄,一天也抄不了一万字,他怎么能干那么多?但在那种风气下,谁越虚夸谁越受到尊敬。一天十万字,一个月三十万字,一年三百六十万字,三十年就是上亿字了。历史所以前有位先生叫田昌五,评职称的时候说:“我有一百万字!J他确实写的比我们都多,应该给他评上,可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应该自愧不如了。据说某先生短短几年就有了一千六百万字之 多,一百万字可是不值钱了呢。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持的,找了三个专家做他的助手,底下还有一批人帮助他们:一共干了二十年才300万字,平均下来一个人一年顶多也就几万字》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位先生几年下来L600万字,就像亩产多少万斤一样,这不是天方夜谭么?
领导知道我懂一点外文,所以有时也来找我。六十年代初,一天秘书处的负责人把我叫去,说是有翻译任务。拿一本书过来,但为了保密,只从中间撕下三章、差不多一百页交给我。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我不知道,内容大概是讲十九世纪中叶,一个英国旅行家Carruthers在中亚旅行的所见所闻。有一天,我们研究室的冒怀辛到我办公室来,问我在忙什么。我说上边交代了个任务,让翻译一本书。他扒到我桌上看了看,正译到这位旅行家某天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迪化知府请他吃饭。这顿饭从早上吃到天黑,一共上了三十六道菜,第一道是什么,第二道是什么……把每道菜介绍了一遍,而且中间还要把席面抬开,重换了桌子等等,光这些内容就写了好几页。冒怀辛说:
“这有什么意思,你不是浪费时间吗?”
的确如他所说,我又不研究烹饪史,也不研究美食史,费那许多精神一干就是好几个月,和我的专业有什么关系呢?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和苏联的关系闹僵了,上边要找有关中苏边界的资料。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找中苏边境问题的专家才对,他们更熟悉,也知道哪些材料最重要。我是既没研究过中亚,也没研究过新疆,连地名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得从头来,而且完全摸不着头脑。那是什么个效率,会有什么效果呢?
再比如WG后期,有一次领导交代一篇翻译的文章让我校对,结果我发现问题很多。当然,一个人的水平有高低,这是勉强不来的,就像不能要求每个运动员都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水平不行也不必嘲笑他。但你不能弄虚作假。比如参加一万米的你少跑两圈,或者参加跳高的你从竿子底下钻过去,这是不行的。这位同志的翻译,凡是疑难的句子都跳过去,原文没有的话他在那儿胡编乱造。这种翻译,除了充数有什么意义呢?
还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历史所有位女同事叫刘坤一,老燕京出身,年纪比我还大。有一次,我们的副所长拿她的译稿让我校对,同样让我惊讶的是,她的译稿不但和原文对不上,而且连中文都不通。刘坤一是研究生毕业,怎么会中文都不通呢?我不相信。后来有一次和她聊天,她大发牢骚,说:“老让我们做“无名英雄”。”比如某领导忽然对某个题目感了兴趣,就交代篇文章让底下人翻译。吭吭 哧哧干了俩月交上去,他三分钟看看没意思,啪,往废纸只一扔——得,这两个月的劳动就报销了。经她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她为什么连中文都写不通了。
对知识不尊重,对人才不珍惜,倒使滥竽充数成了风气。
1976年唐山闹地震,上面交代让整理地震资料,搞得像国家机密一样。人手一套地方志,比如《某某府志》,拿来一页一页翻。忽然发现一条记载,说康熙某某年,某地发生了地震,死了若干人。于是赶紧把它抄下来,这就是历代地震的材料了。也许这是需要的,假如真研究地震,可能也很有意思。可是我们不懂地震,也不研究地震,一弄几个月,倒也弄了一 大厚摞,做什么用呢?
学部虽然牌子挂的是“中国科学院”,但在领导体制上归中宣部管,明确属于“党的理论战斗队伍”,带有很大的官僚行政机构的性质。所以,历史所的工作实际上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比如WG前夜,历史所接到上级任务,查历代政变的资料。于是乎,男女老少齐上阵,翻箱倒柜找材料。之后不久,林彪有一个讲话在当时非常有名,历数二战以后全世界的政变以及中国的历代政变。我想,他用的就是我们提供的那些材料。后来又有所谓的“二月兵变”,针对的应该是几位老帅,最后好像 都推到贺龙身上,是WG初期很重要的一个案件。我想这或许是故意制造的一个“事变”,所以要事先找 材料渲染一种气氛。
LB事件后搞儒法斗争,把法家捧的不得了,把儒家批得一无是处,接着就是批林批孔。其实,都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林彪引过《论语》里“克己复礼”这句话,于是认为他反动思想的老根子全在孔老二的身上,所以就猛批孔老二。
如果不参与其中的内幕,你永远都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孔子已经离我们两千五百年了,我不相信他对今天还能有多大的影响,费那么大劲批他做什么?不等于唐吉诃德先生跟风车作战,犯了神经病么?再者,今天的青年人究竟有几个真正崇拜孔子、跟孔子走的?我想即使有,也是极少,没有多大力量。孔老夫子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对、哪些错,这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你要打倒什么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必借着这个说那个,一味地影射。林彪跟孔子有什么关系?
其实都是牵强附会,太政治实用主义了,也可以叫作“古为今用”吧。
再说说科学研究。按理说,那应该是先研究、再下结论。可当时正相反,我们是先有结论,而所谓“研究”,无非是给这个结论提供证据。
那几年,国内关于历史学的文章有两个热门题目,一个是农民起义。因为按《毛选》上说,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就是农民起义。另外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毛选》上说了,就是没有外国的侵略,中国也会自己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于是这些就成了热门。其实这两点都是先有结论,把结论变成了前提,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据证明。但底下这批搞历史的人就都这么附和,到处找材料证明这两个先验结论的正确。
实际上,中国的历史资料并没有农民起义的记载,都是写“盗匪”。比如黄巾起义是“黄巾贼”,天平天国的人都留长头发,叫“发贼”。于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就把所有“贼盗”都说成农民起义,把中国历史改写成农民起义的历史,或者叫农民革命史,全是造反有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历史上那么多、那么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那中国历史就应该是最先进的,是全世界发展的最高峰了一实际上却又大谬不然。英国在十九世纪以前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但我翻了半天苏联的教科书,只发现十四世纪的英国有个Wat Tyler的起义。难道因为这,英国就变成近代史上最先进的国家了?我不相信。
再有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说。这也是个设定了的结论,于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到处找萌芽,结果找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说雇佣劳动,有人提供了生产工具、雇人替他劳动,从而产生了雇佣关系,那么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了。要这么说的话,就太幼稚了。比如我请个保姆帮我做饭,她没有生产工具,锅碗瓢盆都是我提供的,每月我要付给她工资,这就 是资本主义萌芽了?按我的理解,什么是萌芽?它得开花、结果才能算是萌芽。可是萌了几百年的芽,始终没有继续发展,那还算是萌芽吗?古今中外到处都有雇佣劳动,那全世界就到处都是资本主义萌芽,那还得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事先设定一个唯一正确的理论标准,大家都要照着这个说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敢反对。但是,思想怎么可以定于一尊呢? 一个人怎么可能字字都是真理?如果理论到某某人就是顶峰了,别人说的都不对,唯有他是正确的,别人都得听他的。那么,人类思想、人类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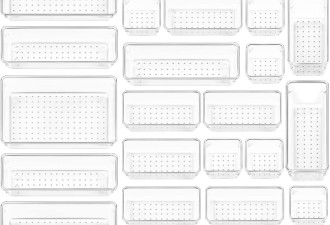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