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收骨团”1975年赴滇收日军遗骨
在研究写作滇西抗战历史的这些年里,笔者无数次地与“遗骨”与“亡灵”问题遭遇。在拙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序章中,笔者尽量以平静的心情写道:“如何对待阵亡人员遗骨,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但当昔日在滇缅战场交战的日本、中国及其盟国美国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在眼前赫然对比,郁结于胸的痛楚与悲愤是难以抑制的。最让人难以面对的,是日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做法。

节节败退之际,脖子上仍挂着骨灰盒
1944年,日军在滇西战场上遭受惨重失败,战死的日军尸骨遍地。战后,日本方面曾绘制了滇西地区遗骨分布图,日军遗骨分布为:拉孟(松山)阵地1250人,红木树附近100人,龙陵周边2937人,腾冲城及周边1800人,瓦甸及大塘子附近200人,桥头街及冷水沟附近100人,芒市及上街附近878人,遮放及滇缅国境附近400人,保山附近约200人……合计约8265人。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资料只是日军在松山、高黎贡山、腾冲、龙陵等地阵亡后“弃尸”的情况,并非其阵亡的全部数字。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资料,在滇西战场上,侵华日军共战死14052人。但除了在松山、腾冲两地因“全员玉碎”而无法收尸,在其他各地的战斗都属被击溃后还是收敛带走了部分尸骨。
据很多抗战老兵回忆,当年跟日军作战时,即便打了胜仗,也很难看到日军尸体,他们对收敛处理阵亡人员尸体极为重视。在日军传统中,战场上弃尸是对军人归属感的伤害,会严重影响部队士气;另外,日军非常好面子,即便从“护短不示弱”的角度考虑,也会及时处理阵亡者遗骨。
据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李嘉祜1944年4月20日呈报《腾冲敌情报告书》载:“……(日军)凡有伤亡,必严密警戒不令人见,焚烧扫除后方才解除警戒”。在松山战役中,日军指挥官曾下令“处理”重伤员,要么用手榴弹自杀,要么吞下用来代替毒药的升汞片。实际上,这种办法已属“人本”之举,在过去流动性较强或仓促间失败的作战中,日军对重伤者甚至“活杀”。“……每有伤亡,必将死尸抢运后焚化,决不留一具尸首与人看见。轻伤者抬回医治,重伤者虽其人尚能言动,要求抬回医治,皆不听,每以大刀砍为两段,以马驮之而回”。从这些事实来看,至少在操作层面,日军处理遗骨的做法并非纯粹基于“人道”,或者对于牺牲精神的呵护,反而强烈地体现出将人作为战争工具和材料的色彩。这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最近在读军事科学院编译的内部图书《日本陆军统帅纲领与统帅参考》,这是1928年、1932年日军为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中将以上)颁布的战略战术法规及诠释文本,日本自卫队又于1962年重印,作为干部、军事研究家的必读书籍。在书中笔者发现,对于“靖国亡灵”的祭祀,曾被列为日本帝国核心的统治权,由天皇直接行使。具体表述如下:“日本帝国鉴于立宪政治的弊病,为了限制其危害,规定统帅、祭祀、奖励等统治权均不由国务大臣辅佐行使。这就是帝国宪法的精神。”文中所说的统帅权即为兵权,这正是日军被称为“皇军”的缘由;而祭祀权竟位列其次,可想这个问题在日本帝国政治构架中的地位。

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笔者认为军旗与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最高物化形式,是解读日军这只凶猛怪兽的秘密所在。实际上,军旗对应着统帅权,靖国神社对应着祭祀权,如果再加上对应奖励权的荣誉勋赏制度,对于日本帝国“精神”的理解就大致全面了。
在这一制度和文化理念指导下,日军在相关问题上的做法极为引人注目。
通常情况下,日军对阵亡者的处理遵循着一套完整的制度。一般为,在战场上及时将阵亡者尸体烧制成遗骨,装在骨灰盒里携行;待战事告一段落后,由各级指挥官亲自主持,举行大型慰灵式祭奠,而后择机运回日本安葬,灵位入祀靖国神社。若遭遇惨败战事,难以及时处理完整的尸体,就采取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以专用的“化学燃烧毯”或干脆架上柴火烧制成遗骨。到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挎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战争时期日军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歌,即为《怀抱战友的遗骨》;除非遭到惨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绝不抛尸弃骨。
一户腾冲居民光复后回家,发现自家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奖章等物。这显然是收集好准备后送的。那户人家又惊又怒,一炬焚之。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全员玉碎”,日军是不会如此狼狈的。
战后的几十年,日本人在费尽心力地弥补着这个缺憾。
“搜骨”经历漫长坎坷,但日本人执着如初
在日军野炮56联队战记《炮烟》一书的附录中,有一份日本战后在缅甸收敛阵亡人员遗骨的资料,是自1975年首次向缅甸派出“收骨团”赴缅,直至1980年派出“慰灵团”来zhong 国云南活动的大事记。每次收骨回国后,日本国内的各部队战友会即组织慰灵祭,资料中还附有侵占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龙兵团)及其所辖野炮56联队的历次祭奠活动的详细记录。
这一切的发端,是日本于1973年发起成立“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推动日本政府厚生省于1974年制定出“海外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并为即将派出的“全缅战联协”团员募集活动资金,在当年4月和10月两次共募得8500万日元。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缅甸战场的阵亡人员约为13.7万,因此留下大量未能及时处理的弃尸。

1975年,第一次“收骨团”踏上了赴缅旅程,成员由141人组成。其中,厚生省职员10名,老兵90名,阵亡者遗族25名,还有志愿者组成的“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成员15名。此次,共收集遗骨10717柱。
1976年,第二次“收骨团”赴缅,此次由163人组成。其中厚生省职员12人,老兵100名,阵亡者遗族40名,“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成员10名。此次共收集遗骨12589柱。
以上两次共搜集遗骨23306柱。
日本方面如何在缅甸打开的局面,笔者未见详细的资料,然而“金钱铺路”这一点却是不会错的。
战争时期,缅甸为英国殖民地。日本为实现侵缅意图,战前即派遣特务赴缅积极活动,以支持缅甸民族独立运动为诱饵,组织昂山、奈温等一批缅甸民族精英在日占区台湾、海南予以培训,又秘密遣返回国组建缅甸独立军,在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时积极配合;当时,中国派出远征军第一路赴缅与英军并肩抗日,很多缅甸人却对我怀有深深敌意。虽然昂山后来看清形势,于1944年倒戈加入了反法西斯战线,协助盟军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投降,但1947年英国又反悔当初允诺缅甸独立的协议,指使歹徒刺杀了昂山,使缅甸人深受伤害。此后,缅甸民族主义意识日趋浓烈,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昂山的继任者奈温以仇华反共为政治基点,铲平了缅甸境内的大量中国军人墓地和纪念碑,却对前来收骨、慰灵的日本人予以配合。
从1975年开始,在政府、财团和民众的大力支持下,日本人在缅甸打通了种种关节,在各个战场都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灵塔和纪念碑,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还是居民房,日本人皆重金买下做祭祀之所,甚至,为战死缅甸的军马也立了纪念碑。距曼德勒三十多英里、伊洛瓦底江边的自敢山,为缅甸著名佛教胜地,山上山下佛塔林立。风光最佳处,有一座由日本人出资修建的巨型鎏金佛塔,是其悼念战死者亡魂之所,白色佛塔基座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几千个日本军人的名字。以这座塔为中心,四面有日本人修建的各种慰灵塔、悼魂碑、镇魂牌。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大量日本人在僧人带领下来这里进行祭祀活动。日本人为在缅甸和滇西战死的800匹军马所建立的纪念碑,在它旁边,还有一块由台湾人立的台湾籍日军战死者的纪念碑。
几乎与在缅甸的活动同步,日本人也开始了对于中国云南的活动。虽然期间经历漫长坎坷,但日本人却始终执着如初。
1974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云南昆明。他们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阵亡日军的亡灵。这个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这是作家邓贤在《大国之魂》中提及日本最早为滇西遗骨问题与中国方面的交涉。
1978年,原侵华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品野实,办理了赴中国的护照。但受当时形势所囿,他仍未获准允许去滇西地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写一本书——后来这本书写成了,就是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异国的鬼》。
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当时云南对外开放地域限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虽然大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人却个个愁眉不展,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临行前,他们面西肃立,而后长跪不起。他们仍是要到滇西祭奠日军亡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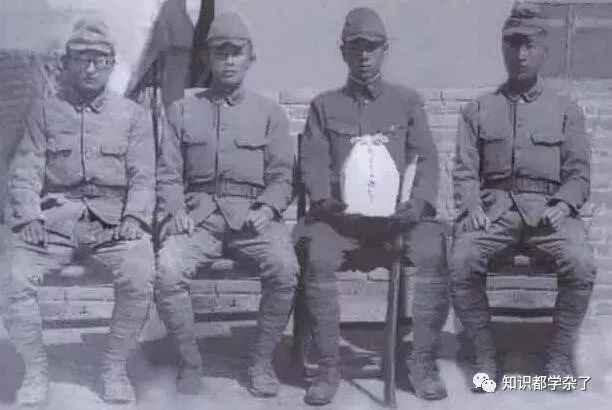
1980年1月,日本人终于在战后首次踏上滇西的土地。这次,由日本“全缅战联协”派遣的“云南地区慰灵团”来到中国。大概在外交接洽环节,日方已考虑到在中国收骨不会成功,这一次只是试探性地派出了10个人来摸情况,成员由清一色老兵组成,以甲谷秀太郎为团长。这次品野实又积极争取,却仍未能被选中,大概因为他在战争时期仅参加了龙陵作战,不属最重要的亲历者。与那段历史有密切关联的10个日本老兵中,有从松山战场奉命逃出去的原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在腾冲战场活下来的卫生兵吉野孝公,还有在龙陵帮助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自杀的大尉副官土生甚吾,及曾在第56师团司令部任职的中尉石井皎。据品野实《异国的鬼》一书记述,“这次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这些日本人得到了滇西战场上的泥土”。回国后,在原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多的日本人终于可以以“旅游观光”的名义来到滇西。在松山旧战场上,他们一般不跟当地老百姓说话,表情肃穆。上了山后,在这个再度枝繁叶茂的山峦里搂树抓土,哭天叫地,诉说祷告……当地人印象最深的一位日本老者,曾带着一群男女儿孙来到松山,坚辞导游,竟能在山上轻车熟路地走动。有当地的明白人问他:你是当年那位逃出去的日军炮兵中尉吧?此人正是木下昌巳。从1980年起他来滇西十多次,心愿只有一个:为死在松山的日军在当地建一座慰灵碑。为此他走访了所有死者的遗族,向他们讲述死者最后的“战迹”;他后半生全部的心愿就是满足死者的心愿。为此,他曾表现出一些诚意,比如捐资龙陵在原日军第56师团前进指挥所驻地赵氏宗祠前建了一所白塔小学,当地人谓之“赎罪”学校。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有保留的理解,但认为他要为松山日军阵亡者立碑之事,却属非分之想。
笔者在滇西采访期间,常常听到当地人说起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这些,自然是日本方面在通过外交努力无果,从而私下活动后播散出来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据载,“云南地区慰灵团”自1980年起至1990年代,至少4次来到云南,曾改换名义为“日中友好恳谈会”,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1988年7月,日本“全缅战联协”常务理事甲谷秀太郎一行4人沿滇缅公路到达滇西,在龙陵、腾冲、芒市、畹町等地战场遗址进行谢罪忏悔。参加活动的老兵们当时已六七十岁,他们也做了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们三番五次来云南的真正目的。当时在昆明市日资企业——日本华兴株式会社驻昆办事处供职的陈晓耘女士见证了这一事件。
1990年,陈晓耘应邀参加了欢迎甲谷秀太郎的宴会。甲谷认为陈晓耘是日本公司雇员,似可信任,所以在昆明逗留期间曾多次到陈晓耘工作之处拜访。陈晓耘了解到,甲谷参加过侵缅战争。一次,甲谷将一份滇西各战场日军遗骨分布图给了陈晓耘,其中《拉孟(即松山)阵地要图》和《腾越(即腾冲,为旧地名)城附近守备要图》上清楚地记录了1944年6月至9月的战斗情况。甲谷对日军的侵华罪行做了谢罪,同时希望收集遗骨的事能有所突破。在多次通过外交的、民间的交涉未果后,甲谷希望陈晓耘能帮他在此事上做些工作,回到日本后又多次来电。但陈晓耘认为,日本侵略云南的史实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罪恶,所以婉拒了他的请求,并请他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那么,当年日军丢弃在滇西的遗骨情况到底如何呢?
据资料,有少量是在战死后由日军自行处理的,活下来的日本老兵曾记录保存下来一些资料;大量的则因无法及时收尸,在战后由当地人收敛掩埋了,由于当事人纷纷离世,已很难找到准确的位置。但是,当地也保留下了日军丢弃的一些遗骨,并挖掘出了一部分,至今仍集中保存着。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是国内最早披露这一信息的人。2002年,方军在龙陵采访见证抗战的“最后一批人”时,曾看到了这些日军遗骨,并在《保山日报》首次报道。据当时龙陵县史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1988年至1989年,县政府曾组织人力在松山一带收集了一些日军遗骨和遗物。当时组织挖掘的目的,一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二是史志办需要收集一些与战争相关的资料和物证。之后,这些遗骨和遗物被装在陶罐和木箱内,一直放置在龙陵县史志办的仓库内。据闻,2005年龙陵抗战纪念广场落成,这些东西又被搬迁到了新建的抗战纪念馆内。

方军曾对所看到的日军遗物做分类介绍:
有五个陶罐装的骨灰,是日军第56师团将在缅甸战死的日本兵烧成骨灰,带入中国滇西的。据说日军当时曾准备带着这些骨灰打到昆明、重庆去。装骨灰的陶罐口小、肚大,是缅甸萨尔温江流域妇女顶在头上使用的陶瓷器皿。
当年战事结束后,当地群众担心污染空气和水源而收敛日军尸体,属于草草掩埋。1988年,仅在松山挖掘出了其中一部分骨骸,装在本地烧制的三十几个陶罐里。
此外,和遗骨一起出土的还有日军的钢盔、皮鞋、饭盒和炮弹等物品,装在二十几个木箱里。
据闻,日本方面看到后,曾与中国外交部交涉,希望就此遗骨的返还问题进行磋商。但此后的消息是,当地政府回应本地并无此物,媒体刊载的消息属作者个人行为,本地不予证实。
(注:文章摘自《看历史》 作者:余戈 原题为《日本:在遗骨与亡灵背后隐忍》。)







![[二手好物]台灯](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1ee4ce31-34ab-4f0e-b55f-969d7b956e33.1080x1080.jpg)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