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年父母 在北上广做保安和服务员
2021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67亿人,卫健委此前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近1800万老人,背井离乡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成为“随迁老人”。他们来大城市的理由极其相似,不是帮子女赚钱,就是给子女带娃。这也是一个沉默而庞大的人群,他们依偎在子女身边,人到老年,远离家乡,重新接受一线城市的节奏与洗礼,甚至开启一个全新的人生。
而工作,成了“老漂”们帮儿女带娃之外,试图融入大城市的最关键一步,他们或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在大城市立足,“不给儿女添压力”,或是想证明自己还能继续发光发热,创造价值,在工作中得到自我认同。但在北上广深,年龄大、没技能的老年父母们,注定要在工作中尝尽苦头,帮父母找工作的儿女们,会如何看待父母的困境?
老漂
母亲49岁,北漂5年了。
这是王倩倩的母亲。她的“北漂”母亲已经在北京换了4份工作。2017年,最小的儿子也去了北京,家里除了丈夫以外毫无牵挂,母亲一口气打包行李从山西运城老家出发,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北京。
到了首都,她对三个孩子说,“我想找份工作了”。在此之前,母亲住在农村里,干了一辈子农活,从没上过一天班。王倩倩在家里是大姐,给母亲找工作的活儿自然落到了她头上。
给母亲找个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别墅区保姆,王倩倩向老乡打听来的,平时需要负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但母亲没想到,去了以后,衣服全都要手洗,一个别墅的卫生全由一人负责,她还需要顺带照看雇主家的老人,根本忙不过来。
▲ 图 / 视觉中国
一个月后,母亲辞职了。王倩倩又带她去了商场,一家一家问,招不招人。母亲先后去了杨国福麻辣烫和章鱼小丸子当店员,工资5000元,住在地下室宿舍里,每天忙到凌晨,回去倒头就睡。
在南边的上海,陈怡也在带着母亲找工作,这是陈怡来到上海的第3年。和王倩倩的情况相似,陈怡和弟弟都在上海工作,母亲便也投奔而来。母女俩走过火锅店、小炒店、早餐店,但凡看到有招聘启事,陈怡拉着母亲进门就问,“我妈成吗?”
她给母亲圈定了一个工作范围:母亲不会坐地铁,不能距离自己太远,最好步行或骑车能到;母亲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上海专业的月嫂需要证书,所以服务员、家政相对适合一些;以及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再熬夜上班。这样圈下来,可选的并不多。
很快,陈怡发现一个问题,母亲的年龄在上海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来上海之前,爸妈生活在山东老家,春夏秋自己种大蒜,冬天就做临时工,父亲去冷库扛蒜,母亲给厂家包装大蒜。和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已经错过就业黄金期——上海大多数家政和服务员都要求50岁以下。
她同时在网络上给妈妈联系合适岗位,看了一个保洁和服务员,原先聊得好好的,陈怡刚把母亲的年龄信息发过去,对方就没了下文。网上要求很明确,但母亲就是多了一两岁。
“我当时就准备带我妈在线下试试看,可能还会有些空间。”陈怡转头看了母亲一眼,虽然52岁,但母亲皮肤不错,看起来还算年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走进下一家火锅店时,她撒了一个谎,“我妈身份证当时登记错了,她真实年龄只有48岁”。
事实上,陈怡发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人会在意这一两岁的偏差。“见面和网络不一样,当面找工作,对方更关注我妈妈的整体状态。”陈怡的母亲就这样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火锅店服务员。
在大城市,初来乍到的父母们没有门路,大多只能依靠子女给找工作,或者自己挨门挨户地问,小区物业、写字楼、商场门店,碰到个差不多的就先试试,但总逃不出保安、保洁、服务员这些范畴。相对来说,拥有各类证书、牌照的中老年人,选择的空间就要大很多。
同在上海的李淼就顺利给公公找到了一份家附近的工作,公公以前是来往于天津港和山东的货车司机,大车牌照是公公最大的优势,刚开始,李淼考虑过让公公开校车,但上海不比过去的长途固定路线,公公不熟路,不敢开。
后来他们发现,家附近的建筑垃圾转运站正在招洒水车工人,公公一试就成功了,一个月6000元,三险一金,上午、下午绕着转运站各洒两圈水,工作也轻松,“至少不用和一大批人争抢保安、保洁这些岗位”。
妈妈在地下室住了一个月后,王倩倩总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她又通过在北京的山西人,打听到一个在京的老乡群,里头有一些山西人当中介,介绍工作机会,确认入职后,才会拿抽成。这些招工信息相当详细,会具体到工作时长、工资待遇以及年龄、性别和身高限制。
在群里,她替母亲找到了一家新的餐厅,也是当服务员,在海淀,包吃包住。最后一天,王倩倩一大早帮母亲来宿舍收拾行李,她才看清这个宿舍的环境,一个不到4平方米的地下室,灰白墙,水泥地,没有窗户,透着一股沉闷的霉味,屋子里只有竖放的一张床,和一张左右摇晃的桌子,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
走出逼仄的房间,王倩倩往四周看,密密麻麻的小门像无数的孔洞,看不见头。天还早,已经有人陆续从小孔中走出,这些基本上是外来务工的中年人,走廊没有灯光,看不清他们的真实模样,每个人套在工装里,快递员、外卖员、服务员,他们拉开房门,光线立刻从缝隙中涌出,关门,瞬间又复归昏暗。
▲ 王倩倩帮母亲找工作的接单群。图 / 受访者提供
“就是来赚钱的”
第一次来大城市,几乎每一位父母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不适应。
陈怡母亲刚上岗时,因为不会用iPad,经常点错菜,被客人骂。从老家来,她并不适应城市餐饮店的规则。
陈怡有时候会把母亲接来自己的出租屋住,有一回,她心情不好,倒豆子一般和母亲说了工作上的烦恼。母亲突然沉默了,抬起头,竟然带着哭腔说,“我今天也被罚款了”。
她才知道,母亲今天有一位客人逃单了。通常情况下,作为服务员,客人买单时,只需要尽到引导职责,前台收银才负责每一位客人的买单工作,但经理从母亲的工资里扣去了客人两百多元的饭钱。陈怡向母亲追问,店里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样,母亲只会哭,一直摇头,言辞含糊。
陈怡也哭了,她忘记自己是怎么下的楼,当天晚上一个人冲到了火锅店里。店里快打烊,只有零星几个服务员在收拾桌椅。她在后台找到了经理,“我们两个的语气都不是很好,我是替我妈委屈,他有一种不想搭理我的感觉”。陈怡要求他们调出了监控,在录像里,她看到,母亲明明已经向客人用手势指引了前台买单的方向。
争论的时候,陈怡的电话没有断过,都是母亲打来的。母亲担心陈怡和老板起冲突,在电话里边哭边大叫,“你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咱们不要这个钱了,妈妈再也不说了”。
陈怡最终没有等到经理的道歉,对方只同意不罚款。走回家的路上,陈怡在想,“我的妈妈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母亲年轻时脾气暴,一有不顺心,吃饭就摔筷子,她和沉默的丈夫不同,遇到不公平的事,敢红着脸和别人争论,一定要求个公平。但现在,母亲学会了顺从。后来陈怡才知道,经理有时候脾气上来了,经常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母亲的鼻子骂。
“你多忍忍,人家气消了,就不会骂你了。我们就是来挣钱的。”母亲告诉陈怡。
今年年初,陈怡的父亲也来了上海。父亲是电焊工,早年和叔伯们去了扬州的一个县城船厂,工作到现在。船厂小,需要等活,忙起来一个月能挣一万多,有时候干脆一两个月没有收入。
父亲是陈怡和母亲一起劝来的,“想着都在上海,一家人能在一块儿了”。起初父亲并不愿意,他对上海一无所知,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直到陈怡给他找了一个崇明岛船厂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又是他熟悉的工种,父亲同意了。
但一家人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经常见面,在崇明和在扬州,并没有多大区别。父亲整日被困在船厂里,无聊时就看看东海,偶尔会给陈怡发消息,觉得“有些孤单”。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闷。有一回,陈怡和他通电话,父亲突然向她吐槽起了船厂的网络很差,时有时无,他怀念过去在扬州的日子,也没网,大家不舍得用流量,一群老家人呼啦啦跑到隔壁村子里,蹭wifi刷抖音。“那是第一次他和我说,自己想回家了。”陈怡说。
▲ 节假日时,陈怡妈妈要凌晨才能下班,陈怡和父亲会一起去接她下班。 图 / 受访者提供
唐悦的母亲3年前来北京投靠自己,她的父亲是村支书,母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每个月收入只有2000元不到,干脆辞职来北京。
她带母亲参加了家政培训班,母亲毕竟是老师出身,有竞争力,一周内就找到了份不错的工作,在通州给一家人做饭接送孩子,加上辅导基础作业,一个月6000元。但很快,职业的不稳定性也显露出来,孩子的妈妈失业了,家庭收入的动荡让这家人重新考虑未来规划。他们最终选择卖房,离开了北京,唐悦妈妈也随之失业。“她和那家人感情特别深,本来想一直陪那个孩子到小学毕业的。”
在一个新城市里,尽管投靠最亲近的子女,父母们依旧不得不面对城乡的差异,要适应那种快节奏、灵活多变的市场,也要面临自我尊严与价值的重新审视。这个过程很难,但每一个中老年父母都清楚,他们不可能再轻易回老家去了。
李淼邻居家的大爷也在找工作,人到60岁,过了进转运站的年纪,只能去附近做保安,经常通宵,眼睛熬得通红。在转运站,60岁是一条红线。李淼还记得,公公和她提起过转运站的一对四川夫妻,负责垃圾分拣,刚到60岁,转运站就给他们下发了清退通知。但夫妻两当作没看见,每天顶着主管微妙的眼神,照常上班。他们的儿子还没结婚,两人加起来一个月能在上海挣一万块,这都是儿子未来的彩礼钱。
“听说过年也不敢回家,生怕人回去了,工作就没了。”李淼说。
▲ 图 / 视觉中国
一切为了孩子
当然,牵绊着父母们无法离开的,还是孩子。在大城市里赚钱,大多是给孩子赚的,来到大城市生活,大多是来照顾孙辈的,能让已经退休的父母们放弃老家安逸的生活,背井离乡来大城市继续发光发热的,只有孩子。
李淼的孩子今年两岁,正是需要人带的时候,公婆两人都从山东老家过来给他们带孩子。像这样的父母,是老漂群体的主力,孩子大了稍微好带一些,父母闲下来的一方就会出去找工作,找点事做,顺带赚钱,减轻大城市生活的压力。
唐悦的母亲也告诉她,同村有一个女人,来北京给女儿带孩子,女儿的公公也来了,“家里已经用不上她,就让她回老家”。但女人自己又想留在北京,不同意回家,干脆在医院找了个保洁工作,一个月3500元。
在中国,大多数父母的职责随着子女的需求而变迁,这种需求甚至直接决定了父母将处在哪种社会角色上。王倩倩家一共三姐弟,过去父亲开长途,母亲就在运城老家种苹果,孩子一开学,苹果就不种了,得接送孩子,孩子放假了,又回去操起农活。如此生活数十年,直到小儿子走向社会,“她才彻底解放”。
“解放”了并不代表可以停下来歇歇。在母亲心里,一直还挂念着儿子以后的问题,需要继续赚钱。母亲就在县城里找了几份工作,但老家根本无法为中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薪资。王倩倩的妈妈卖过衣服、给别人打过小工,还在一个化工厂上过一阵子班,夏天厂里比外头还热,化学材料隐隐透着股刺鼻的味儿,三个月合同一到期,母亲吓得立刻就走。
▲ 王倩倩母亲在饭店工作。图 / 受访者提供
唐悦母亲起初也在县城里的工厂找过一份出纳工作,早出晚归,一个月3000元。李淼公公没来上海前,在老家做过环卫工人,凌晨三四点就得起来,一个月只有4000元不到。“其实父母过去付出了很高的劳动成本,回报却很低。”陈怡庆幸自己带父母来上海,他们在山东老家种蒜种棉花,种出他们的学费已经艰难,一辈子也没存到钱。
如今在一线城市,他们的收入上涨不少甚至翻番。来北京几年,王倩倩母亲已经盘算着给儿子在县城买房了。
唐悦母亲失业后,不到一周,又找到一份工作,同样是住家保姆以及辅导小孩,一个月工资涨到了8000元。母亲欣喜若狂,没想到自己在北京“是有价值的”,但唐悦知道,真正让她开心的,是自己还能给小儿子多存些钱。
她的弟弟即将结婚,按照安徽老家的规矩,男方需要买房,或是出个买房的大头数,再加上十几万的彩礼,母亲过去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看。如今房子倒是买了,家里存款也空了。尽管母亲对唐悦说,“你弟弟房子买了,我现在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养老钱”,但唐悦偶然一次听到,母亲小声打电话向安徽的亲戚打听,“装修一般得花多少?”
陈怡也发现,最近休息的时候,妈妈总是给她带一家附近早餐店的卷饼,她觉得奇怪。母亲在火锅店的工作下班晚,多数时间住在宿舍里,两人平时也见不着。“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又开始支支吾吾。”
一个周末,陈怡起了个大早,顺着周边早餐店找过去,果然在一家店里看见了母亲,她正在包子蒸笼的氤氲里忙得不可开交。她一问差点崩溃,这么久以来,母亲晚上在火锅店忙到凌晨一两点,早上就背着陈怡,偷偷起来在早餐店打下手。这种两份工的日子,母亲已经持续了两个月。
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陈怡不想承认的事实:“为了给弟弟多攒一些钱。”
这是父母无法抛却的天职,人到中年,儿女长大,新的压力又扣上一环,他们又该为下一代的成家与血脉繁衍而操劳。父母的情绪甚至传导给了唐悦,她早已成家,又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经济条件还算宽裕,不忍看父母操心,弟弟买房前,她一咬牙,一口气转了十几万过去。而陈怡能做的,是帮母亲辞了早餐店的工作,以及自己下班后,去火锅店帮母亲收拾桌椅,再拖个地。
只有极少数父母,会因为追求自身的价值而来到大城市。
何夕婉准备给55岁的母亲在深圳找个工作,来之前,她劝过母亲好多回,“别来了,在家养老多好”。但母亲并不愿意。她大专毕业,选拔分配到了何夕婉父亲所在的炮弹厂,在这里成家生子。炮弹厂是个封闭的小社会,这里的员工几乎都是子承父业,家庭和工作以及社会关系紧紧缠绕在一起(电视剧)。只有何夕婉的母亲是个异类,她没有任何背景,也无法融入这里的内部规则与风气,更没办法和丈夫的发小朋友们待在一起——他们没有任何的共同话题。
在何夕婉的记忆里,母亲不爱出门,下了班就回家,对她的态度也不同于其他家长,她鼓励何夕婉自由成长。直到5年前,母亲在炮弹厂提前退休,她自己又在家门口找了个高校后勤老师的工作,统管所有宿管人员。有一天,何夕婉和母亲走在校园里,那些大姐看到她,一个劲打招呼,“老师你来啦”,母亲就笑眯眯地点点头。
何夕婉当时才反应过来,母亲也需要自己的朋友和一个舒适的圈子。今年10月,母亲从高校后勤岗位上退休,她明明可以吃穿不愁,又总是闲不住,立刻打电话告诉何夕婉,“我要去深圳找你啦,不待厂里了,快帮我问问有没有保洁和家政可以做”。
但何夕婉妈妈的存在终究是少数。在某种程度上,多数中老年父母就像浮萍,漂浮在孩子的人生之上,水流一旦有波动,就任由自己随意转换方向。王倩倩的老姑和母亲曾在同一个饭店工作,老姑当了好几年洗碗工,补贴家用。老姑的儿子,今年给她生了个孙女,结果她只能回家,兜兜转转,一切又拉回了“带孩子”的原点上。
“回家了,现在可后悔了,说家里根本找不到这么挣钱的工作。”
▲ 图 / 视觉中国
离开的与留下的
王倩倩的父亲去年也来了北京。他55岁,过去是个卡车司机,常年往返于山西和福建,疫情导致客户和生意大减,父亲在老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母亲一通电话,把父亲叫来,王倩倩又开始前前后后给父亲张罗工作。
但北京就业市场里,中年男性显然没有女性占优势,工作多数为体力活,留给父亲的选择并不多。父亲最初在一家银行里干保安,负责看监控,朝九晚五,4000元一个月,因为请假回家和经理闹得不愉快,被辞退了。后来王倩倩给他找了高铁上水工的活儿,高铁一停,父亲需要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给高铁车厢加热水,时间一长,父亲总爱听别人的议论,听说高铁上水工,冬冷夏热,每天吃的也是青菜豆腐,就不肯再去。
▲ 男性大多能找的活都是保安、巡逻类体力活。 图 / 受访者提供
后来听说一家餐厅招传菜工,父亲又去干杂活,结果除了传菜,洗碗拖地、后厨点菜都得干,父亲不想跑动,没干几天又走了。
母亲总对父亲说一句话:“怎么别人都干的下去,就你干不下去?”
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过去,王倩倩父母的地位关系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开完长途车一回家,躺下什么都不用干,一切由母亲操心。在北京找工作不顺利后,父亲开始对工资特别敏感,他会私底下问王倩倩,“这个工作,有你妈(工资)高不?”
王倩倩倒是理解他,父亲跑车一辈子,早就过惯了没有拘束的生活。“或许我爸只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她想到老家的叔叔,去了很多城市找活,工地、工厂,都不适应,只有一个护工的工作,他一直做了下去。“他就喜欢那种坐在那儿,看个人,啥也不用干的。”
现在父亲回了运城老家,“他在北京根本待不住”。走之前,他叹了口气,“来一趟,啥都没干成就回去了”。
在上海,李淼的公婆来后,家里多了许多矛盾。公婆看不惯李淼夫妻点外卖,唠叨挂在嘴边,夫妻俩只能躲着吃。公婆本来就睡得早,加上公公第二天一早要工作,8点就早早上床休息。但李淼和丈夫时常加班,孩子精力又旺盛,10点多还在家里跑来跑去,时不时敲开公婆的门。“老人家也没办法”,李淼能看出他们在极力忍着困意,下床陪着孩子玩。
来了城市,父母不再是自己,而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婆婆腿脚不好,公公下班后,担负起了带孩子下楼玩的职责,他很少有朋友,眼睛也从不敢离开孩子。但他极少和李淼夫妇说起这些,直到今年夏天,上海天热,婆婆带孩子回老家住,公公下了班后,什么也干不了,坐在家里看着电视直发呆。
李淼试探地问了一句,“不然爸爸您也回家住几天吧?”公公眼睛瞬间就亮了,又马上低下头,这份工作没有节假日,他回家几天,就意味着扣几天的工资。李淼看着心疼,告诉他:“不用在意这个钱,咱们回家。”
候鸟迁徙,总有想家的那一天。回家几天,公公的状态明显好起来,回上海后,他满嘴还离不开老家的亲戚、朋友和收成,边说边比划,眉飞色舞。
来了上海,陈怡觉得,一家人见面时间好像也没有增多,尤其是父母之间,差了几十公里,坐趟公交,来回就得一天。她正在尽力让一家人拧在一起。她帮弟弟学编程,让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孩子顺利留在上海。陈怡买了辆车,开车带着母亲和弟弟去崇明岛,最近父亲告诉她,自己花150元买了辆黄色的自行车——其实是一辆没锁的被盗共享单车,平时能在园区附近骑自行车多走多看。
在陈怡爸妈的那个年代,当工人、农民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与土地打交道,多数人并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等到时代迁移的机会到来,他们已经陷在土地里,再也赶不上,逐渐脱轨。而子女们却越飞越远,两代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少了很多共同话题,现在一家人还能经常待在一起,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陈怡还记得第一次开车送父亲去崇明岛上班的那天,当时主管看到这对父女,对陈怡父亲打趣,“哎呀这么大人了,还让女儿送”。沉默寡言的父亲第一次红了脸,扭过头去。那一瞬间,陈怡突然觉得,“我要成为家里的那棵大树了”。
让王倩倩有些安慰的是,母亲倒还算适应北京,她今年得了个优秀员工,饭店给她发了一笔奖金。自己也和饭店的客人越来越熟,有一回,她兴奋地和倩倩说,今天有人叫她的名字了。
那是在北京,第一次除了家人,有人叫她的名字。不是服务员。不是阿姨。更不是喂。
而是,“郝大姐,你好啊!”
▲ 王倩倩母亲工作的包厢。图 / 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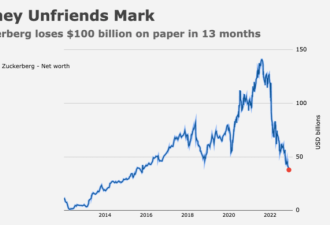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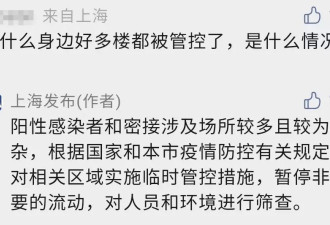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