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冠感染潮涌向白鹿原上的卫生所 ....
去年年底下了一场大雪,白鹿原留下的斑驳痕迹还没有完全消失。
何城的卫生室开在废弃的乡村小学,正门朝北,也是村里人中常说的阴面。平时阳光无法直接照到门前,兼又有房屋遮挡,即使已经过了半个多月,门口地面上还是留着各样被踩踏且凝固的冰面,进出的人们小心翼翼,寻找不易滑倒的地方探脚,两位穿着红色大花的棉袄大婶,互相搀扶着向里迈步。
何城没有时间去打扫门前的积雪,过去的一个月,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迎头撞见了自己作为村医执照上岗后最“乱七八糟且心有余悸”的一段日子。

1
在何城的记忆里,这一切开始的毫无预兆——
“感觉头天还要去镇子卫生院支援做核酸检测,结果第二天就说在家等通知,第三天就直接说以后再也不做核酸了。让我们回自己所属村落待命,后来就允许根据情况自行问诊了,这个问诊特指发热。”
12月7号之后,西安主城区的新冠感染者数量激增,在中旬就已经显著扩散并持续走高。然而不同的是,何城清晰记得自己不足20平米的诊室里迎来的第一个发热病人来自12月19日。
“村里有个婶子一大早就敲门,天还黑着,正冷的时候,差不多六七点钟,她说自己浑身疼,好像有点发烧,睡不着,折腾了一夜,所以等不到天明就来了,想让我给打一针。”
何城说,他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诊疗发热病患的经验了,过去近三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在卫生院的实习,还是在同为村医的叔叔跟前学习,“政策上,都是不允许我们这些诊所私自接受发热患者的,都得往定点的医疗机构送。”
过去3年,何城的主要工作从看病变成了核酸采集、封村站岗,早上不到5点就赶到镇子做准备,中午12点再回驻村,何城的卫生室在疫情期间大多都在关门状态。忙于防疫而被迫停诊以及无法接诊发热病人的情况让何城的问诊收入常常徘徊在千元上下。
何城说,对于许多村镇一级的医生来说,在这之前对于真正新冠确诊者的接触都少之又少,而这也意味着,面对突如其来涌入村镇卫生室的这群发热邻里,何城的诊治经验都几乎为“0”。

当然,这些在乡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新冠感染者。
过去几年,为了让更多人意识到新冠的危险及传染性,许多村里老人们接触到的宣传措辞都令他们心生恐惧,也因此,面对具体的诊疗,何城更多是告诉他们的问题是感冒发热,或者是气管炎之类。
他对老人们很少讨论新冠,一方面,卫生室只有他一个人,没时间指导老人使用抗原自测;另一方面,他担心告诉老人们反而会把他们吓坏,“好多人觉得阳了很可怕。”
而对于老人来说,最常见的表示身体不适描述自我症状的用词也不过就是,“我可能受凉了,所以有点发烧,你给打个肌肉针肯定就好了,检查啥,不用查,费那钱干啥。”
和村民打交道久了后,何城也有了自己的一些乡村生活智慧,比如,顺着村里叔婶们说话,声音要大,语气要显得坚定有力,多以安抚开导为主。
乡村的八卦和闲言碎语有时候比病毒感染本身还要传播的快,谁家有人刚从西安回来就进了卫生室,谁家又发烧头疼一直咳嗽,一开始的日子里,人们之间有种诡异的默契,拉开的距离暗示着对于彼此的怀疑。直至彻底爆发,“全都一样了,也就没谁嫌弃谁了。”
大家打招呼的方式也完全变了,从“你吃了没?”到“你阳了没?”——前后不过三五天。

2
但对于何城来说,短短三五天里远远无法完成妥善的反应和准备。“那时候我还听有专家说农村感染潮得在春节后,哪能想这么快啊,全铺开了。”
12月16日,有关部门发布《关于印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要按服务人口的15-20%人份动态储备抗原检测试剂盒。
但何城没有采购,不仅是因为没有采购渠道,连他自己都没有做抗原。“感觉没啥必要,之前核酸检测免费大家都不想做,还得催,抗原需要自己买就更没人了,而且农村老人多,也不会操作,演示都麻烦得很,现在就是治病,对症下药就行了。”
大多时候,何城都选择给村民按照感冒发热的经验进行诊治。

然而,当时在何城的卫生室里,连基本的退烧药也难以保障。过去3年,退烧药、止咳药、抗生素和抗病毒药长期被列为严格管控的“四类药品”,何城没机会也没任何概念预期提前做储备。
后来,再采购又已完全来不及,“城里都买不到,更别说我们这些村里小诊所了,我这一盒布洛芬都没有,药商那边进价就得28一盒,我想了想还是算了,村里人便宜的药买惯了,你多收他一块钱他都要问你个一二三,解释起来太费劲了。”
至于网上最近大火且引起热议的辉瑞特效药Paxlovid和阿兹夫定,何城表示在自己的印象里那只是一个模糊的名字,因为但凡超过100的单价药想在村卫生室卖给受众,“那几乎就属于天方夜谭,哪有人要啊?”
面对感染潮,何城的药房里只剩下此前常备的“大罐子配药。”
预估到药品不够的现状后,何城只能选择用输液或打针来替代。“人最多的时候,我这一天至少20多个挂吊瓶的,床上地上围着坐的都是人,我叔叔那更夸张,他负责的村子接近2000口人,每天天不亮就开门,直到半夜三更才能歇下,打退烧针有时要排队一两个小时,挂水的也在50多人左右,根本顾不过来,全天不带停。”

何城手中的检查设备主要是体温表,血压表和听诊器,至于具体该怎样问诊,则全凭经验,何城也深知抗生素的使用需要做药敏,但是简陋的卫生院实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时候也会听到外界评价说他们都是“ 抗生素 + 激素 ”输液两件套,方案不科学,但何城对此难以评价,他说“管他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况且这是病毒性感染,我也没见到什么特别规范成熟的治疗方案,指望我们村医自行研究,这不是开玩笑吗?”
面对疫情过峰,何城在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考验。“首先,能自己抵达村卫生院的八成以上都是老人,且很多都是轻症,症状主要是发热、咳嗽、咽痛等,严重的肯定打 120 送到上面的医院了,所以对症下药也没啥错,而且照目前形势看,这么治也不会有啥大问题。 ”

3
村里的人大多信赖挂吊瓶的效果,因此大都主动要求打针或输液,“他们难受了好久,想要的不是开几盒药,劝也劝不动。”
大量的输液需求现实,也导致何城的吊瓶、生理盐水、葡萄糖都陷入短缺,后来由于缺货的缘故,这些药品的价格也产生上涨。“连基础液体都从三十多一箱涨到七八十。就这也得采购,但物流又卡住了,买不到就找关系弄,或者跟其它附近村医互相交换,看对方储备量稍微多点的话就想办法匀一点。”
来卫生室看病的人,发烧只要到 38.5℃ 以上的,何城大多会给他们挂吊瓶,一般是炎琥宁或者是维生素 C。低烧的就给开点自己配的白色绿色片片药,“因为实在没其他的。”
针对部分老年人,何城也选择抗生素加上葡萄糖治疗,“一般三五天也就差不多了。”而其用药的抗生素也主要为头孢类抗菌药,“当然,也有一些有抗病毒效果的中成药,像双黄连什么的。”

何城时常觉得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也看到新闻上说医院爆满、重症患者排不上队的信息,一方面很紧张,怕自己真正遇到棘手的情况,另一方面又觉得,多亏自己负责的村子人口少,不至于完全没有精力应对未知。
何城身边虽然少有老人去世的情况,但私下村医们的交流中,何城也发现这个冬天,去世的老人比起往年多了不少,他凭感觉认为,这或多或少和新冠之间有联系。
至于何城自己,这个冬天距离病患死亡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2月24日,“正是忙的时候,村上有个婶子打电话说她爸爸不太好,老人说不了话,几天不好好吃饭,也没法下床,想让我去她家帮着看一下,我说给这波人挂完水就去,1点多,人少了我赶紧往她家跑,去的路上打电话想再问问啥情况,结果她就说不用来了,老人已经走了。”
老人去世后,埋在村头的公墓。办过白事后,村里又陆续出现了很多发热症状的人。
在关中农村,造成病毒传播的渠道往往是集中进行的婚礼或葬礼,人群聚集为病毒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翻开互联网上的短视频,农村的大席上,往往是村民们围坐一起吃吃喝喝的画面,而画外音却是此起彼伏的咳嗽与喷嚏声。
12月中下旬的感染潮高峰,何城每天都要接诊至少30余位病人,到现在,每天的人数减至10人以下,但何城也坦然承认,不敢说第一波感染潮已经完全度过。

由于自己的家距离负责的村卫生室还有一段距离,为了方便工作,何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过去的一个月,何城的门都在6点左右就会被敲醒,小小的卫生室里挤满了前来挂水或问诊的老人,早上的时间段里总是满满当当,至于那些打电话的,行动不便的老人,也只能等待着何城忙完再在空闲时上门诊治。
而一旦要到上门诊治的阶段,何城也就都做好了告诉患者家里人提前做好心理,或者赶紧送往大医院的准备。“就是那个没撑到我去的大爷,他下葬没几天,他老伴也卧床不起了,我去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基本能确定是肺部感染。嗡嗡嗡的,让往西安送去拍片治疗,但老人太犟了,死活不去,家里人也是,可能也没有心劲了吧,让我给开消炎药,打针吊水,减缓老人的痛苦就行,但我这里,更多的措施也做不到了,剩下的只能看命。”
对于许多村里的老人来说,“确实都只能靠命,命硬的,熬过去,命薄的,就走了。”这个冬天,死亡成为了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元旦前后的日子,村子里三天两头都是鞭炮声。
“不是为了庆祝新年,我叔给我说,他们村里,两天走了四位老人。”
■ 文中人物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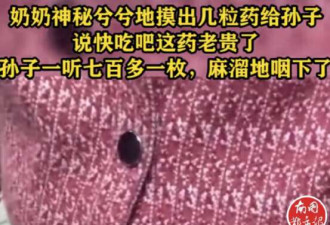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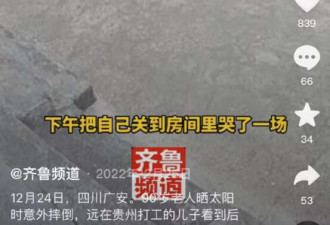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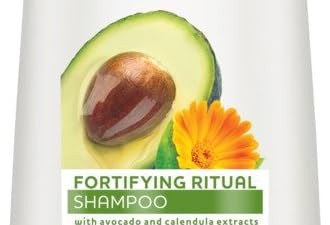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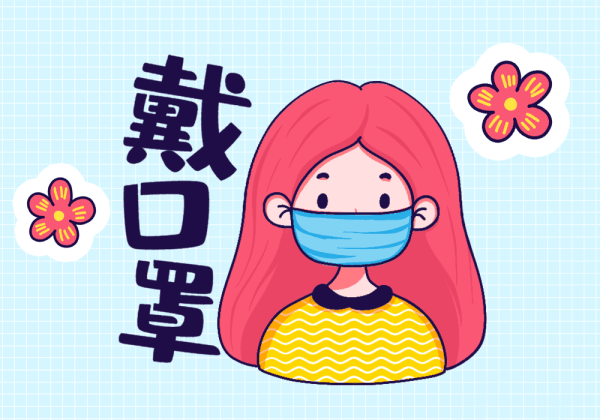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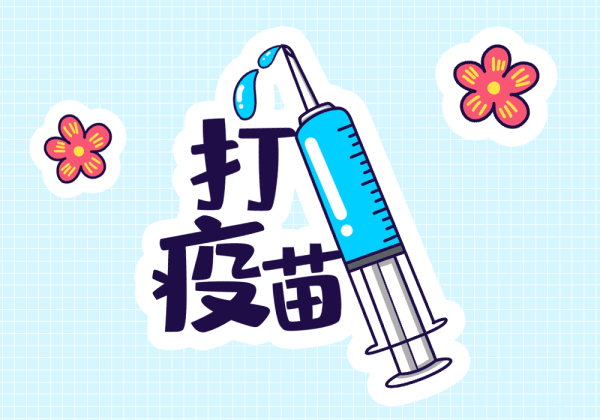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