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做噩梦?是你的身体发出了信号

梦境对人类来说,一直是神奇的无人之境,噩梦的来源却是我们的心理产生的恐怖幻想。
“你确实只身在梦乡”
这全都起源于一只会说话的蟑螂。“在它说话的时候,我能听到它嘴巴发出的咔咔声,并且感觉到它的腿在抓挠我,”克里斯蒂娜·华莱士(Kristina Wallace)写到她可以回忆起的第一个噩梦,她才四岁。到她六岁的时候,她开始思考为什么没有害怕沉入梦乡。在她32岁的时候,噩梦还缠扰着她。
梦代表了我们大脑最难以捉摸的一部分,把我们在清醒时接受到的所有感官信息组织成从极其平凡到令人费解的恐怖的冒险。做梦的潜在目的之一是带走我们大脑中的所有碎屑,在一场幻想中的狂欢中将其散列,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
噩梦,是最可怕的一种梦,是我们的一部分。它是比梦本身还要可怕的一种概念。“梦是由内部产生的。”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拉斐尔·佩拉约(Rafael Pelayo)说道:“它们代表了你的想法和你的恐惧。你基本上是在害怕自己所产生的东西”。外部世界可能提供了噩梦的来源,但却是我们的心理产生这些恐怖幻想。

Via:《盗梦空间》
噩梦让所有人都困扰,但如果它们开始影响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噩梦就触及到了精神紊乱的领域。梦魇症(Nightmare Disorder, ND)的特征是每周有四到多个噩梦,并且持续的噩梦感觉逐渐侵入到日常生活中。梦魇症常常出现在三岁到六岁,并对有些人来讲,它在10岁后会减弱。大约有4%的成年人经历梦魇症。
针对这种情况也有一定的治疗法。哌唑嗪(Prazosin)是主要的处方药,它也可以治疗高血压。但对很多人来说,包括华莱士女士,这些治疗法并不管用。最近,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其他治疗法,包括以认知为基础的方法还有清醒梦。这两个治疗法皆在帮助人们更好应对噩梦,也能帮助我们最终理解噩梦以及为什么会控制我们的思想。
佩拉约说道,当我们大脑睡觉时,大脑一部分在做梦,一部分通过两个不同的过程来产生梦的内容。他说位于脑干的脑桥被认为是“主要的发电机”,把大脑转变为做梦模式。如果梦在脑桥中产生,那么原材料来自于海马体和相应的大脑皮层(海马体是情感与记忆中心,而大脑皮层是像面条一样的结构,并且掌控着我们的感官输入)。同时,控制着决策功能和推理功能的前额叶的活动减少。佩拉约解释这样的减少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会质疑梦的真实性,让我们很容易被说话的蟑螂吓到。
华莱士的梦魇症可以“很容易变得虚弱“,她写道。噩梦会让她在清醒世界中变得神经兮兮的。她会从她中枪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却会在同一个地方伴随着幽灵般的疼痛感持续着她的一天。
“你确实一只脚活在梦境中。”她写道。华莱士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手工艺人。
“很难去解释梦魇症,因为如果你的解释不够好,它就听起来像一场狂热的梦,但现实是你沉静在这样紧张的梦中,你经历的一切就像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一样”,华莱士写道。每个人在试图描述一场梦的时候,都在寻找救命稻草。但华莱士惊讶地发现,在梦退却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回忆起山上刺骨的寒冷,她曾在那里躲避了一直灰熊,感觉就像几星期一样。
梦魇症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紊乱症状,但它也是来自于现实经验的创伤性后遗症(PTSD)的结果。佩拉约认为PTSD是大脑无法去忘记一些事情。“能记得美好的事情是很好的一件事,但能去忘记事情也是同等重要的。你不应该把每一个小东西都塞进大脑。”他说道。

Via:《盗梦空间》
学习与野兽共存以及如何驯服它
一种认知行为治疗法,意象训练治疗(Imagery Rehearsal Therapy,IRT)用作治疗噩梦。在这项治疗中,做梦者有意识地回到噩梦中,并改写它的结局。
“基本上,就是让你回去重新掌握全局”,佩拉约说。噩梦可能仅来自我们的大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掌控它。“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家,并且画了一幅很可怕的画,你可以改变画面的,对吧?你也可以改变你的梦。”
IRT对华莱士的评价喜忧参半。她说IRT只有一部分对她有作用,但她还是在练习它。即使她不能找到比较快乐的结局,它可以帮助她处理痛苦的感受。“我会让我的大脑过一遍发生了什么,然后拥抱我内心自我,所以我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它不是真实的,或者不是现实发生的”,华莱士写道。
十月份发布在期刊《Current Biology》中的一篇研究想用定向记忆再激活法(Targeted Memory Reactivation,TMR)作为IRT的补充治疗。通过TMR,一个人将特定的记忆或感觉与一个提示联系起来。这个提示可以是一种声音或者气味,因为气味被证实是与记忆最有关的感觉。
在这项36人患有梦魇症的实验中,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的实验员把参与者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在两周内只练习IRT。另一组在练习IRT的同时使用TMR,也就是它们在白练习IRT并这个过程中聆听一种特定的声音----钢琴和弦C69,只播放一秒钟。
在睡觉的过程中,后一组的成员会带可以检测何时进入快速翻眼睡眠阶段(REM)的头带,这是睡眠的最深阶段,也是梦境产生的时候,然后研究人员播放那一个声音。理论上讲,这个小组将一个更积极的梦境与这种声音联系在一起。一旦这个声音播放起来并且深入到最可怕的梦境的一个节点中的时候,这有利于在梦境中浮现安全感和控制感。
两周后,比起只练习了IRT的小组,同时进行IRT和TMR的小组不怎么频繁地受噩梦的折磨,并且享受梦境里积极的情感。在没有任何深入的干扰后,这种频率在三个月后依旧持续减少。
在日内瓦大学的神经科学研究员索菲·施瓦茨(Sophie Schwartz)强调这两组的噩梦都有缓解。但IRT和TMR小组有更明显的缓解,这种变化一直存在,让施瓦茨和她的小组感到惊讶。

Via:《无尽梦魇》
施瓦茨对这个治疗法抱有希望。“通过在家中部署和普及易于使用的设备来永久巩固安全记忆,这些疗法可以很容易地影响到大部分临床人群,并带来促进情绪健康的新创新方法,”她写道。虽然这是一项需要更多调查的概念验证研究,但它为未来对这种联合认知疗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外,施瓦茨强调,IRT 是一种已经建立的方案,仍然值得尝试,因为 ND 和其他导致频繁做噩梦的疾病的治疗进展缓慢。
该研究给佩拉约留下了好印象。他认为这是第一次临床上使用TMR。把一种声音和积极情绪联系起来,从而缓解噩梦,是一种“很炫酷”的治疗法。他对把这项疗法运用在除REM外的睡眠阶段和更广泛的人群中感兴趣。
华莱士知道目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停止噩梦,但她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举个例子,她避免有歌词和鼓点的音乐,锻炼到她身体筋疲力尽,并且只在中午前摄入咖啡因。她两只狗和同样患有梦魇症的丈夫也是一个福音。
她最后提到:“尽管每个人都听烦了这句话,试着去爱自己,并且善意地和自己内心对话。”她写道,“是的,我还是每晚都会做噩梦,并且它们真的很可怕,但它们也变得不再让我感到害怕了,因为我可以在梦中和自己冷静地对话。”
佩拉约说还有一种有用的治疗法。即使很难每日都做到清醒梦,但它也可以有效治疗噩梦。在此状态下,做梦者在做梦时十分清醒,并且可以控制梦中的决定和行为。
在 2020 年发表在《心理学前沿》杂志上的国际清醒梦诱导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 355 名参与者的认知技术以诱导清醒梦,发现该研究中有 55% 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清醒梦。
IRT是迈向清醒梦的一步。它帮助梦者重获控制。清醒梦比较难实施,佩拉约说。清醒梦大师不仅控制他们的动作,也可以控制整个梦境。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探索自我隐藏的一部分,把令人可怕的未知变为我们从未有过的新奇经验。
佩拉约回忆起他已故同事威廉·德门特(William Dement)——被誉为睡眠医学之父——曾经教过他清醒梦。这个学生会做从悬崖掉下来的噩梦。德门特指使这个学生在清醒状态下去撞地。
“这个人真这么做了。”佩拉约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他告诉德门特,他反弹了起来。”

Via:《盗梦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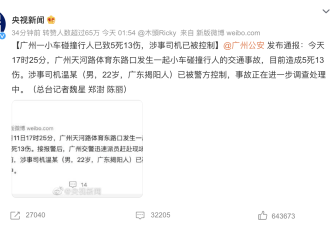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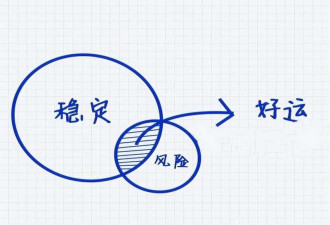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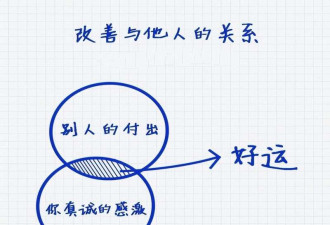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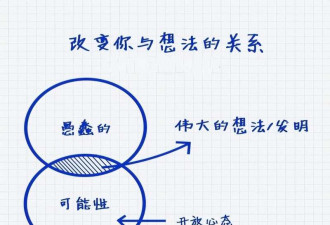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