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成为了移植中心取器官的医生
01 第一次危机
1989年底,一个漆黑的冬夜,一架螺旋桨飞机掠过美国中西部广袤无际的原野,飞向堪萨斯城。当晨曦布满天际时,小飞机再次升空,朝着东北方向飞去。我的心情如同初升的太阳,在云蒸霞蔚中冉冉升腾。
这次飞行是为了完成一场手术,对我这样的访问学者来说,它或许胜过一个博士学位,因为这预示着我有机会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器官移植中心,成为肝移植的主刀医生。飞机上为我们准备了三明治和阿拉斯加雪蟹腿,怎样从坚硬的蟹壳中轻松取出一条蟹腿肉的功夫,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三个月后,我成为了匹茨堡移植中心“首席”取器官的医生。在六位来自不同国家取器官的医生当中,我包揽了百分之六十的手术。东京电视台专程来匹茨堡做了个节目“日本医生在匹茨堡”,却意料之外地给了我一个特写镜头,可能是想展示一下日本医生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匹茨堡移植中心的风采,为大和民族争得了荣誉吧。在东京的Suzuki医生看后当即打来电话自嘲了一番,随后给我寄来了那段录像的光盘。
有一次,我乘飞机去圣路易斯取脏器,因为器官质量不好,我们早早地升空返航。当飞机飞临圣路易斯著名的拱门上空时,大家起哄要求飞行员穿越拱门。飞行员在我们的欢呼声中,驾驶飞机在拱门上方盘旋了几圈后,面对着拱门俯冲飞行,在一片惊叹声中,飞机从拱门的上方一掠而过。那时,全天候飞行已成为我每天的常规,我期待着有朝一日在这里更上一层楼,主刀肝移植。

一天,我的上司Dr. Todo通知我不要再做取脏器的手术了。我在惊诧中问:
“为什么?”
Dr. Todo说:“你有三份来自器官捐献医院的投诉信,OPO*决定取消你取器官医生的资格。”
我脱口而出:“不可能!”
Dr. Todo摊开双手说:“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是来通知你一声。”
我在眩晕中努力回忆了我最近做的所有手术,确信它们没有问题。于是,我立刻驱车去了匹茨堡OPO办公室。刚进门便迎面碰上办公室主任Mr. Bryan,他比我高出一头,仪表堂堂,他是跟随Dr. Starzl打天下的“马仔”。
我开门见山,向他陈述了我的情况。他说,确实接到了三封投诉信,然后摊开双手说:“我也没有办法帮你。”
我说:“这不可能!我可以看一下信件吗?”
他说:“信上没写医生的名字,但我们调查后发现,那几次都是你值班。”
“好吧,您可以给我那几家医院OPO的电话号码吗?”
“可以。”
我追问了一句:“情况不明之前,我能继续手术吗?”
“不行。”他回答得斩钉截铁。
“Please!”
“No!”
我在美国刚刚起步的外科职业生涯就这样戛然而止。
回到家,我抄起电话,从下午一直打到深夜,终于彻底弄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确定此事是张冠李戴,但不排除有人故意移花接木。
午夜时分我拨通了Dr. Todo家里的电话,我说:
“对不起,Dr. Todo, 深夜打电话给您!但这事我无法等到明天向您汇报。”
Todo平静地说:“没事,你说。”
我急切地说:“确实有三封来自器官捐献医院的投诉信,但没有一封与我有关。”
“那为什么Bryan要停你的手术?”
“Bryan打电话问了来自南美的主治医生、师兄何塞, 他告诉Bryan那几天是我值班,所以Bryan就停了我的手术。”
其实,在匹茨堡并没有取器官医生轮流值班这一规定,而是由负责器官移植的手术医生决定谁来获取他(她)即将移植的脏器,采用末位淘汰制。显然,何塞没说实话。
我接着说:“我直接打电话给了器官捐献医院,从手术记录中查到了三个医生的名字。这是三个不同的医生,此事与我无关。” 我又告诉Dr. Todo:“其实Bryan可以仔细查一查OPO的飞行记录,也是不难弄清楚此事的。”
第二天一早,Dr. Todo对我说:“你可以继续手术了。”我在匹茨堡的第一次危机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开始,又闪电般地结束了。或许这只是虚惊一场,不能算作危机,但于我印象深刻,总感觉这是我在美国工作中面临的第一次危机,因为它差点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失去在美国重新握起手术刀的机会,这是我留学的“初心”。我触电了,感受到这里的电光火石。从此我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这里的一切,在后来的无数次危机中,我渐渐融入这片神奇的土地。
02 传票
1993年,我成为美国爱荷华大学移植中心的主治医生和助理教授。
一天,我从手术室回到办公室,坐在摇椅上抿一口咖啡,回味刚刚结束的手术:又下一城,新的肝移植术式让我们接近了两小时的手术时间极限,小儿亲体肝移植也有了重大突破,肾移植已经迅速从全美国第六十的排名升至第十一位,爱荷华大学是胰腺移植的发源地之一,乌卡医生第一年就成功的做了十七例......
门口,金发碧眼的女秘书轻轻敲门,送上了今天的文件。她刻意递给我一只大信封,看着我的眼睛说:“传票。”我在惊愕中打开信封,四年前的一段往事浮现眼前。
那天是周末,我在匹茨堡儿童医院值班。十点钟,护士报告有个全脏器移植的小病人早晨做了腰部脊髓穿刺,现在穿刺点周围出现了淤斑。我仔细检查了这个小病人,一个小淤斑,下肢活动自如。我舒了一口气,没有脊髓损伤的症状。想想该是早查房的时间了,于是打了一个电话给马里奥,他是我的上级医生,来自南美州。电话无人接听,我继续打,一直到中午始终是忙音。我有些诧异,把电话打到了儿肝移植主任西蒙的家里,汇报了小病人和马里奥的情况。西蒙没有新的指示,让我继续观察小病人的病情,等待马里奥前来查房。到了下午,护士突然给我来了电话:“吴医生, 那个小病人后背痛得厉害,你来看一下吧。” 我再一次给小病人做了体检,感觉他下肢无力。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马里奥和主任,同时请了神经外科会诊。MRI (核磁共振)确诊为硬膜外血肿,压迫脊髓。神经外科的手术立即开始,血肿被清除,可是小病人术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截瘫。

全脏器移植示意图
晚上10点钟,马里奥医生终于给我来了电话:“对不起,吴医生, 昨晚有个大聚会,我临时改了机票,多待了几个小时。你猜,我碰到谁了?” 稍停片刻,他又问:“怎么样,病房里都好吧?” 马里奥大概是刚下飞机,兴奋中有点气喘吁吁。
午夜,马里奥来到病房,病人已安然入睡。
第二天,病房里看起来井然有序,其实暗流涌动。大家窃窃私语关于昨天的事故,传说病人家属要告医院和移植科医生。随后,有人悄悄地告诉我,在病历封存前,有人改了那个小病人的病历。我知道这是犯法的,但感觉与我无关,就没放在心上。
一个星期后,主任西蒙在办公室里对我说:“你的处理没有错,只有一点今后要注意,你给马里奥打电话的事也应当随时记录在病历中。” 来美国之前,我在中国的教学医院做了五年医生,从来没有遇到法律纠纷,也没有建立随时记录病情之外点滴事件的职业素养。而这个疏忽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又过了几天,马里奥在办公室里拿着一份文件对我说:“吴医生, 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字。”
我读了一下文件的内容,大致是说事故发生的那天,我没有打电话给主治医生汇报病情,特此证明。
我对马里奥笑笑,说:“这不是事实。”
马里奥也笑笑,说:“这种事起码五年后才会追究,那时候你已在中国,谁也管不了你啦。” 他朝我挤了一下眼睛,半真半假地说:“我们还要在这里混饭吃。”
我想,马里奥是我的同龄人,我们一起查房,一起手术,我不知道马里奥是不是把我当成朋友,但我对他却充满朴素的真诚。在中国,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一件美事,何况我眼前的这事儿不过是个顺水人情。于是,我没多想,笑嘻嘻地签了字。随后,马里奥脸上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拿着那份文件飘然而去。
此后整整四年,我与马里奥像两个绝缘体,再无交集,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从回忆中醒来,仔细地阅读传票。那上面清楚地写着小病人父母状告匹茨堡儿童医院,和爱荷华大学的移植科主治医生-我。至于移植科主任西蒙,主治医生马里奥,晚上值班做腰部脊髓穿刺的医生,和他一起做穿刺的急症室医生统统榜上无名。
小病人家属要求五百万美元的天价赔偿,这个天文数字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来美国前我在中国作为医生的月工资只有十美元啊。
那时我事业上风头正劲,在为晋升副教授努力。事情来的如此突兀,我捧着传票,不知所措地坐到暮色降临。作为外科医生,我可以从容面对手术室里的任何突发状况,有足够的胆量去迎接任何挑战,然而第一次面对法律诉讼,我除了陌生、还有恐惧,对未知领域的恐惧。
几天后,从匹茨堡的律师事务所寄来了一整箱病历,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仔细回顾了那天的细节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接着,我去了爱荷华大学法律系,邀约了我熟悉的一位研究器官移植的法学教授。他给我讲解了美国法律诉讼程序,并善意地提醒我说,你现在属于爱荷华大学,你的律师是为匹茨堡大学服务的,你可能并不是他们的重点保护对象。
我问:“对我来说,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失去工作。”
“啊?”
他看我一脸茫然,又解释:“如果你输了五百万的案子,你从此就有了案底。爱荷华大学不会因此辞退你,但你如果再次找工作时,别的医院就会认为你是一个trouble maker (麻烦制造者),就不会给你机会。”
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社会个人信誉的重要性,不,准确地说,这场无妄之灾让我意识到一场危机正排山倒海的向我袭来。那段日子,我感觉头上高悬着达摩克利斯魔剑,我忘我的开刀,似乎手术刀会随时离我而去。
春天来了,我锁着眉头前往日本京都参加世界移植大会。
会议期间,大家相约去了世界最大的木塔朝圣,一千多人排着长队求签。我看着老和尚哗哗哗地抖动签筒,从不拜佛求仙的我,平生唯一一次在心中虔诚祷告,希望佛祖能庇佑我安然度过那个五百万美元的诉讼案。我的眼睛紧盯着老和尚高悬在空中的手,看着它缓缓地放下。“啪”的一声,一根竹签飞出签筒,老和尚捡起竹签,朝我作揖,嘴里嘟哝了一句日语。我在昏暗的灯光下,战战兢兢地看那根泛出油光的竹签,赫然入目的竟然是三个中文字:上上签。

我暗自庆幸,付了二百日元的抽签费,接过老和尚递来的宣纸,一张印有“上上签”的符。我捧着它如获至宝,挨个去问别的医生抽了什么签,出乎意料,我竟是那天第二个获得上上签的朝拜者。一个星期之后,我怀揣着“上上签”飞往美国的匹茨堡。飞机起飞时,我在心底对自己说,我会度过危机的,作为医生,我始终恪尽职守,臻于至善,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03 触电法律诉讼
那是一九九五年的初夏,我走进了匹茨堡最富盛名的钻石大楼,见到了我的律师。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穿着灰色的西装,打着红色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也穿了正装,握手后我们坐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涉及法律诉讼,心中有好奇,但更多的是忐忑。我先向律师陈述了事故当天的情况,律师只是点头,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律师告诉我,明天的听证会将持续一整天,简单的说,就是对方律师不停地问你各种问题,你要随时回答。今天我们见面的目的主要是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在开始之前,我先讲几个最基本的原则。
他侃侃而谈,我戴目倾耳,认真聆听。虽然他说的很多内容于我很陌生,然而它们却不断地给我全新的感受。听完他专业性的陈述,原本忐忑不安的我进入到一种奇怪的状态,就像一个无知的人打开了一扇神奇之门,眼前的一切是新鲜的、未知的、微妙的。
“记住,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主动提供信息。你在回答问题时应尽量简短,记住三个字就可以了。” 律师看着我的眼睛说:“Yes, No, and Don’t Recall. (是的、不、不记得了)” 他特别强调:“今天,我不会教你明天怎样去回答问题,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回答问题的方式方法。” 接着,他又一次郑重地强调:“我不会教你如何具体地回答问题,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决定。律师误导当事人是违法的。” 我对律师这番话似懂非懂,频频点头。
接着,律师扮演原告的律师,对我模拟提问。他的问题之多,之繁琐,之细致,令我极不适应,只能根据记忆和临时的判断,尽可能迅速地做出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喜欢刻板又单调地重复问我同一个问题。比如:你吃饭了吗?没吃。你吃饭了吗?没吃。你吃饭了吗?没吃。

几次三番后,我逐渐意识到什么才是我该说的“正确答案”。于是,当他再一次问:“你吃饭了吗?我便毫不犹豫地回答:“吃了。” 他对我的回答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立刻机械地开始下一个问题。
中午,我和律师一起去吃工作午餐。呵,我第一次发现匹茨堡竟然会有如此丰盛的午餐,可惜我官司缠身,毫无胃口,脑海中充斥着许许多多模棱两可的问题,我不停地琢磨到底怎样回答才是“正确的”回答。很多年后,我再复盘这件事时,得出一个结论,事实在律师眼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一个逻辑清晰的故事。
下午,我们重复着上午的一切,我像一条疲于奔命的猎犬,不停地追逐那些问题,差不多过了四个小时,我终于在无可名状的极度疲劳中听到律师宣布:“你明天可以上阵了。”
华灯初上,匹茨堡下城的夜晚恬静而优美。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空旷的大街上,鬼使神差地进了一间酒吧。
酒吧里人声鼎沸,很多人在喝酒。匹茨堡生活了六年,我从没把自己当成一个美国人,也从未进过酒吧。我在高高的吧台边坐下,学着电视里看过的画面,要了一瓶啤酒,两眼呆滞地望着电视里的球赛,大脑一片空白。酒精是个好东西啊,我渐渐的感到燥热,头脑中往日的时光闪现。记得隔壁就是那家我刚来美国时每周打一天工的中餐馆,老板娘来自家乡南京的一家医院...... 我又想起了明天的听证会,许多问题杂乱无章的涌上心头。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能请我喝一杯吗?” 一个妖艳的女郎叼着长长的女士香烟,张着红红的嘴唇在向我微笑。我顿时有了电影情境的感觉,装作老酒吧的范儿,看着卖酒的吧女,用手指在吧台上敲了几下,嘴里发出声音:“请来一杯。” “要什么酒?” 坐在一旁的女郎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吧女知道我没听懂,也许她看我喝的是最廉价的啤酒,或是看出我对酒吧的生疏,她对那位妖艳的女郎说:“别欺负老实人了,是个新客。” 说完开了一瓶啤酒递给了女郎。我与女郎实在找不到可以讨论的话题,于是匆匆地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在吧台上放了二十块钱,扬长而去。那晚,我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早晨神清气爽,我走进了原告的律师事务所。
我举起右手宣誓,回答姓名、职业,验明正身。没有悬念,一切问题我们几乎都有所准备。对方律师翻着医学典籍,在专业术语和英文方面给我出难题,好在我和我的律师都一一化解或拒绝回答。下午听证会结束前,原告律师站了起来,口中振振有词,逻辑清晰地指出了我在这起医疗事故中应付主要责任的理由,他在结束前连着问了四个为什么,然后自问自答,他说完后扬起眉毛微笑着看着我。我也在笑,我在笑他用排比句说我符合了所有医疗疏忽的四大条件。原告律师带着胜利的微笑结束了他字字铿锵,言之凿凿的总结。我的律师没有提出问题,也没有做总结发言,我只看见原告律师一脸灿烂的笑容,大家在一片祥和中结束了听证会。我站起身来,向着原告律师走去,屋子里的每个人停下手中的事情,把头转向我,眼里是“你这是要干什么?”的疑惑。我抢上一步,握住了原告律师的手,面含微笑地说:“谢谢你,我今天学到很多。” 他个子很高,低下头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尬笑,一脸的懵懂。我们回到律师事务所,同行的美女律师助理进门就对同行们说,吴医生今天结束时握了对方律师的手,还说谢谢他。又引来一阵尬笑。我估计他们都不解我为什么要感谢原告律师,其实我是真心感谢所有的律师,他们让我看见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给我上了一堂美国式法学大课。一群衣冠楚楚代表正义的精英,匍匐在五百万美元面前,以法律神圣的名义,以无可辩驳的四个疑问句,慷慨陈词一个不存在的事实,我当时在心里已经笑喷了。在大家的欢笑声中,律师带我去了一家豪华的餐厅,微醺中谈笑风生。
回到酒店,我突然感觉坐立不安,一股凉气袭上心头。一天下来接触了太多的信息,在一群衣冠楚楚的律师的包围之下,我得到了什么?思绪慢慢地恢复,每一条线索结果都指向我的未来,我的家和我的女儿。我想起在匹茨堡时无数的不眠之夜,想起家乡南京的老母亲..... 我从烦躁中渐渐平静下来,摸了摸口袋里的上上签,脑中出现一条清晰的结论,我要翻案。
我当即电话律师:“你们今天没有保护我,但我保护了你们。” 我继续说:“我按照你们昨天的设计,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但这不是整个案件的真相。” 律师不说话,于是我又说:“如果你们不能让我出局,我明天就去对面的大楼说出一切。” 电话中的律师显然有些意外,他说:“这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样吧,我们明天早晨再谈这件事。” 我感觉律师有些激动。
第二天一早,事务所的老板和我的律师同时出现在一间圆形的小会议室里,屋子的中央有个小圆桌,头上是钻石形状的玻璃拱顶,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我们的辩论进行了三个小时,问题的关键是马里奥医生那天究竟在不在匹茨堡?而我的书面证词写得明明白白,是我没有打电话向马里奥医生汇报病情。二位大律师和颜悦色地告诉我,我推翻我自己证词的危险后果,最坏的结果可能要坐牢。而且我也无法证明我的翻案就是事实,因为病历上没有记录。我不但写了书面证词,昨天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了事实,这是一个铁案。
“那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五年前的证词吧。” 我说。我开始朗读那一页即将毁灭我一生努力的小纸片,两位大律师静静地聆听。读完后我问了一个问题:“二位觉得我的英文水平有这么好吗?” “请问我把我的过失写得这么清晰、详尽,动机是什么呢?我有这个必要吗?”
律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自问自答:“显然,这是有人写好了证词,诱导我签字的。” 我陈述了当时的情境。
“你签字了,这就是法律文件。”
“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一天马里奥医生究竟在天上还是在地下吧?” 两位大律师静静地聆听。“那一天根本就没有主治医生查房,马里奥医生在哪里呢?”
“病历里所有的记录都有他的签字。”
“他可以事后签字啊。”我没能说服二位律师,焦急中我说:“那天马里奥就在天上。”
“可是你不能证明你说的话。”
“我们可以查那天晚上在迈阿密确实有大聚会。”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还可以查航空公司的飞行纪录,一定有马里奥的名字。”
“这么多年了,航空公司不会保留这些资料这么多年。”
我当时也不清楚航空公司是如何保留飞行纪录的,但我还是说:“航空公司一定有马里奥的飞行纪录。”
我又问:“为什么移植科主任不承担任何责任呢?我打电话给他了呀?”
“病人喜欢他,没有告他。”
“那做腰穿的两个医生为什么也没有被告呢?”
“他们是学生,受到医院的保护。再说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延误诊断。”
我们又回到问题的焦点,马里奥是否在天上的事。我说:“这件事一定可以查清楚的,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事故不公平,我不可能接受。”
两位律师开始宽慰我:“儿童医院将承担大头,你那时是fellow(学生),只在这个案子中承担一小部分责任。” “保险公司负责赔款,不会影响你的任何利益。” “你还是你,你可以继续你的外科医生生涯。”
我没了退路,开始了最后一搏:“我前面已说的很清楚,那份证词是马里奥写的,我是在他的诱导下签字的,我为朋友签字源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里奥那天在天上的事实,除了在航空公司可以找到记录,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人证,前一天晚上在迈阿密的许多医生是我的朋友,他们也是人证。
两位律师面面相觑,还是不置可否。我想他们也许昨晚已经庆祝了他们的胜利,不是不settle(调解)这个案子,而是放出一个当年的访问医生,保住了主治医生和主任,也许已达到了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是一门生意。
我在走投无路之下,放出了狠话:“你们如果不让我出局,我现在就去隔壁把马里奥在天上的事说了。”
两位律师对我的话没有反应,于是我又说:“你们前天为我准备听证会的目的,就是要我接受你们编好的故事,让我承担全部责任。你们教我的问答技巧,就是企图Misleading(误导)我的一部分。” 我惊奇我经过三天的美国法律的熏陶,已开始运用法律术语了。
我又加强语气道:“我想告诉二位,如果今天下午我去隔壁,你们二位将因为伪造事实而失去律师执照,匹茨堡大学将赔偿更多的钱。”
两位衣冠楚楚的律师笑起来,事务所的老板没有犹豫,他站起身来,笑容可掬地向我伸出手来,说:“你赢了。” 我记得那是中午时分,钻石玻璃房内阳光灿烂。
我当天就回了爱荷华小城。第二天傍晚律师从匹茨堡打来电话:“恭喜你,此案与你无关了。”
我又去请教爱荷华的法律教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起了法律。教授大约六十多岁,穿着黑色的西服,领子上系着红色的领结,墙上是许许多多的证书。我告诉他我在匹茨堡的经历,他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我隐约记得他说我没按常理出牌,也可能匹茨堡的律师轻敌了。后来我想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不按常理出牌,我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牌,比如我天真的要为朋友两肋插刀,自诩关云长义薄云天;比如我起先天真的相信律师就是拿了钱为我消灾的;比如我觉得既然律师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感觉这是一种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而教授接下来的分析则让我对许多问题顿开茅塞。他说医疗事故的案子属于民事诉讼,99%都以和解结束,由保险公司买单。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当然是花的钱越少越好,而律师就是保险公司雇佣的经营这单生意的商人。我在这单生意中保护了他们的软肋,但在他们出卖我的前提下,我又要卖了他们的软肋,如果软肋暴露出来,那么这起事故就不单纯是个医疗疏忽的案子,而是一场责任事故,原告就可以予取予求。“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只能让你全身而退。” 教授看着我的眼睛说。
我刚来美国时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匹茨堡的每一个人都是“劳动模范”呢?Dr. Starzl似乎从来也不需要做任何人的思想工作,这个看起来一盘散沙的群体,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所有人捏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美国的体制建立在个人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只要上升的通道公平的开放,不怕小医生不拼命。这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冠冕堂皇的道德制高点和规范,都与金钱有关,法律诉讼也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
我在爱荷华度过了匹茨堡的一大危机,来年升任了外科副教授,又过了一年,担任了移植中心主任。这个案子之后,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起移植法律诉讼的专家组成员。这是美国南方的两家著名医院,在做亲体肝移植中搞错了父亲和母亲的ABO血型,导致移植失败和病人死亡。这件案子的成功法律诉讼最终使UNOS*改变了器官捐献中的许多规则。我也因此成为美国移植诉讼案炙手可热的专家之一,对手都是美国最知名的移植专家,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我参加过的案件居然没有输过。多少年之后我从爱荷华法律教授当年的话中悟出了道理,我担任的都是原告的专家,赢几乎是一定的,只是赢多少钱而已。
04 阿肯色探险
日子一天天过去,危机也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我经历了无数的危机,没想到美国社会也这么复杂。后来我总结了一条自以为是的规律,钱越多的地方,就越复杂。在结束这篇“危机”的短文之前,我想再讲一个危机的故事吧,因为那段经历真的让我刻骨铭心,颠覆了我的三观。
二零零四年,我在对美国南方极大好奇心的驱使下,辞去了爱荷华大学稳定的工作,去阿肯色大学创建肝移植中心。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这里已是朝九晚五,工作失去了激情。” “阿肯色的中心将是美国最后一个肝移植中心,那里条件比较差,经历了十一年的努力也没有建成,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好机会。”
我去阿肯色之前,Dr.Starzl来信说:“我将非常有兴趣看你在那里的探险。” 他的这句话不但没能让我止步,却让我加倍地兴奋。许多年后我在“午饭”中与Dr. Starzl谈起此事,他笑着说:“吴,你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不过我很高兴,你又打回来了。” 他是说我又打回了纽约,身体中又充满了激情。

阿肯色移植中心的发展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这个项目是医学院新科校长的五大目标之一,支持力度特别大。我第一次见校长,他让我先阅读他的五年规划,然后告诉我,外科主任佩琦教授浪费了他三年时间。我又去见佩琦教授,他说他被移植科主任三百页的简历骗了,他不会开刀。医院毫不犹豫地开除了移植中心主任,他是被四个彪形大汉押解出医院的。那天我在手术室开刀,出来时主任办公室已是人去楼空,连办公室的家具也搬空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校长对我说:“阿肯色不仅需要你来当肝移植的主任,还需要你来领导整个移植中心。” 秘书带着我去了家具店,让我选一套自己喜欢的家具。州政府保险公司(Medicaid)的领导特意送我一幅无比喜庆的中国年画,金娃娃抱着黄河大鲤鱼,让我哭笑不得。我去走访阿肯色各地的医生,州政府保险公司会租一辆加长的林肯豪华轿车,远一点的地方,直接派专机接送。
一天,外科主任佩琦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在这个科,没有人可以越过他直接去见校长,否则就不会有工作。” 我懂他的意思,回答说:“没有问题。” 第二天,校长又打来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谈谈移植的事情。我说:“对不起,佩琦教授刚刚宣布了他的原则,我不能单独见你。” 校长说是急事。我说不。院长又打来电话说:“过来吧,我担保你没事。万一佩琦教授问起此事,我可以证明是我们要你来的。” 我在忐忑不安中去了校长办公室。半小时后接到外科主任秘书打来的电话,让我去主任办公室一趟。我是带着院长的尚方宝剑走进主任办公室的。当秘书关上办公室大门的瞬间,佩琦教授温怒地质问我:
“你去了校长办公室!”
“去了。”
“你不记得我的原则吗?”
“记得。我告诉校长你的原则了。”
“可你还是去了!”
“是校长和院长强迫我去的,他们说他们会向您解释。”
佩琦教授涨红了脸,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叠文件,朝着我的方向向空中摔出去,纸片在空中飘飘洒洒,又落了满地。
“My word is my bond.” (我说话算数)佩琦教授大发雷霆。我站立在偌大办公室的正中间,面对外科主任的咆哮,沉下脸说:“佩琦教授,你必须对你今天的言行负责。” 我一扭头出了主任办公室,把电话打到了院长办公室,汇报了刚刚发生的情况。十五分钟后,我和佩琦教授坐在了校长办公室里。校长说:
“佩琦教授,你必须向吴道歉。”
“对不起。” 佩琦教授说。他看我没有反应,又加上一句说:“我都道歉了。你还要怎样!”
校长说:“今晚我请二位吃饭。” 我和佩琦都没有说话,校长稍停片刻,又说:“请二位takemy rain check,(接受我的预约)今晚我已有约,改日再请二位吃饭。”
此事过后没多久,我接到外科办公室的通知,面试来自蔓菲斯的移植医生,他是来面试移植科主任的。那个医生我们原来就认识,他后来为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做了肝移植手术。我们俩见面时都忍不住地笑,握手后我开门见山:
“你知道是我建立了这个肝移植中心,而且保持着百分百的存活率。” 他点头。我又说:“请回吧,我是不会让出我的位置的。”
他没有说话,我们二人站起身来又握手,两人的脸上都泛出微妙的微笑。
后来我听说校长告诉外科主任:“只要我在这里一天,吴就是移植科主任。”

半年之后,阿肯色大学医院获得了UNOS的准许,做了阿肯色州的第一例肝移植。两年之后,我们以肝移植术后百分百的一年存活率,和移植后平均住院五天的结果,通过了美国联邦政府保险公司(Medicare) 的现场验收。验收的官员是我在匹茨堡时的同事,他在评语中写道:这个中心出类拔萃,甚至比美国最好的移植中心更好。我也在那一年被评为阿肯色美国最佳医生中的最佳。六年以后,阿肯色大学的肝移植以95%的三年存活率,获得全美肝移植九佳中心的第一名,至今这仍是美国肝移植的一项纪录。从此,阿肯色的病人不需要去外州做肝移植了,州政府的官员对我说:“不管你花多少钱做肝移植,这钱还在阿肯色。我们投资一美元,联邦政府就补贴我们阿肯色一美元。肉烂在锅里,钱越花越多。

阿肯色大学医院肝移植医生、护士与麻醉师在模拟肝移植手术后合影

二零零五年五月,阿肯色第一例肝脏移植病人在术后第四天参加记者招待会
鲜花与掌声有时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肝移植是个新项目,我们只有两位协调员,但这两位护士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资深护士。一位来自英国,她在与我一起工作之前,是监护病房的护士长。另一位来自东部,她来之前已有数十年肝移植协调员的经验。两个人轮流值班,没有移植时她们夜里在家待命有每小时两美元的补贴,如果有移植,她们的加班费按正常工资的一点五倍算,再加上她们的基础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医院里的任何护士。美国护士买了一辆红色敞篷跑车,英国护士买了一辆悍马吉普车,来自中国的我换了一辆S级大奔。中午肝移植的员工去餐馆吃饭,浩浩荡荡。肾移植中心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和七位护士,集体提出要平均分担肝移植护士的值班,我和移植中心的行政总管与肝移植护士协商未果,这件事就拖下来了。

我的美国与英国护士
第二年保险公司又要来检查,移植的数量增加了,文件当然特别多,两位协调员每晚加班准备汇报材料。移植中心的行政总管是这个科的老人,她告诉两位肝移植护士,如果数据有错误,中心有可能被关闭。两位护士更加夜以继日。
检查团来了,他们不吃医院的饭,也不同移植科的人谈话,埋头检查文件。到了第三天,他们与全科的医生护士开了一个晨会,大体是说中心的工作是规范的,但发现了一些数据错误,比如肝移植对肝癌大小的描述不准确,发现一例与原始数据不符,把2公分的肿瘤写成了2.1公分,他们还发现原始病历有涂改的痕迹。
过了几天,这份2.1公分肿瘤的报告上报到了医院领导,一位资深副院长亲自来到移植科调查此事。我告诉他,2公分的肝癌与2.1公分的肝癌在临床上没有区别,如果是1.9公分区别就大了,这与肝癌的分级和肝脏的分配有关。我请来了放射科医生解释此事,他说其实肝癌也不是真正的圆形,换个角度测量就可以有几毫米的误差。会后我听说副院长对放射科医生的解释很是不满。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移植科又恢复了往日的常规,我不时地提醒两位护士:低调、低调。她俩哈哈大笑。
一天我又在手术室开刀,出手术室的时候已是下午。秘书急匆匆的告诉我,今天早晨你手术的时候,那位副院长召集了移植科大会,宣布开除两位肝移植护士,罪名是篡改原始病历。两位护士不服,坚持要等你来了再走。可你在手术室开刀,最后医院的保安强迫她们离开了医院。
我回到办公室,又是人去楼空,这是第二次了。这两个护士是阿肯色大学成就全美最佳肝移植中心的主要功臣,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们呢。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走动,每个人似乎都很忙。移植科行政主管来到我的办公室,解释了两位护士被医院开除的原因。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大家心照不宣。
我出了移植办公室,直奔校长办公室。校长坐在他的大摇椅上朝我微笑,我也不铺垫,直接抗议医院开除了我的两位护士。
“两公分的肝癌与2.1公分的肝癌没有区别,这是陷害。”“我早就知道这帮老人都嫉妒这两位护士。她们要求分享肝移植的加班费好长时间了。”
校长不动声色,他还是看着我微笑,听我陈述。短暂的沉寂后,校长说:“既然法律已经介入,就让法律来解决吧。” “法律铁面无私,以事实为依据,它只确定是否违法,并不追究背后的阴谋。” 我当时这样想,但没有再说话。
两天以后,我觉得愧对两位协调员,于是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慰问两位护士。
“你俩怎么样?”
“好得很!我们在弗吉尼亚海滩晒太阳呢,哈哈哈......” 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
我在笑声里从沮丧中缓过一口气来,跟着二位护士也嘿嘿地笑了起来,刚挂了电话,又陷入了莫名的沉思中。我突然想起了Dr. Starzl对我说过的话:“我将非常有兴趣看你在那里(阿肯色)的探险。” 我在一瞬间懂得了Dr. Starzl“探险”两个字的含义。
医院在第二天就招来了新的肝移植协调员,看来早有准备。肝移植夜班也由全科护士轮流值班,虽然肾移植的护士对肝移植不太熟悉,但训练一下,也是能够胜任的,只是我更忙了。由于肝肾移植统一值班,医院节约了一笔不小的经费。
这件事让我对美国文化有些失望,不就是加班费吗,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但我看到两位护士似乎对失去工作云淡风轻,她们在尽情地享受闲暇的时间,然后再找一份相似的工作而已。
几天后,我在郁郁寡欢中走进医院政府关系部主任的办公室,因为我的肝移植支持委员会中有前任州长和现任参议员,还有几位本州的超级富豪。我看见主任硕大的栗色办公桌旁矗立着星条旗,桌后一幅巨大的油画扑面而来。

作者与州参议员
我记录了我那天的感受:“油画只有一种颜色, 浅蓝,只有一根劲草,疾风中卑躬。不解,问寓意如何?曰:做人如小草,任八面来风,随风摇曳,立不败之地。沉思良久,唏嘘。传说中的墙头草嘛,风骨呢?
接下来的事,让我目瞪口呆,我的美国护士二十岁的独生女儿自杀了。传言她是因为她妈妈失去了工作,又离了婚,不能像以前那样满足女儿在金钱方面的要求...... 在追思会庄严肃穆的管风琴音乐声中,我看见肝移植与肾移植的护士又抱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露出圣洁的表情,她们在二十岁花季少女的遗像前,右手食指在胸前不停地画着十字,或是双手抱拳、低头沉思,她们在庆祝少女短暂而幸福的一生,她们嘴里念念有词:阿门!愿你在天国永远幸福,幸福永远,哈利路亚。
所有的匪夷所思让我眩晕,我想这是来自我自己的原因,是我还没有真正融入这片土地。美国是法制社会,在法治的框架下,人性中的恶无所不在,钱是这块土地的灵魂。在这个国度里,只有财务自由才有肉体与灵魂浑然一体的自由。但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缺乏心流的挣钱,会让心很累。我还是个无神论者,对宗教一知半解。在这块土地上,也有印度赫尔德瓦尔的恒河,只要勇敢地跳进去,灵魂的腐朽会在甘露中化为神奇。肤浅的人把宗教当作迷信,求些现实的结果,逃避内心的罪恶。圣徒也是想用宗教解决问题,只是那是一个无可逃避却无可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困难得多,也高级得多的问题,它没有现实的手段可以使用,它靠的是艰苦的玄思和坚定不移的信仰。
05 后记
几年过去,移植科已成为医院的招牌,妥妥的摇钱树。医学院校长辞职去了马里兰大学担任了大学副校长。他在那里又去匹茨堡招兵买马,建立起了美国第一流的异种心脏移植中心。二零二二年,马里兰大学的猪到人的心脏移植在全世界大放异彩,校长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美国的各大媒体上。校长临走前兑现了我的合同,继续我爱荷华大学终身教授的头衔。分管教工的副校长戏虐地对我说:“这很重要,你以后只要不杀人放火,就没人能够动你。” 我想起爱荷华大学一位领导说过的话:我们要谁走,就让他难过,比如减点工资什么滴。
外科主任没有兑现合同中的奖金,并且说:“Dr. Wu, 是我们把你提升到现在的高度。” 我找了律师,他们告诉我,阿肯色大学医院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他们不能得罪医院。不久,外科主任带着建立阿肯色移植中心的光环,去了一家更大的医院担任外科主任。
我写完这篇第三次危机后,告诉我的同学,我的第三次危机是灵魂的危机,是我对美国文化一知半解、格格不入的结果。他说:达芬奇在十五世纪搞清了人体的骨骼与肌肉,但达芬奇说:我没有找到灵魂。我回答:我的魂在太平洋上呢!达芬奇没有看到灵魂,于是他赋予了灵魂变幻莫测的色彩。我想起了Dr. Starzl在我来阿肯色之前对我说的话:“你还是去一个具有国际背景的大学比较好。”
不久我以全美第一名肝移植中心的成绩辞了阿肯色的工作,去了纽约。阿肯色大学医院又恢复了它的本色,一水原汁原味的阿肯色。
HealthGrades Liver Transplant Excellence Award recognized 9 recipients out of 111 hospitals evaluated in USA November 14th,2011
UAMS Medical Center; Little Rock, AR
California Pacific Medical Center – Pacific; San Francisco, CA
UCSF Medical Center; San Francisco, CA
Mayo Clinic; Jacksonville, FL
Ochsner Clinic Foundation; New Orleans, LA
Cleveland Clinic; Cleveland OH
Saint Lukes Episcopal Hospital; Houston, TX
Shands Hospital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ical Center – Riverside; Minneapolis, MN
我学着校长与外科主任的样子,也把自己卖了,卖给了全美肝移植倒数第一名的医院,我第一次在商言商、讨价还价。匹茨堡的朋友说那里危机四伏,Dr. Starzl说那里可以激发你的斗志。我又回到匹茨堡,在新建的儿童医院里流连忘返,与Dr.Starzl共进午餐,听他说他在山里小木屋的故事,从电脑里看他波兰老家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他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他最终的回答是:有。
在飞向纽约的飞机上,我的大脑中回荡着“斗牛士进行曲”,那是匹茨堡六号手术室肝移植结束时的英雄交响曲,歌声中往事呼啸,感觉Dr. Starzl就是移植世界的尼采,带着酒文化的浪漫,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意志,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风度翩翩,这是美国的灵魂;我还看见“校长”满脸的微笑,他似乎有中国道家上善若水的风范,这是美国的智慧;芸芸众生嘛,贪婪自私是人的本性,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是什么?感觉是个怪胎。如同一块东方炙热的烙铁,在西方的铁匠铺里被锻打后,又将被投进人情冷暖的纽约淬火。

花季少女葬礼上的管风琴声在大脑中嗡嗡作响,我极目远眺,曼哈顿漂浮在滚滚云层之上。飞机开始颠簸,感觉自己像一叶轻舟,随波逐流。前方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华尔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五大道购物天堂、芭蕾舞伴着嘻哈音乐,纽约是一个大染缸,纽约是一个大熔炉,哈德逊河在夕阳中泛出闪闪烁烁的金光,又在黎明飘飘渺渺的薄雾中汇入大海,潮起潮落,走向未来。
人生若无危机,岂不寡淡。岁月若无危机,何谓人生。
*OPO:器官捐献办公室
*UNOS:美国器官捐献与分配组织
外科医生英文警句:Always have a plan for the worst-case scenario.
作者:吴幼民 - 美国纽约医学院终身教授,移植外科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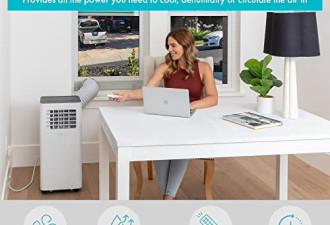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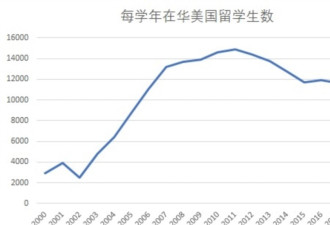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