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四次婚姻的父亲,喜寿之年在继母陪伴下离世
我父亲生于1925年1月9日,故于2001年8月11日,活了77岁,喜寿。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定数,父亲不像大多数人尤其是同时代的平民那样只经历一次新婚之“喜”,而是有过“四喜”——先后有过四任妻子。当然,他与母亲的婚姻维持最长,我曾以《贫苦一生的母亲,不是元配却与父亲结成“红宝石婚”》一文表达对母亲的怀念。父亲节前,我把父亲另外三桩或很短或稍长的婚姻也写出来,既为有兴趣研究8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状况、研究人性和婚姻问题的人提供一点一手资料,也再次表达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前年8月11日,父亲去世20年忌日,我曾以《运动——贯穿父亲悲情人生的关键词》一文表达过对父亲的怀念。
头婚:在战乱与疾病的双击下凋零
我从第二故乡调回老家工作以后,父亲去世以前,每年清明时节,父亲领我和大哥到半山腰的祖坟上祭扫完毕,下到村口路边,父亲会指着一个没有墓碑的小土包说:“这里还有一座,你们也拜一下!”兄弟俩遵嘱而行,摆上祭品,燃香烧纸放鞭炮后作三个揖,父亲则会面色凝重地遥望远方……
扫过几回墓后我们知道,那是父亲的元配之墓。与母亲借住在乡下二叔家时,父亲与元配的弟弟还偶有来往,彼此还显得很亲近,父亲当着他的面回忆起往事,一口一个“旷妹”,足见当年用情之深。
父亲去世十年后,我将他在晚年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编印成书,对他的这段情感经历也有了一些了解。
父亲与元配是青梅竹马的玩伴,“20年代末期每年春节都要在熊家铺外婆家相聚,欢声笑语不断。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属符家姐妹……1938年,她外公亲自为媒,把我俩拉到一块……”
“旷妹”与父亲一样上的是私塾,7岁起“苦读《四字女经》和《四书》《古文》等……十四五岁就能挑起百多斤重的干谷上楼进仓,她虽只读五年书……几行毛笔大字,写得苍劲有力,令人赞不绝口……”
1943年初,在桂林军校(黄埔军校第六分校)结束半年预备教育后,父亲在第十九期入学考试中名落孙山,原所在部队又“已远去云南,进入缅甸”,于是干脆当逃兵,回老家解决终身大事。

父亲与“旷妹”正式订婚以后,两人反倒变得拘谨,“以前那种爱说爱笑,嘻嘻哈哈的场面再也不见了……从军后的两年,一在天涯,一在海角,也没有鸿雁传书,互通音讯。即使后来到了她家坐馆,……不同桌共餐,不交头接耳,她为我洗洗补补,两人也没有直接接触过,总是通过她老奶奶或她的小弟弟为我们接送衣物,有时两人见了面也要想办法马上避开,或者面红耳赤,羞羞答答地擦身而过”。这“使几位老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紧筹办婚礼。于是,在“子承父业”教了一期私塾后,父亲“七月初就在她家拜堂成亲”。
父亲惜墨如金地描述他的人生三大喜事之一——“洞房之夜,却又显得亲热起来”。每每读到这里,我都会忍俊不禁,想象父亲提笔时欲说还“羞”的神态,我觉得一向不苟言笑,深沉威严的父亲此刻变成了一个可爱的老顽童。
战乱年代,美好是非常态而苦难是常态。1944年6月,鬼子来了。“首先传来令人愤慨的消息是南燕冲一名青年妇女被扫荡的鬼子当作活靶子一枪命中,倒在洗衣的脚盆边,血流如注,当场毙命,她家里的人还不知道,而鬼子却哈哈大笑,一溜烟跑了。消息传到各村,立刻引起极大震动和不安。接着第二天上午又传来XXX的大儿子被鬼子的刺刀捅死,肠子都流了出来,尸体丢在他屋门口的水塘里。随后又传来几名妇女躲在山上茶树下,也被扫荡的鬼子搜了出来强奸……”
那时“旷妹”刚为父亲“生下第一个小宝宝”,父亲刚尝到初为人父的欢喜,第三天就传来县城不幸沦陷的消息,“一夜之间她就由产妇变成了难民,带着婴儿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逃回娘家避难。不久凶狂残暴的鬼子像是有意与她作对,时刻进行骚扰,使她寝食不安,立足未稳,就随我不断地转移,四处漂泊,过起了逃亡生活。”
“六月下旬,我们由宋家岭被逼上唐家岭时,她因产后未能很好休养,加以营养不良,又长期奔波,担惊受怕而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被她的父母接了回去,住在唐家岭附近一个破纸槽里。这时兆厘也饿得奄奄一息,没有跟娘去外婆家,在缺医少药和缺奶的双重困境中”,“生下来只活了69天的兆厘,七月初六就离开了我们,莲昌闻讯,病情雪上加霜……”
抗战胜利后,父亲一时无处谋生,只好把上街瓦屋略加装修改造,成了小铺面,夫妻双双在这里卖米豆腐,这种生意本小利微,但也算解决了我们的基本生活。可这时病魔又一次缠上了她,十月初,她开始由感冒转伤寒,继而成了霍乱,上吐下泻,急得我四处求援,借钱借米,为她求医煎药,还请来道士为她驱邪逐鬼,烧纸许愿。然而这些举措都挽救不了她的生命,几天之后,她就病得把腹内的小孩流产。我父亲看她已病入膏肓,怀着好心几次劝我俩从上街搬回下街老家……十月二十日深夜,也就是我俩从上街搬到下街的次日晚,她的病情果然急转直下,终因医药无效而与世长辞,时年不足二十二岁……”
这桩婚姻,时长27个月。父亲这样描述他的感受:“与我同甘共苦的妻子,竟然突然离我而去,令我痛不欲生。如果不是战火的摧残,不是鬼子的长期侵略,她哪能猝然撒手人寰,使我像只失群的孤雁。国恨家仇,一齐涌上了心头。”
三婚:“她没有给我半点温暖感”
1989年中元节,是母亲去世后第一个祭祀的日子。我们兄弟姊妹在乡下老家祭奠完已故亲人,大哥把父亲接到城里自己家照顾。
大哥此举,出自孝心,却勉为其难。他家那时住的是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工厂自建家属房,大哥大嫂,侄子侄女,加上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大嫂之母,本已拥挤。父亲“晚上在客厅里打开沙发就成了床铺”。
比起生活的不便,孤独寂寞大概让父亲更感难以忍受。实际上母亲去世后没多久他就或明或暗地向哥哥姐姐和我透露过想再找老伴的心事,四个子女没有一个人反对他动这个念头,只是哥哥姐姐一致认为我的婚事比他的婚事更迫切一些,毕竟这也是母亲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事,她虽然已见过我的女友一面,却不知道会不会成就姻缘——那时我与女友相识也不过十余天,所以哥哥姐姐都劝他,在我解决了终身大事后他再考虑,父亲对此倒也没有表示异议。
世界需要热心肠,世界不乏热心肠。父亲从乡下住进大哥家后,左邻右舍既见过父亲在小院或街头彳亍独行的背影,又听说他有续弦之意,“顿起恻隐之心,愿为我搭鹊桥”。一家二轻企业的一名退休女工就这样闯进了父亲的生活。1990年元旦我结婚,此后两三个月,父亲“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结婚后我就把家从乡下搬到了南街,向居委会租了一间公房,在这里‘安营扎寨’,度过晚年”。
可惜的是,父亲虽然社会阅历非常丰富,饱经沧桑,且已有过两次婚姻经验,对包括自身弱点在内的人性弱点及婚姻的实质等认识远不够深透,以至于婚后不久他就觉得,这场多少显得有些仓促的黄昏恋给他带来的痛苦感远远强过幸福感。
退休女工小父亲七八岁,一年前刚离过婚,与当乡村医生的前夫育有四个女儿,头两个已出嫁,最小的跟她生活,那时还在读中学。她的退休工资不高,家里经济负担较重,她显然希望能从父亲身上获得多一点经济援助。
但她或许高估了父亲的经济实力。六口之家,曾经长年都主要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何况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常要吃药开销,因此父亲并没有多少积蓄。另外,一辈子过紧日子惯了,父亲对钱看得很重,无论对人对己都很抠。姐姐困顿时向他借过一回钱,过了不太长的时间父亲就催她还,以至于姐姐至今都耿耿于怀。
家庭重组后,柴米油盐之类的日常生活支出是由父亲负担的,细至每天买点白菜萝卜,他都记着账;但非共同生活开支,比如对方买衣物等,父亲大概不出或很少出。彼此都觉得义务与权利不够平衡,矛盾便产生并不断加深。我偶尔上门,看到过以前极少做家务的父亲“亲自”洗衣,看到过“一对沉默寡言人”……
父亲在回忆录中如此反思这桩婚姻:“结婚后,她没有给我半点温暖感……洗衣做饭,我不自己动手,则食不饱衣不暖。她在经济上则时常冷言冷语,纠缠不休,不到一年,她提出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期待她回心转意,但她不为所动,我自愿赔偿她500元经济损失,满足她提出的离婚条件,她终于第二次走上法庭履行离婚手续。”
四婚:46年前的数面之缘成就最终姻缘
1992年春节后,父亲回乡下与叔叔团聚话家常,二叔二婶得知父亲重归单身,遂为他“穿针引线,再架鹊桥”,介绍他与一名五年前丧夫的村妇S相见。S丧夫后不堪儿媳虐待,有改嫁之意。
缘分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两人见了面粗略一聊,发现彼此竟是46年前的熟人。
1946年春,经历了丧妻失子的父亲外出谋生,在洞庭湖边的一个县教了半年私塾,学生中就有S的未婚夫和弟弟,“并在她家做过客,端午节后去她家吃过饭”,父亲对她的印象是“聪明能干,热爱劳动,礼貌待人”。1952年当地遭受特大水灾,已结婚四年的S随丈夫回到其老家,与父亲的老家“近在咫尺”,只不过此前父亲“一无所知,不知道四十多年前的学生在我身边”。
双方原就有一定了解,又因晚年近在咫尺对彼此的为人处世和家庭状况容易打听,认可并愿意接受对方,因此一拍即合。S的一儿两女,我和哥哥姐姐也都同意这桩婚事,当年中秋节前11天,S成了我的继母。
父亲再立新家后不久,带着继母旧地重游,回他工作了35年的那个湘南小县探亲访友,被安排住进了县税务局的“内部招待所四楼,一室一厅客房,厨房厕所等设施齐全,有阳台走廊,窗明几净,空气清新”,小哥和姐姐又送去各种生活用品,令父亲“一时感觉心情无比舒畅……像立刻到了‘天堂’。早晨天未大亮,我们就披衣起床,开始一天的步行锻炼,绕着环城新马路步行一圈后才回来共进早餐,有时下面煮粉,有时进店喝粥,白天或与老同志一道走进门球场参加门球运动,或走进那条古老的十字街与乡亲父老促膝谈心……”
1993年底,父亲和继母返回老家,在离大哥家三四百米远的“县电力局对面租了一间民房,每天有成琳和成琦姐弟俩从门口经过,他们是去城关中学和城西完小上学的,每次路过,都会向我问候,使我倍感骨肉情深,家庭温暖和老年人特有的幸福,显得特别愉快……”
一年半以后,父亲和继母又把家搬回乡下,向小叔租了两间楼房住。父亲“每日里锄园种菜或吟诗写字,或在江边独钓,借以消遣度日,社会上那股牌赌之风盛行,但我绝不参与,上对得起父母在天之灵,下对得起儿孙”。
无论在哪里,继母对父亲的饮食起居都照顾得很好,让他在母亲病重去世后重新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我也从未听说她打听父亲的钱财或向父亲索要物质享受之类,她在农村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对父亲也很好,逢年过节自不必说,平时也会送上一些鸡蛋、鸡鱼及诸如自酿米酒之类的土产,开启父亲的“开心一刻”。父亲虽然处理人情世故方面的经验十分匮乏,多少也知道适时“投桃报李”。
上世纪末我以亲戚名义在城西完小购买了一套无电梯的集资房后,父亲与继母不愿随我住六楼,他跟大哥将我的车库略加改造,隔出前后两间,与继母住了进去,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
2001年8月10下午将近下班时,我在单位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获悉父亲摔倒昏迷了。我立刻请单位的司机开车送我回家。
原来,父亲在门前锯一根木条时突然栽倒在地,继母一时慌了神,知识的局限让她采取了雪上加霜的措施,她以为是中暑而不断地对父亲人中、手等进行掐刮,见毫无效果后才赶紧去告诉住得不远的大哥……
刚进县人民医院时,医生问父亲姓名、年龄等情况,眼睛始终闭着的父亲还能准确地回答,等做过CT等检查出来,父亲对医生的提问已没有了反应。医生看看片子,又掀开父亲的眼皮看看,说父亲脑溢血,颅内已有大量积血,完全没法抢救了……
父亲被输着氧气送回车库。电告远在湘南的姐姐和小哥后,大哥又匆匆赶往乡下。第二天早上,在大哥领着小叔赶到前,父亲已在我与继母的陪伴中安详离世。
父亲本意是要在百年之后陪伴在母亲身边的,但母亲去世安葬后旁边那一小块地没来得及垒一座假坟就被别人占了,他最终也就只能长眠在位置稍下的另一处地方了。
落葬的那天,继母送父亲上了山。据说,按老家的习俗,这是表明心志——此生不再婚;否则,丧夫之妇是不会上山的。
父亲没有任何“不动产”可以继承、变卖或瓜分。遵从父亲早已写好的遗嘱,我们将包括父亲丧葬费在内的所有积蓄平分成五份,四个子女及继母各占其一。
此后继母回到农村与儿子同住。我一家三口后来若从浙南回了老家过年,到乡下拜年时也总会去看望她。那一刻她总是难掩激动,眼泛泪花拉着我的手不住地念叨:“我享了你爸爸的福,享了国家的福……”
如今,继母已是94岁的高龄老人,想必还如去年春节见到她时一样身体健朗思维清晰。我相信,这一定也会是天堂里的父亲乐意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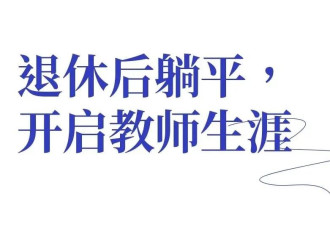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