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滂沱,想起这一生的流放和疤痕
夏天的长沙太热,所以我决定回岭南去避暑。顺便看看故乡的云,走走这半生曾行过的路。
沿着萌渚岭由湘入桂,天色已黑。经过故乡时,那座小村庄已经被暮色吞噬,我只是从路边一座影影绰绰的山梁判别出,这是我的故乡。
瞬间想起海子那首诗《亚洲铜》。祖父葬在这里,曾祖高祖葬在这里,自从先祖从广东梅州逃荒来到桂东北,他们一代又一代,在这山沟穷尽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
我驾车像蒲公英一样滑过,不曾惊扰他们。
目的地是小姑家。我上一次来是80年代,是中学生,归来已是半百中年。
小姑准备了白切鸡、烧鹅和扣肉,以及客家豆腐酿、葫芦瓜酿、辣椒酿、茄子酿,正中我胃里的乡愁。她刚当上曾祖母,于是6岁多的流氓猴居然荣升表叔,他好开心,在庭院里不停做侧手翻,逗得7个月大的双胞胎表侄们咯咯笑。
深夜,和小姑聊家族往事。她说起我的曾祖父,是个遗腹子,高祖母生下曾祖父之后,孤儿寡母被族人欺负,想尽各种手段撵她回娘家。高祖母非常硬气,就是不走,也不改嫁。有次婆家人的墙砖掉落,里边夹藏的几枚银元滚落到她家这侧,高祖母拾起银元,原样夹回墙砖里,然后告诉那些凉薄龌龊的婆家亲戚:我不占你们分文便宜,钱在这里,你们拿回去,莫要诬我图什么才呆在你们刘家。
高祖母生于道光年间,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号,殁于民国。我从族谱上推算,20岁的她在光绪年间嫁到刘家才一月余,便成了寡妇,但高祖却留下了血脉,亦有了我们这一支。这个晚清的山地女子,倔强刚烈地扛起了所有尘世悲苦,守了一辈子的寡。我多么想知道她的名字。但我只知道她唤作李氏。
那夜,开了10个小时车的我,和年逾古稀的小姑,聊到凌晨两点多。
翌日早晨,我们继续往南宁赶。小姑往我们车后箱塞了好多她亲手做的粽子,还有水果。满头白发的她和我们挥手道别,我心里忽然被割了一下。
两年前的早春,母亲病危,小姑抛下家里的所有事情,去南宁照顾陪护。当我神情恍惚地坐在救护车上去医院办死亡证明时,是年迈的小姑在给母亲换殓衣。只有最亲的人,才会在生死关头和你在一起。所以,那年办完后事,我送小姑到南宁琅东站的闸口,望着她的背影,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按照故乡习俗,我本应在母亲过世后逐一拜访亲戚,但这几年疫情阻隔,我时至今日,才终于去看望小姑。算是还了心债。
从贺州的小姑家返南宁,要经过故乡钟山,我特意不走高速,想去看看当年的城,当年的路。
车过钟山县羊头镇时,我想起了童年时一个内向寡言的小伙伴,我们小时候总在一起玩,他姓何。有年暑假,他随父亲回羊头镇,在河里溺死了。40年过去,不知道他投胎到哪里了,但愿他能开朗奔放些才好,别像前世这般,腼腆得跟小姑娘似的。
羊头一带,风景秀丽,我却不愿停车拍照。一直在苦苦回忆小伙伴的名字,但我却想不起,终究是老了。
直奔我的母校钟山中学,想让娃看看老爹成长的地方。门卫却拦住,说外人不可入内。我淡淡一笑,打转方向盘便走,你既冷漠,我亦无深情。
于是去重温了我的童年。此处曾是钟山一中旧址,如今改成了钟山公园,还起了个漂亮的名字叫状元峰。我旧时在山脚平房住了10多年,也没听说这地方出过什么状元。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钻的山洞。流氓兔和流氓猴起哄叫我再爬一次,我说哪怕你们去钻都会卡住肚皮,我们那代人吃不饱,才能穿山越岭。你们营养太好,脂肪太多,配不上这山洞的直径。

从山上俯瞰远方,正前方红色屋顶处是我的小学母校。当年曾经叫钟山一小,如今叫特殊教育学校。有时我看着镜中双目无神表情呆滞的自己,觉得确实是特殊教育学校出来的特殊校友。
我是时代的傻瓜。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惟一唏嘘的是这蔸竹子。它就生长在这里,就生长在我住的平房后面的二十米处,童年时我们把它削来作枪,填上野果互相射击。
几十年后,它仍然在这里,像尘世间的凝望与守候。仿佛前世的情人。
童年的我曾枕着雨声入梦,梦入远方。它总陪着我。如今我在几千里之外,它依然站着,让白发的我,归来时能寻见旧人。

望见旧时山河,总是欣慰的。
驾车穿过县城,每条街都是记忆。
朝西北去,正是我当年上大学的路。
记忆中有接天莲叶的十里莲塘,有骨骼清奇的俊俏山峰。但三十年前的我无心欣赏,只觉得全是穷山恶水,我总是默默地在长途大巴上想着心事。
桂东北一带喀斯特地貌太多,我们打小就看腻了。
只有在中国大地游荡了几十年,回头再看,才发现这山还挺水灵的。
我停车拍了几张照,姿色却是一般。不如还是看视频罢。
继续一路向西,经过外婆家蒙山,拐下高速,约表姐吃个午饭。
两年前,表姐也是抛下工作和孩子,专程去南宁帮我接母亲出院,我背着母亲摇摇晃晃地爬楼梯,她肩扛手提着四五个沉重的包跟在后面。有一夜,母亲病情危急,我忽然想起连寿衣都还没准备,表姐和兔妈连夜全城去找,市中心找不到,她们一急,直接到殡仪馆附近的路段去找。
两个弱女子,在夜深人寂的时候,穿梭于一家家阴森的寿衣店,这真不容易。
母亲生前的最后一次理发,是表姐帮她剪的。
吃完饭继续赶路,经过蒙山长寿桥时,流氓兔说要去拍个照。我允了。

几十年前建这座桥时,外婆掏出了平素卖菜攒的钱捐了,照例捐钱是可以刻字留名的,不知为何,她留了我的名。
所以,我大概也算是有些关于此桥的名分罢。
在桥上眺望蒙江,望见了童年的我。

这弯浅浅的江水,我曾经摸过田螺,打过水仗。
外婆家,是个多么美好的名词。她滋养过幼小的我们,让我们知道,尘世里是有依附、有托付的。
深夜回到南宁,先去了大姑家,把小姑捎给她的东西拿过去。
大姑和姑丈都学医出身,母亲生病那些年,他们动用了所有社会资源,给母亲找最好的医院和医生,身为博导教授的姑丈在医院下班,经常送鸡汤过来,还和他的学生、主治医生一起商量各种治疗方案。
大姑多年卧病在床,却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援。
有一夜,母亲似是撑不过去了,我情急之下,拨通大姑的视频通话,大姑眼含热泪,激励母亲要撑下去,要活下去。已是弥留状态的母亲,那一夜竟然又顽强地顶了过去。我又多当了几天有娘的孩子。
那夜,是母亲和大姑今世的最后一次相望。
这个夏天,我在一天内驱车千里,见了那年陪伴我经历丧乱和疼痛的三个亲人,我深深地感激她们。世道凉薄寡情,即便是血亲,亦未必能在最艰难的时候出现在你眼前。
有人心里有爱,有人心里只有钱币。
在南宁只勾留几夜,连市中心都没去过,我们直奔南海而去。
先到安铺古镇逛了一下,尝了最著名的安铺鸡,在我心目中这是中国第一鸡。香浓滑嫩,入口Q弹,洪七公来了也要扔掉黄蓉做的叫化鸡,改啃这安铺鸡。
然后扑向湛江的金沙湾,俩娃好久没见过大海了,欣喜若狂。
花了20分钟,换上各种装备,吹好了游泳圈。结果下水才5分钟,乌云压城,风急雨骤,俩娃被海边的保安赶上了岸,都快哭了。

回到了兔妈爷爷家。上一次来,已经是新冠疫情之前,这几年,我们总惦记着来看望爷爷,有一回行李都收拾停当,准备开车了,打电话给爷爷,他却说:你们莫来,万一这边有疫情,封了城,你们跑都跑不掉。
寂寞的老人总是替儿孙着想。
6岁的二宝和96岁的外太爷特别亲,虽然语言不通,各说各话,外太爷总是疼爱地捏二宝肉嘟嘟的小脸,给玩得浑身湿透的他换汗巾。
我们都很珍惜大疫之后的劫后重逢。
兔外公见俩娃泡海水没过瘾,带我们去了吴川鼎龙湾,此处天蓝沙幼,游客稀少,海水都是深黛色的。
我们甚至在游泳时看到了水母,被浪潮推了过来,它拼命游动却无能为力,就像在俗世中身不由己的我们。
沿着南海一路游荡,我们到了珠海。
去看珠海渔女雕像。我和兔妈各骑一辆共享单车,驮着加起来100多斤的两个肉团,在情侣路上晃荡。

再到澳门游大三巴牌坊,看赌场和教堂。
澳门回归时,我才25岁。
可是当我来到这里,已经是两个25岁了。

在岭南游荡了一圈,仿佛半个世纪就过去了。
那天赶在台风来临前回长沙,路上大雨倾盆,我打着双闪,龟速跑在高速路上。岭南已在身后,正在远去。
像极了那些远去的岁月。
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这江山。这过往。这悲凉。
算是人世的馈赠,也算是岁月的文身。谁的身上,没有被现世痛扁得血肉模糊的疤痕?
我们来过,爱过,最终还是要与这时光和解。
明天带娃继续浪荡在中国的海岸线上。下一站厦门泉州,本周六周日,东海见。时间地点详见以下海报。购书链接请点文末的“阅读原文”。
爱值得爱的人,爱这白马过隙的时光,爱满天的星光。
厦门见。泉州见。长沙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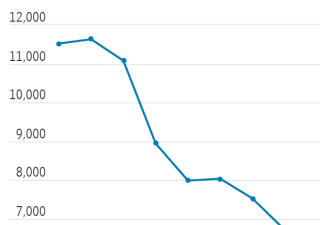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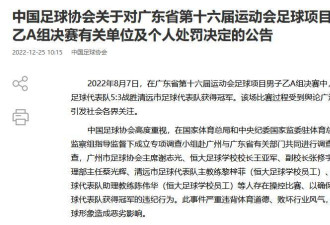

![[集市好物]EVERGREEN 雪呔](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c97a672e-e4b9-4c54-8d8b-e7015bceee43.1080x233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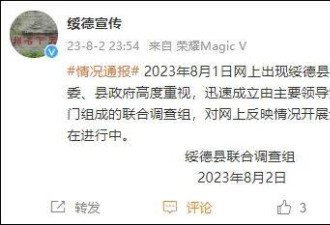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