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了,才看懂这本书里的爱情!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前段时间,米兰·昆德拉去世,首次出版于1984年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可能是他最知名的作品。这本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被翻译、引进中国,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熟知。
许多初看小说的人,都会被里面复杂胶着的关系所困惑,尤其是托马斯与特蕾莎的关系,它到底想要写什么?在小说出版40年后,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带着我们剥开层层叙事上的迷雾,去探索和发现,原来个人的情绪中暗藏着复杂的世界。情欲的“轻”与社会的“重”之间,是对于自由的本质性探讨。
01.
关系,是一种社会肯定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从公共领域,从前面很严肃的政治话题、政治处境,“哗”一下就好像转变得很“轻”了。
这两点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也可以说是“相反相成”的。这时托马斯有一种轻量化、娱乐化的游戏性的需求,跟前半部分写的“性友谊”有本质区别。
在这时,托马斯在大家眼中有点类似英雄了,他那么受欢迎,变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人。他在一户户地擦玻璃时,可以无障碍地进入各种家庭,与不同女性(产生关系)。
如果用东方视角来看,特蕾莎和托马斯两个人共同走过这么多,发生了那么多的命运关联,托马斯应该对特蕾莎特别珍惜,有一种唯一性,这可能是我们阅读时会产生的一种期待。
但这种期待,我觉得可能有问题。文学作品就是文学作品,它其实是文字结构,是符号体系,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要完成艺术上的某种表达。
托马斯在这些与不同女性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自由,当然也包括性自由。一般来说,在政治高压下,压抑、痛苦都需要释放。
要释放时,个人很容易产生问题。托马斯在特蕾莎那里,实际上很难获得释放。与那么多女性交往,其实托马斯就好像也处在了不同的社会处境里,(他体会到的)也是别人对他的肯定。
托马斯释放出来的,不是单纯的荷尔蒙魅力。他感受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女性对他的肯定,这是一种身体语言层面的共存。

书里直接写了这个问题,“他在所有女性身上找寻什么?她们身上什么在吸引他?肉体之爱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无限重复?绝非如此。总有百分之几是难以想象的。”
他用不上解剖刀了,然后,“一个女人喜欢奶酪胜于蛋糕,另外一个忍受不了花椰菜”,在这百万分之一的不同里,显示出了某种珍惜。
其实这里写了一种隐藏的东西,在一个专制体制里,要求板块化,要求同一性,要求一个声音,一个步调,一个姿态。但是托马斯追求的是差异,追求的是不同,所以这里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抗性。与那种板块化、把人削平的外部环境不同,在与不同女性的交往,体现出了一种反抗性的存在。
这是一个哲学化或者价值观的表达,这里的关键是,“百万分之一的不同才显出珍贵”。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像以前写爱情,写唯一的爱恋,托马斯与特蕾莎愈发珍惜地在一起。这样写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轻佻很游戏,实际上特别庄重,跳出肉体这样看似简单的内涵,你会发现,这里体现出更深的价值。
书后面写:“追逐众多女性的男人很容易被归为两类。一类人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找他们自己的梦,他们对于女性的主观意念。另一类人则被欲念所驱使,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的无尽的多样性。”
前者是一种浪漫型迷恋,他们总是不断地在找自己的理想,又不断失望,因为理想是很难找到的。后者是放荡型,所有女人他们都感兴趣,这是一种收集性的心态,好像有关系的女性越多越好。
托马斯身上同时体现了这两点,他“收集”了太多女性,但追求多样性,渴求百万分之一的差异,又好像指向了那种浪漫型。但这两种价值观看起来又是绝对冲突的。
所以托马斯遇到的问题在于,他好像喜欢多样性,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那种顽强的、对“非如此不可”的坚持。特蕾莎实际是他生命里的“重”,但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在面临不断的(与不同女性交往带来的)新处境里,他又渴望一种多样性。
也就是说,小说里写这个部分,没有简单化地写,不是说世界上只有这种人或是那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有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冲突。托马斯后来和特蕾莎的关系里边,也有起起伏伏。
在这个过程中,在政治模式里,也可能具有一种非常多元的又同时单极的书写。书前面写的托马斯,可能更有这种自由感、多元多样性,而他又有着另一种人性。另外一种理想。他一直想寻找这个理想,却总是寻找不到。
02.
托马斯的内心深处,有人类所有的矛盾
这种写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后来到一个女人家里,托马斯跟她想上床,人家要挡一下,这让我想起乔伊斯。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里有一篇小说叫作“悲惨事件”,展示了欲望的混乱。一篇小说写得好,逻辑就不能是很单向或很简单的。
书里有一个先生,他很寂寞,妻子死了自己单身一人,就很希望能有点艳遇。他认识了一位中年女性,这位女性很有浪漫情怀先生,看到这个女人的打扮有些野性,他觉得天然地有一种(情欲的)可能性,两个人越走越近。
有一次,女人过来拜访他,在家里谈得越来越亲切。忽然那个女人一下子抓住他的手,顺理成章的,欲望似乎就要释放出来了。没想到这个先生一瞬间,心里理想自我好像出现了。他觉得自己是个绅士,便显出吃惊的模样说,你要干什么?好像突然就竖起了一座道德的高墙,那个女人好像被震住了,便觉得很羞愧。
这位先生其实心里很想跟她发生强烈的情爱关系,结果没想到却做出了相反的行为。这里打破了前面说的分类学,所以其实人的状态是很复杂的。
这个女人后来再没出现了。乔伊斯的小说最后,隔了六年,这个先生忽然看到一个很小的新闻,一个女人在穿过马路的时候,神情恍惚,被车撞死了。他一看就发现,报道说的就是那个女人,她这些年好像不太正常,生活得越来越潦倒,越来越不成体统。
这位先生的第一反应是,幸好当年没跟她在一起,要不然多么可耻。但是到了半夜,这个先生再想这件事情,忽然觉得很悲痛,他知道一切是自己造成的。
米兰·昆德拉写托马斯也是类似,他不会因为前面做出这些选择,就走向了一条不回头的单行道。后来他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托马斯内心深处,其实有着人类所有的矛盾。
这也反映到了跟特蕾莎的关系上。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巧妙的叙事,(张力)通过从公共领域一路下来,最后又转到两位女人身上,仿佛清晰化、具像化了。

但实际这反而变得更矛盾化了,把深潜的人性又深挖了一层。人在不断地在体会生命的时候,可能就不断地陷入到更大的迷惑与迷惘中。
后来,特蕾莎想体会到一种生活的死亡感,想与那位工程师,激发一种尝试性和探险性的感觉。而当托马斯经历过约200个女人,“曾经沧海”已经那么多,心理上已经变得有点小小的畸形,很难与女性交往了。
只有在不断寻找刺激时,他才又能成为一个强者,尤其这点:“他细细察看她长满红色雀斑的脸,在上面寻找女人被绊倒在地时的惊慌神情,那无法模仿的表情刚刚将一股亢奋传入他的大脑。”
托马斯是一个被现实的政治压制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成为边缘了,那种男性的主体感、控制感、拥有感都降低了太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托马斯要通过身体来感觉到,自己还具有主导性、控制性。
所以托马斯看到对方的“惊慌神情”,就感受到了一种性亢奋。他去洗澡时,女人告诉他,怎么放热水、毛巾、手套啊,就像女人变成了母体,在照顾孩子一样。在对方的无微不至的照顾面前,托马斯感觉到了一股本能的欲望,他还是想有拥有一种自在,所以他很希望单独待在浴室里。
所以这时,他反而希望一个人呆着,而不是跟那位女性缠绵。在这里,对方可能是想通过沐浴与他更进一步接触。但托马斯不想再逢场作戏,不想再安抚对方。对托马斯来说,在已经达到情欲高潮之后,他不想再触及大脑的反应。
03.
责任,让爱变得不自由
这很有意思,诗化记忆不光是肉体性的,“它记录的,是让我们陶醉,令我们感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美丽的一切”。
托马斯认识特蕾莎之后,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到达头脑的区域,留下哪怕是短暂的记忆,所以这就推出来一种反转的逻辑,“特蕾莎暴君般地独霸他的诗化记忆”。特蕾莎的独特存在,反而极大地限定了他的自由,限制了他可能释放的身体或者精神的自在。因为特蕾莎太想跟他合为一体。
但是在托马斯身上,更广阔地说,体现了人类历史的情感状态、精神状态。人类经历过渔猎时代,也经历过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托马斯在用自身论证人的自由时,也不光是一个“文明”行为,在本能上,还有一些游牧时代的遗存,所以你看,实际上,托马斯对于特蕾莎的唯一性的追求,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自由的感觉。
在这里,这句话要仔细体会,“爱情故事只发生在做爱之后,特蕾莎发烧了”,发烧之后,特蕾莎变成了“被别人放在篮子里顺着河流漂来他身边”,一下就被神圣化了。
所以诗意记忆里有种隐喻,回应了书前面提到过的“隐喻是危险的”。这个部分也写,“爱由隐喻而起。换言之:爱开始于一个女人以某句话印在我们诗化记忆中的那一刻。”
特蕾莎在托马斯的精神世界里,有着一种诞生的隐喻和意象,形成了对托马斯的某种统治性,这种统治性不是那种强者的统治,而是通过水面上漂来的筐里的婴儿一样,是一种让人触动的同情。
但如果同情没有转变成一种深切的爱,一种共同的、深切的情感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变成一种责任、一种义务,爱本身变成了一种不自由。
卢梭在《孤独者漫步的遐想》里有一篇文章,他回家时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乞丐眼巴巴地看着他,他给了一个硬币,第二天再过去时候,乞丐望着他,他的眼神好像更加期待了,甚至变成一种压力,卢梭又给了他钱。
结果到第三天,卢梭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潜意识地回避了这条路,宁可绕远一点,这样就遇不到这个乞丐了。第四天他又这么做,到了第五天,他忽然想起来,为什么自己无意识会不走熟悉的路,才想到这个乞丐的事。
卢梭会冒出来这个意识,不是为了钱,给硬币可以,但是当你面临一个乞讨者、一个弱者,你反复给钱时,人家就会产生更高的期待,这就变成一种义务,在大脑里产生了道德强制。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自由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里,在托马斯和特蕾莎的关系中就隐藏着这个问题。书里的第13节,特蕾莎拿牛奶回来,怀里用红围巾包着乌鸦,就像吉普赛人搂着他们的孩子。
活埋半截的乌鸦,象征性是很强的,带有某种预示性,乌鸦不仅代表特蕾莎,其实也代表了托马斯本身,他们生存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这样一个卡夫卡式的专制与专横制度里,这只乌鸦显得特别无助,特别无能为力。
04.
自由的核心:可以不做什么
所以这时候,需要一个新变化,让托马斯能够体会到他和特蕾莎之间一些潜藏的部分。托马斯来到公司办公室,一开门看到一个微微驼背的高个子男人和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等着他,后者是他的儿子。
托马斯开始与他们纠缠,“这个地方不是我家”,整个环境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两个人就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们读的时候,恐怕有一种越来越接近历史的感觉,它在打开,中间有很多被触及的伤痛部分。
“记者终于切入问题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人仅仅因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被捕”,所以,“说到底,我们心想该做点什么了”。托马斯问,“你们想干什么?”
他们想让托马斯屈服,这时候儿子也出来了,说话结结巴巴的,他说现在有许多犯人受尽折磨,他想起草一份请愿书,上面有许多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签名,这或许是一件好事情。
这里出现了来自下一代的代际变化。下一代代表未来的生活,抗议的青年精神。在这里,托马斯一下迎来了另外的选择,他可能变成一个勇士。
《不能承重的生命之轻》里写的“媚俗”,就是当人投入到所谓的政治抗议里时,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正义的、所有人都应该去舍身扑入的事情。
如果说这是一个绝对律令的话,托马斯就无从选择了,因为他前面有“非如此不可”的东西。儿子说,请愿是要让大家明白,这个国家还有一群男女无所畏惧,明确表明跟谁站在一起。
儿子说,思想同样可以拯救生命。托马斯却说,你们要知道,这一切只是个误会,当年他自己写东西,善与恶的界限极其模糊,“我不要任何人受惩罚。这不是我的初衷。”

托马斯想表达,我不是一个有意识的乌托邦制造者,也没有非常明确的意识思想的阵线和壁垒。他内心的初衷,其实就只有自己对于一样事物的独立理解。
对方(包括儿子)对他的期待,逐渐让他感受到,别人想赋予他一种崇高,一种神圣。他忽然在语词构造里体会到了自己,原来自己并不是一个被赋予的角色。
记者看到他的犹豫,表面还在恳求,但语气已经变成命令式的。儿子也说,你有责任签名。一旦说起责任,托马斯就想起了特蕾莎双臂搂住乌鸦的形象。
在这里,托马斯做出了最终决定。尽管都身处这么一个严酷的环境里,但是人和乌鸦有区别。(签名)不是托马斯自己的决定,而是环境赋予的唯一决定,因为儿子和记者用外在道义,让托马斯好像只能做这样一个决定,但是托马斯内心知道,不是这样的。
当年托马斯写“俄狄浦斯王”,是出于自己的内心所愿,现在不签名。也是一种自由和自我选择所在。尽管对方的呼吁很强烈,但是,这是让人失去自由来做的行为。
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讲的消极自由。从本心上说,也许托马斯签这个请愿书,与他的价值取向并不太冲突。但是这个行为是被强制的和被命令的。在命令这个环节上,这与跟外部环境里的强制是一致的。
世界上有太多的二元对立,双方所描绘出来的,都是一种很崇高的的终极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社会却在这两极之间剧烈摇摆,很难走向统一的进步。
这往往是因为,看似对立的两极,却常常都采用一种强制的规定动作。对托马斯来说,自由的核心就在于,柏林所讲的,人类的自由,就是可以决定自己不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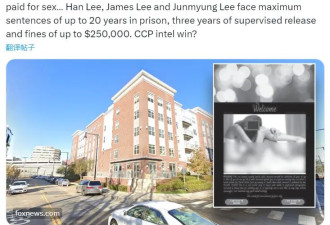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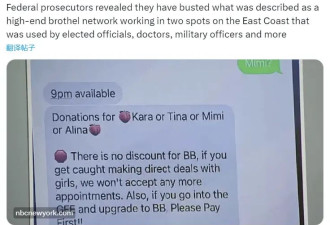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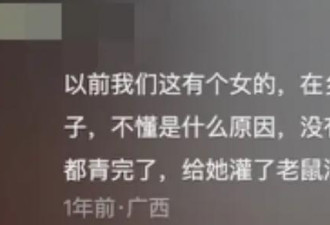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