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读博不值得?被“圈养”的中国女博士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赖逸翰
编辑 | 吴擎
回想起怀孕时那篇即将中刊的文章,林轶仍然觉得小有遗憾。
彼时,工科博士毕业的林轶,就职于某科研单位。文章本身很好,要补的实验也很简单,横亘在她面前的,只有要不要、能不能冒着风险去做个几无难度的实验的选择。
毕竟,化学试剂可能会对胎儿产生不好的影响。
“我当时很纠结,一个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一个是家庭的想法,他们不太理解我的焦虑,觉得我该切换角色了,没有什么事情比小孩大。”
时年34岁的林轶很清楚,这篇文章实际代表着她的科研最佳时期,只要发出来,她的工作肯定能更上一层楼。如果放弃了,机会或许不再来。
对年轻的女性科研者而言,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当社会中有关青年教师“非升即走”压力的讨论越来越多时,女性科研人员还面临着另外一层压力——她们也恰好处于社会所认知的“最佳生育年龄”时期。当社会时钟嘀嗒嘀嗒转动时,她们好似必须在此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个时段里到底选科研,还是选婚育?
而生育则有三难,占用时间,消耗精力,损耗身体。与此同时,有生育计划的女性科研者自己也会犹豫,高龄生育是否会对自己和孩子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但无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还是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申请,都有年龄限制。能不能通过申请,还需要考量过去几年的科研成果。
“不间断地进行科研”、家庭的期待与婚育的责任三件事,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三角藩篱,把正处于关键时期的女博士们“圈养”在其中。
打破三角形最简单的方法,是放弃掉其中一个支点。但这不是一个有关放弃的故事。而是她们从内向外打破“圈养”的藩篱,奔跑在科研路上,不断拷问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如今的林轶将当时的选择称为“命运选择”,“错过,就错过了”。翻越了山丘的她,此时此刻依然在科研的路上狂奔。
“还挺适合做科研”
闫柏,工科博士毕业,此时就职于某高校。在同是材料专业的师妹苏己印象里,被导师频繁提起的闫柏很适合做科研,“师姐毕业论文里用的方法,都是她自己探索创新出来的”。
实验做不出来的日子里,苏己有时反而会向当时已经离开课题组去读博的闫柏求助。“师姐当晚就发了两篇文章过来,让我参考一下办法。第二天我一做,就成功了。”
但在闫柏的说法里,自己只是运气好,在科研上“很顺利”的一个简单原因是,闫柏喜欢。
硕士毕业后闫柏曾经去找了一份工作。“但我去的企业总是无效加班,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更喜欢能够自控时间的感觉。我认为科研对我来说是更合适、更如意顺遂的一条路。”
于是,小时候就想做科学家的闫柏,从硕士变成博士,又成长为青年教师,一直和材料打交道。科研这件事对她来说,有压力,但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凭借自己的力量,总可以克服,也可以做得漂亮。

在别人还需要花一个月准备博士答辩的环境里,怀着孕的闫柏行动力超强,只花了一个星期就做好了所有事,“要提前规划,每天要做些什么,心里要有数”。
无独有偶。单论科研这件事,林轶用了“辛苦是辛苦,但是很幸福”的形容。
2010年,林轶博士毕业进入科研单位,转向更偏实用型的研究方向。“当时单位给的自由空间很大,而且我们不用考虑设备,不用考虑经费,只要考虑技术攻关,实在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我就算加班我也乐意。”
在前四年里,为了能够迅速熟悉新的研究方向,林轶自述几乎是“all in”的状态,体重掉了又掉,但情绪上依旧很饱满。“我当时觉得自己可以把握很多,把所有的宝都押在自己身上。”
靠自己把握,也是周隽的科研常态。如今,工科博后出身的她,已经就职于材料方向的研究所。
2015年,周隽被公派到法国修读博士课程。42个月,1个人,在陌生的国度,要面对21立方米的设备容器,自己切割打磨金属棒材,自己打砂,周隽觉得这段日子比后来在国内做博后更艰难。
“有一段时间,实验结果达不到自己预期,日子又在一天天过去,心里很着急。在做一次实验就非常不容易的前提下,我做了可能有几十次实验。等到实验做完开始写文章,文章又被拒。而且自己一个人在国外,挺孤独的。”再说起读博的崩溃瞬间,周隽的语气已经很平静。

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无非是探索两个字。“做科研给了你容错试错的机会,也是接触新事物,还可以去国际学术会议和别人交流,我自己还蛮愿意做这些事的。”高密度的知识“输入”和对未知边界的探索,让周隽感到幸福。
而这种幸福感足以对冲掉科研所带来的痛苦。“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周隽想了想说。
时 区
但好似年纪一到,林轶就再不能拥有这样“纯粹”的时间。她的大脑被强制性地塞入许多“需要考虑”的事。“什么话都来了。”林轶这么形容。
在全身心投入科研的几年里,林轶也顺利完婚。于是,父母开始烦恼她的下一件“人生大事”,生育。“医院还真的就把35岁以上的产妇自动划分为‘高危产妇’,高危这两个字一出来,就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父母无法理解为何林轶还不抓紧怀孕,甚至问过她,夫妻俩是不是要不到小孩了?
在林轶的想法里,博士毕业后的几年工作时间,对于一个科研者来说非常重要。“错过了这三五年就没资格申请一些项目了,而且项目申请过程中还要看近3年或5年的成果,这就决定了我们真的不敢轻易停歇。一旦中间断了一两年,特别是学术上的东西也不是说捡就能捡起来的,所以当时真的处于非常纠结的状态。”
为此,林轶“稀里糊涂”地考虑过丁克的可能性。
从本心出发,在已经全身心投入事业6年之后,林轶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孩子。受科研影响,林轶可以说是一个“计划通”,想做,那么最好就在计划的时间内做完。
喜欢户外运动的林轶,每周会有固定的5公里跑步计划,但在生育面前不得不“服老”。“生完之后,我才意识到年龄是真的有差距。同病房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她生完就走路回去了,我还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才恢复过来。”

2024年,已经在研究所工作的周隽35岁,周围催生的声音越来越多,“也是来自同事、朋友、亲戚和家人,总感觉聊着聊着,就会聊到生育的话题上”。在这个话题中,周隽的妈妈“火力”稍强,她会直接对女儿说,夫妻俩无论工作上有多大的成就,哪怕赚再多的钱,如果没有一个后代那都算不得成功。
但多数时候,周隽也是“左耳进,右耳出”。“我觉得也是一种关心,但倒也不是他们一说我就觉得我得赶紧怎么样,心里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
时区,周隽提到这个词。虽然社会给女性划了一个时区,但她还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在听从哪里的声音这件事上,周隽的选择更贴近自己的内心,她很喜欢自己现在30多岁的心理状态。
周隽觉得自己才刚刚到心理成熟的年龄,“生育这个事情,不是说我生理上到达某个年龄了就可以了”。合适的时机,尚未出现。
闫柏的父母,反而是开明的那一个。从头到尾,他们都是支持女儿的那批人,无论是结婚还是生育,他们都觉得应该要尊重女儿的意见。
于是在闫柏的家庭里,这个催生的人成了丈夫。本想等到博士毕业再考虑生育的闫柏,在丈夫日复一日的“唠叨”下最终妥协。31岁,博四,即将毕业的闫柏决定生育。
不过好在,彼时,闫柏已经基本完成了所有实验,距离博士毕业,只差后续的测试和一篇写下来的文章。“其实,我的导师、同门都很支持我,我运气真的很好,科研这方面很顺。女性的艰难,我是从成家后的家庭中感受到的。”
不理解
“能过就过,不过就离(婚)”,从公公嘴里听到这句话时,闫柏好像被狠狠扇了一巴掌。争吵,始于博士毕业后的闫柏,要不要前往丈夫所在城市继续科研路的问题。彼时她刚刚生育完不久,小朋友才三四个月大。
闫柏觉得,自己30岁之前的人生实在是太顺遂了,她在学术的岩壁上为自己攀爬,努力就能收获,周围的人也支持闫柏去做自己。30岁之后,她意识到,结构不平等问题几乎彻头彻尾否定了她过往的一切努力。
“在他们的视角里,嫁过去的我就是一个附属品,去哪是由我丈夫决定的。”闫柏在电话那头这么说道。

从打定主意读博开始,就想未来进高校继续科研的闫柏,在怀孕时从婆家处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如果能进站做三年博后就很好,因为丈夫当时还没办法“安家”,三年后也会换城市,正好闫柏可以跟随他一起换。
还没博士毕业的闫柏被立马推到了找工作的“悬崖”边,被要求着往丈夫所在的城市投递简历,自己的意愿直接被无视。不理解科研工作的长辈们甚至要求闫柏赶紧博士毕业找工作,“这样好拿生育津贴”。
还大着肚子,准备博士毕业答辩的闫柏,几乎独自面对着这样的糟糕局面,没有得到丈夫任何的心理支持。
“很多有一定学历的女性,倾听别人的能力和共情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最开始也愿意去考虑他们的观点。但是往丈夫所在城市投完简历后,结果是不理想的。一个是需要我做博后,另一个高校几乎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试用。”
争吵,从这里开始爆发。科研路一直非常顺利的闫柏,在这一环上耽误了整整一年。然而,职业时间是紧迫的。“后来入职高校的时候,对方也顾虑我快35岁了,好在国家延长了女性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时间,所以我当时说我可以申到40岁,这么看我还小。”
闫柏觉得很糟糕的另一点在于,当婆家在要求自己立马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和母亲时,自己的丈夫进入角色却非常缓慢。还在坐月子的闫柏,要忍着育后生理与心理上的不适,反过来“哄”丈夫。

闫柏能隐隐感觉到,在丈夫看来,什么事只要女性可以做到,那一定不是一件难事,于是如果自己能博士顺利毕业,那这也一定是件简单的事。
不理解,不支持,几乎充斥在彼时闫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闫柏过往人生中从未经历过的。相比起来,林轶家庭中的气氛,只能算小小地绊了她一脚。
当两家人为了新的生命而聚在林轶身边时,压力也随之而来。“我们自己知道,有些关键时间不把握就错过了,但是家人那时确实不够理解我。他们不明白明明怀孕了为什么还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为什么养在家里准备生育了,还那么焦虑。”
面对家人的不理解,林轶同样“愤恨”于,家人们仍然要用传统的家庭分工框架,来框住她。可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她,分明注定了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相夫教子的女性。
“传统家庭里,大家会自觉去给赚钱为主的爸爸让位。可是我虽然是妈妈、妻子,我的工作也不比你少,怎么对女方就不是这样的标准”。最让林轶接受不了的,是一路看着自己走来的父母也希望她回归家庭。
“为什么鼓励我走上这条科研路的是他们,反过来让我再回归家庭的也是他们?”林轶真实地为这个问题困惑过。
支撑与新生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要知道,在组建家庭,尤其是生育之后,“我”如何才能在社会藩篱不断挤压空间时,仍然有可能作为“我”存在,如何不把自己忘掉。
和绝大多数职业女性一样,作为科研女性的林轶和周隽,也面临着“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社会性提问。她们几乎“自动式”地在交谈间认真证明,自己真的可以平衡好,工作不会影响家庭,家庭也不会影响工作。

闫柏因那句话与公公翻脸,并顺顺利利在自己父母所在的城市,找到合心意的高校安定下来。“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作为独生女)我能够继承家庭所有的资源和资产,所以我在社会上也拥有了类似男性的话语权,不需要依附另一个家。头一次,女性像男性一样有了根基,我能够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找工作,真的离不开父母的支持。”
今日,闫柏仍在做着适合自己的事。林轶也是。
林轶开出的“药方”是沟通——家人们需要理解科研工作的工作性质与工作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如果改变小家,那么就能改变大家。“工作中已经是竞争的环境了,如果家里还要升级打怪,就是撑不下去的状态了。家庭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尽可能让我周围的环境缓和一些,这样我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去生活。”
家庭的支持,对于科研者而言总是非常重要的。某种程度上,周隽尚未生育的原因也在于,她理解同为科研工作者的丈夫——他正处于“非升即走”的关键阶段,两人还没有一个能称作稳定的状态,来迎接新生命。
但比起仅仅关怀理工科学类女性,闫柏总认为,应该从更宏大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当工作的确成为了女性能够拥有社会话语权的重要原因时,如何让女性能够获得、保住一份工作,或许是更重要的。
女性为生产付出的损伤,哺乳所需要的精力,这都是社会在衡量男女工作要求时,更多需要去考量的方面。“客观来说,工作单位确实在这期间少了一个劳动力,怎么让工作单位能够平和地看待这些事,挺重要的。”闫柏说。

反过来,如果有太多的倾斜,也会造成问题,“这就像人类驯化野生动物一样,有过于好的待遇,能力就会下滑”。在闫柏看来,女性自己保持斗志不滑落,也是“留在牌桌上”的重要一环。
一路走来,周隽已经听了太多“女生读博不值得,读那么多书终究是要结婚生小孩”的话,但她搬器械设备的时候没有停过,打砂的时候没有停过,切割金属棒的时候也没有停过。当自己具备科研热情的时候,科研就是不辛苦的,周隽始终这么认为。
“不要害怕,做好今天的事。”她最后这么说道。







![[集市好物]闲置电子产品(投影仪/可视门铃/家庭摄像头/胶囊机/保温水壶)](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07fc1ada-6fa5-422c-b205-c5c26c31b2c9.1080x81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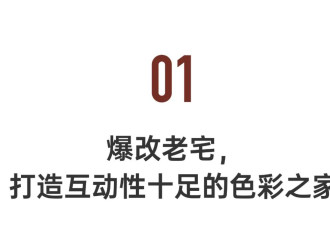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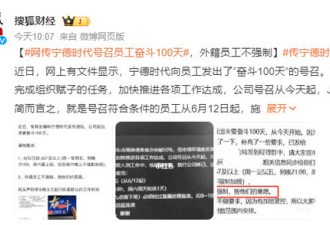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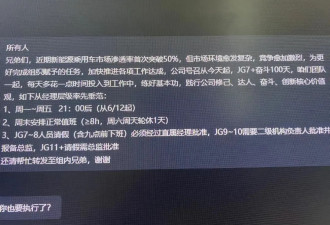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