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必昌:我的父亲邱岳峰

父亲去世至今已有二十七个年头了,这期间时常会想起他,偶尔也会梦到他,但提笔写他还是第一次。
还没我的时候
那是1922年的5月10日,父亲出生在东北的呼伦贝尔(现属内蒙古),故小名叫呼生。
我爷爷是福建省福州人,奶奶是俄国人,所以父亲算是个混血儿。
爷爷奶奶为了生计,带着幼时的父亲在北方一带,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四处奔波,谋事。每到一处,无固定居所,几乎都是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1936年,父亲十五岁,奶奶带着他到了祖籍福州,母子两人同样还是住在亲戚家,生活十分拮据。
1940年春,父亲离开奶奶独自辗转经过上海、北京,最后在天津找到爷爷。此时,已到了1942年的春天。
在那动荡的年代,父亲的学业也就在极不稳定的跳跃中结束了。
父亲在“文革”的交代中曾这样写道:“离开了学校到天津。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就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当布景工人。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一个玩笑,经我述说我的要求后,他同意了,就拿了一个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就会了,于是他就带我去见大亚剧团团长唐皓华,我就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种身份出现,简直是一种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地记地位,背台词,时常偷偷地模拟演员的表情,我终于当了演员。当时,一股脑儿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成为一个名演员的身上。演技呢,是从苦练中得来的,受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我的天地就是干戏。”
于是,父亲的演艺生涯一发不可收拾。八年间,父亲参加过近二十个演出团体。打过杂,演过戏,跑过龙套,扮过主角,干过导演,也当过团长。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去形容父亲的前半辈子,那是个在无奈中挣扎的岁月。他努力过、失望过,理想过、迷茫过,成就过、失败过。直到1949年在上海,父亲迎来了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
父亲说:“终于能当家做主人了,生活安定了,哪儿也不去了。不用寄人篱下,遭人白眼,不用东奔西波,逆来顺受了。”
1950年3月,经人介绍,父亲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

邱岳峰
我很小的时候
长宁路1250弄2支弄46号,我们家曾在那住过。那时我才四岁,对长宁路的那段日子没有什么记忆。惟独记得一天晚饭后,我贪吃父亲为母亲买的香蕉,吃完一根后吵着还要。父亲哄着说:“就一根吧,吃多了会撑着,明天再吃。”我至今还能感觉到那芝麻香蕉的甜糯和那诱人的香味。对于才四岁的我,怎能抵挡这般诱惑,于是又吵又闹。母亲一旁说:“算了,孩子要吃就让他吃吧。”父亲一气之下说:“好!那你吃!看你能吃多少。”我忘了那晚吃了多少,但我知道小肚子很胀,胀到几乎不能随意弯腰、喘气。刚抹完小嘴,父亲狠狠的一把把我抱下楼,拽出门外,在一个很空大的院子里朝着屁股一通打。我又哭又叫,没用。很晚了,没有路人,更没有劝说的,直到母亲追出来才算了结。
多年后,和母亲说笑时谈及此事,我问:“为何非要把我拖到大院打我?”母亲说:“你父亲怕你的哭叫声影响到小楼上下邻居的休息。”对呀,父亲一向很替别人着想,而我却因为这,多挨了几巴掌。

上世纪五十年代,邱必昌与父亲邱岳峰
我小时候·春天
1953年我们搬进了南昌路550弄的丙弄10号,那会儿叫钱家塘。这块地方后来成了全国闻名的襄阳市场,我们家在那住了二三十年,直到动迁。
很多时候,很多人问我:“你父亲生活中是什么样?”我总毫不思索地告诉他:“普通人样,平常人样。”我曾见他为奶奶过世哭过,为得到他学生送他的一副铺板而乐过,为我做错事怒过,也曾为他亲手做成五斗橱而喜过。
隔了那么多年,回想起和父亲一起的日子,很是留恋。
父亲的手长得漂亮,修长、整洁、干净。我曾仔细观察过,父亲在洗脸的同时,常常会用一把软毛板刷刷洗指甲的缝隙,哪怕是劳动改造的那些年。
那时我和二弟还小,都还在上小学,母亲时常抱着妹妹或最小的弟弟去车站接下班回来的父亲,一旦家务脱不了身,就让我和二弟去接。
父亲每天乘45路公共汽车上下班。车站在靠近汾阳路的淮海中路上,离家不远,但要过两条马路。
黄昏,暖暖的,西斜的太阳,透过梧桐树叶洒在街上。路上的车不像现在那么多,行人也不多。我和二弟靠在音乐学院的篱笆墙边,手上摆弄着纸折的船或是什么,等着墨绿色的45路车,等着“阿爸”。
来了一辆!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了,到站车停,下来三五个人,没有父亲。又来一辆,还是没有。
曾有许多次,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亲,就自己对自己说:“再等三辆,不来就回去了。”三辆过后,仍未见父亲。“再等……再等两辆就回去了……再等一辆……”其实很少有自说自话就回去了的时候,总要看到父亲下车才心甘。
已记不清是第几辆45路车了,这一辆我终于看到他在车门旁等着车停妥。车门开了,他没有抢着第一个下车。
我们叫了他一声“阿爸”。父亲边下车边应声,问:“姆妈呢?”我边跳边说:“在烧饭。”
过马路了,父亲握着我们的手,看看两边的车辆,然后搀着我们过去。
过了一条汾阳路,又过了一条襄阳路,进了弄堂,踏着“弹硌路”,穿过“过街楼”,进了家门,我们才松手。
1980年3月30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在他的病床边,看着他安详又似乎熟睡着的脸。
不信,怎么也不信他会就此离开我们。
抢救父亲的医生,和我们家认识。过了好一会儿,她走近我们,身后还有两个医工,推着一辆运尸车。她看看父亲再看看我们几个,用上海话对我说:“爷啊……可惜呀。”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阿爸可能走了。医工上前替父亲整理着,要用白布把他裹起来。我们几个相继凑近父亲,再一次握着他的手,已经凉了的手。阿爸真的走了。
就是这双手,搀扶着我们一路走来。尽管有时他也很累。直到我们都长大了,他松手了。
我们都成人之后,谈及为何幼时几乎抢着接阿爸,说出来也许不信,答案是都想握握阿爸的手,那双漂亮,厚实又温暖的手。
长大了·夏天·深夜
1962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全国的技术学校裁减三分之二的学生。我就读的上海汽车运输学校也不例外,得解散三分之二的学生。学校给学生两个选择:一、直接分配到工矿企业参加工作;二、转到普通中学继续学业。全校解散的一二百人全都同意进工厂,只有我一个想转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和同学玩耍,我很晚才到家。轻手轻脚地上楼,推开门,母亲和弟弟妹妹都睡了,父亲在一角的小台灯下看着书,见我进门说了声:“回来啦,干吗去了,这么晚?”
“快放暑假了,和同学们在一起呢。”
“不困吧?”
“不困。”
“来,和你说说。”
我坐在饭桌边的方凳上,父亲坐我对面稍侧一点。没开大灯,挨得很紧,怕吵醒家人,说话也是轻声轻语。
“听你妈说你想转学,不想去工厂,怎么想的?为什么?”父亲问。
此时我才知道父亲没睡是等我回来谈这事。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喜欢文艺,喜欢表演。从六岁开始,父亲就时常带我去他的厂里配动画片,和译制片中的小孩。上学后,班级上,学校里,凡是跟文艺表演有关的事,基本少不了我,我自以为长大能当个演员。
“我……我想……”父亲似乎很认真,那年我才十四岁,把我当个小大人,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想念书,长大当个演员……”我支支吾吾地说道。
有好一会儿,父亲没说话。
借着暗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我。
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是在寻找恰当的口吻来说服我。他在替他儿子作一个人生中重大的决定。
“不错,”父亲说:“人是要有理想,生活才有意义。”
“你想当演员我并不反对。可你知道吧,干这一行,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干到最好。否则就像篮球场上坐冷板凳的运动员,你会后悔一辈子。我在舞台上‘混’了这么多年,在厂里也干了十来年,不算最好,但还是有一些人知道‘邱岳峰’这三个字,我也还在努力。你想干演员,也可以,但你不一定能干得好,因为你脑子里缺了那根‘弦儿’。”
对啊,一个人的成功,不就是天才加勤奋加机遇吗?而所谓“天才”就是我父亲说的那根“弦儿”。
“进厂,当一个工人。”父亲终于说出了他替我作出的决定。
“我们祖上没有一代当过工人,你是第一个!”
那个年代,大家都会以家里能有个工人阶级为荣。而父亲那时还有帽子在身,恐怕更觉得当工人就不会像他那样——这层意思是很多年后,我一个人琢磨出来的,当时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他有点傻。
“想要读书有夜校,照样念大学。想演戏,业余时间,完全可以。”
那天父亲和我谈到凌晨两点。
第一次谈到这么晚。
第一次谈了那么长时间。
第一次谈得那么认真,像一个成年人和另一个成年人。
“你要踏入社会了,跟上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会遇到很多事,更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千万记住,没有过不去的河!不管遇到什么难处,咬咬牙一定能挺过去。”
直到今天,我的手机的屏幕上还设置着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河”!

50年代初,在梵皇渡路上译厂的小花园里,左起:邱岳峰、尚华、赵慎之、毕克
过年
以前我们都盼过年,可以穿新衣(也许就是做一套蓝布罩衫裤),吃零食,花生、瓜子、糖果,吃父母做的拿手饭菜,粉蒸肉、糟豆芽、鸡油饼。那年头,到了春节会有比平时多一点副食品配给。
曾有那么几年,每个年初二的晚上,是我们家最热闹、最开心的日子。父亲的学生,圈外的朋友,我的同事,会不约而同地来拜年,聊天。
那一天,我们家会早早地吃完晚饭,把饭桌收拾干净,铺上一年只用一次的桌布,摆上糖果,拿出茶壶和茶叶,把取暖的火炉烧得旺旺的,等着大家陆陆续续到来。
有人敲门。
“进来!”我们都会跑着去开门。
“邱家阿爸、邱家姆妈新年好!”“邱叔叔、阿姨新年好!”“邱老师师母新年快乐!”“邱伯伯、伯母新年好!”……来了许多人,他们中有工厂的木匠、车工,有中国画院的,也有插队的、农场的、文化馆、房修队的……
家里地方不大,17.2平方米。进门脱鞋,大家光脚踩在用碱水板刷刷洗过的地板上,一点也不觉得凉。最早来的坐在椅子或方凳上,后来的只能挤坐在床上,再晚来的,干脆拿了垫子或枕头坐地板。好在彼此都熟悉,谁也不会在意。
因为过年而换上60支光的灯泡,使房间比平时亮了许多。炉火越烧越旺,连出烟口的铁皮都烧红了。水开了,热气顺着壶口直往外蹿。母亲张罗着沏茶倒水。
大伙聊着,尽是些开心的事,什么话题都有。你一句、我一句,各自说自己经历的琐事,还有笑话。父亲当然也在其中,听他们说,和他们侃,时不时会尽情地笑。忘了是谁说的一个现实中的笑话,逗得父亲和大伙笑到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有的顺势倒在床上,有的笑到直抹眼泪……
我又往炉子里加了木柴,父亲边笑边用“洋泾浜”上海话说我:“勿要加勒,再加房子阿要烧起来勒。”
是啊,外面刮着风,下着雪,很黑,很冷。可我们家的今晚却点着大灯,烧着火,很亮,很热。
我年轻时候
我年轻时候喜欢旅行,曾计划着每年去外地一次。于是苏州,无锡,杭州,黄山……越走越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伟人的诗词,一直让我期盼着有一天能去东北体验一下,看看那里的冰封,雪飘。但当时家境平平,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无奈,只能暂时作罢。
197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吃完饭,父亲让我洗洗脸,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要带我出去。
“到啥地方去?”我问。
“去汤晓丹伯伯家。”父亲说。
母亲在一旁边收着桌上的碗筷边问:“去老汤那儿干吗?”
父亲说:“上影厂拍一部片子《傲蕾·一兰》,需要很多长相像外国人的演员。我演一个俄罗斯的神父已经定了,老汤想见见他看能演什么。”
汤伯伯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就在我家弄堂边的高塔公寓里,没走几步就能到。汤伯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看了我说:“不错,有点像(外国人),我看可以,明天去上影厂,让姚寿康再看看。”
姚寿康,这部片子负责找演员的副导。见到我,姚导给我出了个小品的题目,等我摆弄完了就说:“好了,就是你了。”我心说,姚导谢谢你。
兴奋,尽管是跑龙套。
暗喜,能去东北出外景,免费体会北国风光。
不久我就随着摄制组去了东北依兰县出外景。第一次独自离家要几个月,出发当天没家人送我,走的时候居然让母亲发现我有些伤感,父亲说我没出息。
到外景地没多久,收到了父亲给我的一封信。
洁缨(我的小名):
一晃走了一个星期了,怎么样?还习惯吗?北国风光没有使你惊奇吗?其实,那里正是你和我出生的地方。也许你现在立足的地方离我出生的呼伦贝尔更近些。这也是件有趣的事。不久,你将看到真正的森林,真正的草原。要把这些新鲜的强烈的印象记在心里,记在画笔下。这就是生活的知识。要在接触老乡的时候,虚心地向他(她)们讨教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事一物,他们的历史,传统,故事,他们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生活的机会。不好好地利用,嘻嘻哈哈地混过去,对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来说,未免可惜。而且是追悔莫及的事。望你能好生体会。
听说你走的那天还流过眼泪,没出息。我在比你还年轻的时候--十九岁。就光棍一个,带着唯一的一件财产--一把牙刷走南闯北了。那个世道,能伸手来扶你一把的人不多,全靠自己呀!也许,你觉得我和妈妈都没回来送你,委屈了?妈妈以为你是在作一次愉快的旅行,而我只知道你是晚上走,回家才知道不是晚上,是六点开车。如果是为的这个,那么,现在就算作解释吧!
胶片要来了两卷21定的,如果有人到长影,把我附的信带给他,也许还能给你小补充一下。注意身体,不要无谓的嬉笑荒废了光阴,多做些有益的事。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向你索取的标准就愈多,不努力就会被淘汰!祝健康!
爸爸 78.6.6
父亲写给家人的信件,保留下来的很少。惟独这封信我一直留着,可以说是很好地珍藏着。
这封信,我读过很多次。字里行间,读得出他对孩子们的期望,更读得出他对孩子们的爱。
这封信,我看过许多遍。每看一遍,就觉得父亲还健在,就坐在我对面,靠得很近,用我听惯了的嗓音说着:“……注意身体,不要无谓嬉笑荒废了光阴……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其中可能还夹杂着一两句“洋泾浜”上海话。

邱岳峰
冬天·梦
那是个人人都不务正业的年代。父亲也不例外,不配音了(没电影可配)。于是乎劳动、扫地、干木匠活、背红宝书。
父亲在我们几个孩子眼里很聪明。家里的五斗橱、茶几、小沙发、靠背椅,都是他亲手做的。从设计图纸、锯、刨、拼、装、油漆,直到完成,都是他利用不务正业的业余时间做的。可惜这些东西在动迁时都丢弃了,现在想想很是可惜。
具体哪一年,忘了,反正是那个年代。
父亲在厂里劳动,下着雨,一不小心,他从湿滑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段日子虽说他腿上绑着石膏不能动弹,但家人倒也庆幸,这样父亲可以不用去厂里接受改造了,能每天在家看书、看报、听广播,和探望他的学生谈天说地。
好景不长。
一天晚饭后,母亲在床上为父亲织着毛背心。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讲鬼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父亲很会讲故事,他不仅是说,还稍带表情演着故事中的人物。也许是太入神了,也许是被吓着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听得一动也不动。母亲时不时地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们几个。
“突然,”父亲说:“有一个影子划过墙头……”
“邱岳峰!”
我们都听到了,楼下有人在喊。
“邱岳峰!”这一声更响,带着命令,带着训斥。
父亲赶紧朝我努努嘴说:“快去看看,什么事?”我拉开房门,走下几格楼梯,看见楼梯尽头有个人,不知道是谁。但肯定是造反派的,冲着我用很大的嗓门说:“邱岳峰,明天早晨八点,到厂里报到!”(这会儿,我真想骂他。你他妈的算老几!)
“砰!”楼下的门被重重地关上了。造反派走了。
我返身进屋,轻轻把门关上。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昏暗中,谁也没动,也没发出声响,母亲手中的绒线针也停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隐约听到母亲的啜泣声,接着弟弟妹妹都哭了。
我看着父亲,父亲对母亲说:“别这样。”又看我红着眼睛不动,冲我说:“来,过来。”我慢慢地走过去,靠着他,一手摸着他腿上的石膏。父亲搂着我们说:“没事,没事,歇了那么多天,很久没去厂里了,去看看也好,别哭……”
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他瘸着腿在厂里是怎么过的,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他在厂里的那些日子。
父亲故世后,我曾不止一次梦到他。
一天,我不知不觉来到万航渡路618号,老翻译片厂。
太阳不知去哪了,连着几天都不露面,即便在不下雨的时候。
傍晚一场大雨过后,天是灰的,地也是灰的,云层低得让我有点喘不过气。进了厂门,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水塘。刚入秋,树叶怎么都掉光了?我也不清楚。我进门往右一拐,看见父亲独自一人坐在演员休息室门外的一张破藤椅上,这把椅子他曾亲手修补过。四周空无一人。我站在老放映间还在滴水的屋檐下,看着眼前破败的一切,以前的翻译片厂不是这样的。墙上的石灰被风雨几乎冲刷光了,露出青灰色的砖头。演员休息室又脏又乱,有一面墙还倒了,一眼望去荒凉一片,没膝的枯草在秋风中漫无目的地摇摆着。
父亲背对着我坐着,这背影太熟悉了,手依在椅背上,托着腮,这是他在休息。还是穿着那件隐约看得出汗渍的老头汗衫,尽管他把短袖卷到肩上,但右肩上的破洞还是露了出来,那是干活磨的。
我轻手轻脚地走近他,去到他身边,他似乎也感觉到我来了,慢慢地转过头。他刚刮过胡子的脸上带着倦意,显得苍白,灰白的头发看得出梳理过,可还是有点凌乱,一定是风吹的。父亲看着我,眼睛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一会儿,我低头小声在他身边说:“他们……他们要你去一躺。”父亲顿了一下,吃力地用双手撑着椅背站起来,无奈地点了下头,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神告诉我:“走吧。”
尽管这样,我很高兴,他还活着,只是病了,病了很久,挺过来了,又能配音了。
梦,只是一个梦。闹钟响了,我躺在床上,懒懒地睁开眼睛。撩起窗帘。“妈的,又是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
我年长的时候·墓地
父亲去世后第十年,我们把他下葬在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公墓里,每年母亲和家人都要去一两次,但还是总是觉得太远,不方便。于是就想着把墓迁到上海。
几年前,听说译制片厂老厂长陈叙一伯伯葬在奉贤临海的一个墓地,我特地驱车前往去看了看。
其实我和陈伯伯也很熟,小时候去译制片厂配音,经常见到他。父亲也曾带我去陈伯伯家中玩过。我至今还记得他背着手走路的样子。
我站在陈伯伯的墓碑前,突然想起父亲曾不止一次在家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陈叙一,就没有我邱岳峰!”说得那么肯定,那么坚决。
当年,父亲被逼着、哄着、骗着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冤枉!据我所知,父亲这一辈子从未革过谁的命,更从未反对过革谁的命),还落个留厂察看的处分。
走,不干了!父亲萌生了离开译制片厂的念头。可陈叙一伯伯从未歧视过父亲。接下来的日子,只要陈伯伯认为适合父亲戏路子的角色,甚至主要角色都会顶着压力交给父亲来配。由此,让父亲感到在译制片这个行当里有他的一席之地,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二十多年。
当下我就决定,就这儿。我要把父亲的墓迁至陈叙一伯伯的墓边,我想他们俩在天之灵一定会很高兴。
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屋住七口人,很挤。如今想让父母在天之灵住得好点,宽敞点。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咬咬牙买下了陈叙一伯伯墓旁的一块地。墓地很贵,贵得离谱,折合成平方算比我现在住的房子还要贵上好几倍!罢了,就算是我们小辈对他们的一片孝心吧。
父亲的墓碑,好友陈丹青在帮着设计,耗费了他很多心思,我有点过意不去。
“墓碑上要不要碑文?”我问。
“不要,”丹青说:“什么都不用写,就邱岳峰三个字,够了。”
是啊,对喜爱他的观众来说,父亲是他(她)们心目中的邱岳峰。
对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来说,邱岳峰是我们的好“阿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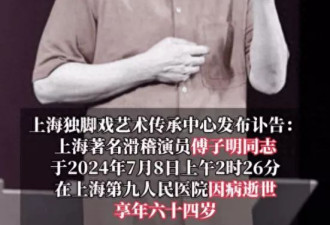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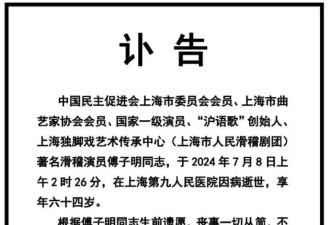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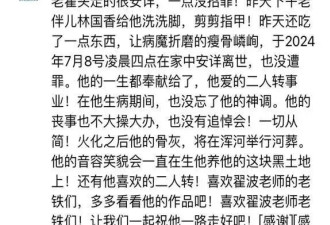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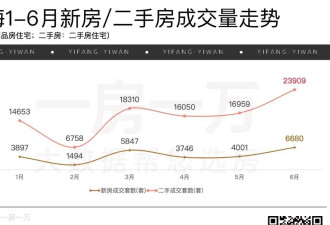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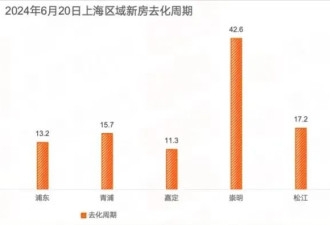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