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女儿嫁豪门,绝望主妇把水银注入血管
王戈多,新闻系毕业,误打误撞去了医院,从此成为一个医院的“局外人”。
不是医生,却也有些医学常识;不是患者,却天天在医院;不是家属,却体味着他们的悲欢离合。
工作十五年后,他记录下医院看到的众生相。
01
人类不感谢罗辑
我当初找他看病的时候,唐远应该还不到三十岁。
几年前的一天,吃了一顿火锅之后,我连续拉了三天肚子,总觉得屁股火辣。刚开始以为只是急性肠炎,吃了点药,三四天也不见好转,我想自己应该长了传说中的痔疮。
那天是周末,和我熟识的几个主任刚好都不上班。值班医生是唐远,一个身材挺拔、面容俊朗的年轻医生。
唐远说:王哥,你侧躺到检查床上,我看看。我以为仅仅是看看,之后才知道自己大意了。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指检”,那滋味,真的让人痛不欲生。
还好痔疮没破。他给我开了一个中医方子,说这个方子很实用,石榴皮、葱白、白矾,温水坐浴五天,让我回家先试试,不管用了还得手术。
作为中医黑,我问唐远:管用吗?他说:你试试吧,应该多少管点用。
照方用药,三天后,我已完全恢复正常。
我问唐远:这种方子为啥不大规模推广?患者得少多少痛苦呀。
他说:王哥你不在临床,有些事你不知道,这个方子是医生之间流传的,大家都觉得管用,但是不在诊疗指南里。咱们认识,我敢给你用,不管用你也不会找我麻烦。但患者要用,一旦出现问题,就都是医生的责任。所以我们只能按照指南来诊疗。
他问我:你记得神经外科李远平主任的事儿吧?我顿时觉得唐远的选择有他的道理。
李主任是神经外科著名的“一把刀”,我们有胶质瘤的病人都会介绍给他。他经验丰富,技术一流,经他手术后的患者复发率极低—— 胶质瘤是一种恶性肿瘤,复发率奇高。经常有患者切了瘤子,还没出院,一复查,又长了出来。
做这个手术风险很大,一旦位置不好,切多一点,患者就有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了。有一些医生就会选择保险一点,少切一点。
这样的医生我不能说是庸医,他们是被一些患者和家属吓怕了,先保命,再说手术。
而李主任是其中的异类,该切多少切多少,将风险全都放到了自己身上。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2013年,连续两例胶质瘤患者出现了后遗症,而且这两个患者的家属还都不是善茬,每天行政办、医务处、卫健委到处告状。
而李主任的脖子,那是属长颈鹿的,头颅高高扬起,只要自己没错就绝不低头。
那年他四十七岁,正是外科医生的黄金年龄,最后不得不辞职,远走海南。
唐远说:我们是医生,也是普通人,也有父母妻子,总得先有工作,养活他们对吧?
晚上我和妻子感慨这个事儿。她说:这种现象很普遍,不是医生不想给患者用最省钱的方式,而是不在指南里,他们不敢用。
那天晚上我正看《三体》,里面有句话:人类不感谢罗辑。
02
急诊科的吉祥物
第一次见到余六六,是我刚到医院工作那会儿。
那天我总值班,在急诊科见到三十多岁的她,一看就知道她智力发育有问题,身体很大只,头部却很小,目光呆滞,正拿着一把扫帚扫地。
我问急诊科主任:现在保洁公司都雇这类人员?
急诊科主任笑着解释说:她叫余六六,我们科的吉祥物,老主任留下来的,我们都很喜欢她。
老主任姓余。1975年6月6日的早晨,他来医院上班,看到急诊科门口的垃圾桶前放着一个小包袱,还在动。抱起来一看,包袱里是一个女婴,三四个月的样子,小脸黝黑,但眼睛明亮,正对着他笑。
余主任说,他当时心中一暖。把孩子抱进急诊,余主任就开始联系派出所、福利院,但那个特殊年代很多单位都不能正常运行,没有单位愿意接收。
就这样,女婴在急诊科落了户。因为是6月6日捡到的,所以大家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六六,随余主任姓。
余主任是北京人,下放到山西,据说之前还被打成右派,性格内敛,一直也没结婚。由于家里没有女人,孩子就放急诊科,谁上班,就抽空帮带带六六。
最开始六六一切正常,但六个多月时出现了发育迟缓现象,两岁多出现语言障碍。尽管就在医院,做遍各种检查,也没查出病因。五岁了仅仅会喊“爸爸”,说一些简单的词语,不管周围有没有人,会一直微笑、拍手。
同时又出现运动障碍,尽管不影响生活,但也不能像其他小孩一样奔跑、蹦跳。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各单位也都正常运行了。
院领导找余主任谈话,说:这么大孩子天天在急诊科,不合适,您也四十多岁,带着这么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还真不准备结婚呀?不如送福利院吧?
余主任一想也对,就听从建议了。可是就在福利院工作人员带着六六走出急诊科时,六六突然回过身,歪着头,微微一笑,看着余主任清晰地喊了一声“爸爸”。
余主任顿时泪崩,跑过去一把抱住六六泪如雨下,院领导也只能在旁边叹息。之后,余主任办理了正规的领养手续,六六依然在急诊科生活。
经过持续观察,余主任发现六六主要特征是对热敏感性高,睡眠少,迷恋水、纸、塑料等东西。在医疗信息匮乏的年代,他最终在国外文献中查到,六六得的是安格曼症候群,英文叫Angelman syndrome。
它有一个异常美丽的名字—— 天使综合征,是一种基因表达异常或功能缺陷引发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直到今天,也无法治愈。
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余主任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六六进行健康管理。通过图片卡、交流卡等工具,六六获得了最基本的交流能力,通过一些基本的行为训练,六六学会了吃饭、扫地、擦桌子等基本生活技能。
1995年,余主任退休,想带六六回家,但六六说什么也不愿意迈出急诊科的门。余主任自己走了出去,六六在后面一直喊“爸爸,爸爸”,但就是不愿意出去。
之后,退休的余主任每天还来急诊科看六六。六六除了智力障碍,还算能照顾自己,也能帮科里做些打扫的活儿,跟急诊科的医生、护士,都能相处融洽。
没有烦恼的六六,成了急诊科天使一般的存在。
2006年,七十一岁的余主任查出了肺癌,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弥留之际,他拉着急诊科李主任的手说:我教了你一辈子,没开口求过你啥事儿,今天求你一定要照顾好六六。等你退休了,让下一任主任、再下一任也都好好照顾六六,我代她谢谢你们了。
也就在那天,正在护理站玩打印纸的六六突发癫痫,躺在地上不停抽搐。
2017年6月的一天,六六突发脑出血,她瞪着空洞的眼睛,双手向上挥舞,一直叫着“爸爸,爸爸”,叫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从容去世,脸上还带着那种特殊的微笑。
03
不存在的孩子
老谢是我下乡时认识的一个哥们儿,年龄和我差不多,是当地政府的一名公务员。那会儿并不熟悉,只是因为工作原因有些接触。
我回医院后,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老婆在当地医院看病,要转到省城的医院,问我哪个医院妇科好。我说来我们医院吧,我们的妇科还是挺不错的。
那天周二,是妇科主任门诊。给老谢老婆看完以后,我问主任啥情况。
主任说:她现在的问题不是妇科,而是要先看精神卫生科。所谓的精神卫生科,其实就是治疗精神类疾病的科室。
老谢的爱人姓刘,比我们小三五岁。两人结婚后曾经有过一个女孩,刚生产完的时候,小刘有过短暂的产后抑郁,因为治疗及时,没有大的问题。
孩子三岁时,小刘带孩子回村里住。中午母女俩在堂屋睡午觉,孩子醒来后,自己下炕到院子里玩,不小心掉进了化粪池。
小刘醒后找不到孩子,最后还是家里的狗一直绕着厕所叫,人们才想到是不是掉到了化粪池里。等最后捞上来的时候,小孩已经气绝很久,浑身污秽,嘴巴大张着。
老谢默默为孩子洗刷干净,将孩子所有的小衣服、小玩具收拾好,焚之一炬。自始至终,他没有苛责妻子一句。
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刘都无法走出痛失爱女的阴影。
直到有一天,小刘欣喜地跟老谢说,已经五十多天没来例假了,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会有第二个孩子。在县医院做了个简单的血检,结果显示孕酮增高,是怀孕的表现,医生建议他们再做个B超确定一下。
但这个孩子对夫妻二人来说太重要了,妻子说什么也不做B超,怕辐射会对孩子有影响。
他们就这样,一直倍加小心地呵护着这个子宫中的孩子。
三个月过去,妻子腹部依旧平平,六个月过去,小腹仅有微微隆起,八个月过去,还是几无变化。
老谢坐不住了,要带妻子去做检查。医生做完超声后跟夫妻二人说,没有看到孩子,但有一个瘤子,有毛发、牙齿,高度怀疑是畸胎瘤。
妻子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她说:怎么可能不是孩子?我每天都跟他说话,他还在肚子里回话,还踢我,怎么可能是个瘤子?他有头发,有牙齿,你当医生这么多年,见过长头发和牙齿的瘤子?
医生无奈,只能建议他们到太原来看。
妇科主任跟老谢说:B超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是畸胎瘤无疑。你老婆感觉到的胎动,都是她的心理作用。畸胎瘤是一种卵巢生殖细胞肿瘤,大部分是良性,少部分是恶性。你老婆这个大概率是良性,需要你做工作,及早治疗。拖得久的话,良性也有恶变可能。
老谢最终没有做通妻子的工作。小刘说:太原的医生也是庸医,我好不容易怀上这一个孩子,他们还想把他拿掉,我们要去北京保胎。
我目送着夫妻二人离开医院,妻子摸着肚子,十分开心。
后来我问老谢,在北京做手术了吗?老谢说,始终都没做,妻子不同意,住了院就和医生大闹,根本没办法做手术,在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也没什么效果。
我问下一步怎么弄,他说他也不知道,妻子还是每天“保胎”。
04
雪花肺
我偶然认识了李璇,她是一家专业媒体的编辑,丈夫是省内某著名大学的中层干部。
她四十多岁,依然是少女的样子,白衣飘飘,除了眉头紧锁,基本上看不出来什么异常。
我第一次见她的女儿时,八九岁,一看就是个美人坯子。李璇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自己又是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
总之,你会觉得,她就是一个妥妥的人生赢家。

发现李璇有点问题,是在一天晚上。
十一点多,她打电话给我,声音压抑而炸裂,能感觉到有非常大的委屈。她说:和公公婆婆在一起住,两个老人都六十多岁了,还当着她的面做夫妻间的事情。
我听完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她丈夫我认识,她公公婆婆我也认识,完全不像能够做出如此有失伦常的事情。
我给她丈夫打电话,丈夫告诉我不可能,他马上就到家。
第二天,我就见到了李璇和她丈夫,李璇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眼中的神采就像被抽干了。
心理医生诊疗的间歇,她丈夫告诉说,李璇一直都有抑郁症,最早是产后抑郁,慢慢发展成了严重的抑郁症。那会儿他们新婚燕尔,郎情妾意,第一个孩子很快来到世间。李璇总是抱怨头痛,莫名其妙地便开始流泪,他也没当回事。
有一天李璇当着他的面,踩着一把椅子爬上了窗台。
他当时还纳闷,这是要干啥?之后发现妻子面无表情,他从后面一把将她拽了下来。李璇就和惊醒一样,问怎么回事。他说:你知道刚才怎么回事不?李璇茫然摇头。
他才发现,李璇可能真的病了。后来病情反反复复,但为了仕途,他不能大张旗鼓带妻子去看病,一拖再拖。
我问: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这和仕途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有一个精神病妻子,领导会如何想?人言可畏,你还年轻,不懂。
对于她丈夫的想法,我确实不懂,不管什么病也得及时治啊。鉴定结果很快出来,心理医生告诉他们,李璇这是重度抑郁,我们医院没有精神病房,建议去专科医院。
男人向我和医生道谢后,说他们回家合计合计。
抑郁症的特点之一,是时好时坏。后来我和李璇约过一次饭,我问她:你知道自己有重度抑郁不?她说知道。
我说:那你得积极治疗呀,你丈夫指望不上,自己的命得自己救。
她说:不行,我得为女儿考虑。一旦我住过院,就打上了精神病的标签,以后谁敢娶精神病的女儿?
她又说每次发病前,大脑中啪的一声,就跟一根橡皮筋断掉一样。我问那怎么办。她说只能自己注意,尽量不让那根橡皮筋断掉。
后来,我跟心理医生了解了下,抑郁症根本不是我们说的心情低落。在这种病人眼里,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除了黑白灰三色,没有第四种颜色,会出现幻听、幻视,所以很多病人自杀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当你真正见了抑郁症的病人,你会发现自己每天嘴里念叨的所谓抑郁,最多只能算心情不好。
后来有一天,李璇丈夫给我打电话,问我们医院呼吸科怎么样,我说还不错。他说他们在救护车上,正往医院走。我知道,一定是李璇又出事了。
李璇的主管医生给我看了一张影像片,上面显示,李璇的整个肺布满了雪花般的白色斑状阴影。影像看上去异常诗意,异常漂亮,却宣告着残忍的结果——这就是传说中的“雪花肺”。
主管医生告诉我,他行医三十年,这是第一次见,只能尽量治疗,不一定能抢救过来。
悲剧是这样发生的:丈夫在外地出差,李璇将家里的三支体温计打碎,用针管将水银搜集起来,注射到了自己的血管里。肺上的“雪花”,就是大剂量汞随血液快速进入体内,通过肺动脉进入毛细血管网,沉积在肺部的景象。
李璇的心中,早已装满整个冬天,冷冽异常,但她自己和家人都没有给予重视。寒冬雪花一片一片累积下来,最终压垮了她。
李璇因多个脏器衰竭去世。去世之前,我过去看望她。她说,她终于解脱了。困在这具躯体中的灵魂化作一只鸟,振翅而飞,向着那渺远的自由之地。
05
凝视深渊时
张昱不是第一次来医院皮肤科了。
第一次来,是因为起了一身莫名的小红点,皮肤科医生初步诊断是接触性皮炎,给开了百多邦软膏。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这个身高一米八,长得方方正正的小伙子不但不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形象也大打折扣:小红点慢慢扩散成红斑,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水疱和坏死,指甲也变得又脆又薄,其中两个干脆脱落,露出鲜红的血肉。
医生担心是红斑狼疮,但他的红斑又不是红斑狼疮特有的蝶形或盘状。
就诊过程中,医生注意到张昱一直在咳嗽,问他什么时候有这症状的。张昱说起疹子没几天就开始咳嗽,估计是感冒了,一直好不了。
医生觉得有可能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就给他做了血、尿的定量分析。
结果出来后,医生问张昱你做什么工作的。张昱说无业在家。
医生又问最近有没有接触过百草枯。张昱反问:百草枯是啥?医生说:我怀疑你这是百草枯中毒,一种剧毒农药。
进一步查体后,发现他口腔黏膜充血,中上腹有压痛感觉,低血压,肺部有罗音。医生确定,张昱一定是百草枯中毒,赶紧做了肺部CT,结果显示整个肺已经严重纤维化。
医生让张昱马上转急诊科,这病不好看,随时要命。
张昱去了急诊科,但心想可能也没这么严重,或许是医生在吓唬他。急诊科刘主任让他赶紧通知家属,并重新抽血、留尿作毒物鉴定。
最终毒物鉴定结果显示确实是百草枯中毒。
问题是,毒物来源是什么?病人没有接触史,像张昱这种极度配合的病人,也不像是要自杀的人。洗胃后从胃液里也没有检测出百草枯残留,但血液中百草枯残留却出奇地高。
正疑惑着,张昱的妻子李晴来到了急诊室,身材好,皮肤白,面目清秀,说话柔声细语,给人感觉是个绵羊般温顺的女人。
刘主任心想,这女人真可怜,年纪轻轻就要经历丧夫之痛了。
百草枯中毒,病情大多呈渐进式发展,病人前期看似活蹦乱跳,三天内肺、肾、肝、心脏等脏器就会相继出现损害,七天内出现肝功能异常等肝损害表现,甚至出现肝坏死,接着会出现迟发性肺纤维化,最终死于呼吸衰竭。
而张昱来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肺纤维化,估计也就三五天时间了。
在向家属交代病情时,李晴问刘主任还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就一定不会放弃。刘主任说:依现在的病情,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肺移植。
但2017年全国见报道的肺移植仅两百例,一例手术不仅费用超百万,还要有合适的肺源,怕是来不及了。李晴表示,钱她可以想办法筹,请主任一定帮忙联系。
但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刘主任心间:夫妻双方都生活在城市,也不在化工厂或者农业部门工作,照理说没有接触百草枯的机会,张昱为什么会百草枯中毒,并且完全符合经皮慢性中毒的症状?
这个看似急切的妻子,不一定那么简单。刘主任选择了报警。
警方介入后,在张昱租房的淋浴水箱里发现了百草枯残留,并在卫生间柜子里发现了被撕掉标签的百草枯空瓶。所有证据都指向了李晴。
后来,从警察那儿得知,夫妻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从农村到城市打拼。张昱不仅好吃懒做,还有赌博恶习,每每输钱后便喝酒,喝多了便回来打老婆。
为了维持自己的恶习,居然打算让老婆去卖淫,自己当皮条客。李晴几次想离开,他又威胁说只要敢离开,就找她的家人报复。
温顺善良的李晴,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决定铤而走险,找来百草枯,每天加几滴在淋浴水箱里,长达几个月之久。
住院的第三天,张昱死了,死于呼吸衰竭。他死的时候,会想起什么?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还是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我想起了尼采那句,当你凝视着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 注:本文节选自王戈多《医院是座动物园》)










![[集市好物]2011 Volkswagen Jetta](https://storage.51yun.ca/auto-car-photos/67ebe288-07f8-4b6c-a248-67608eb673b9.800x6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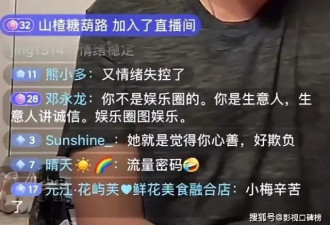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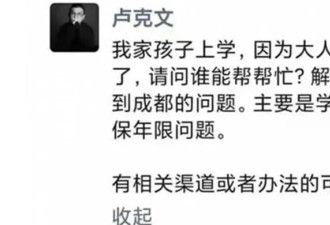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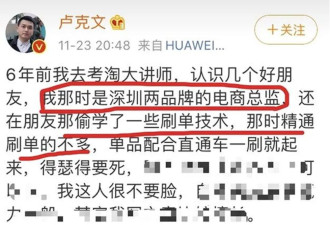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