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休拉·勒古恩:美国人为什么害怕龙?

本文作者厄休拉·勒古恩
这篇文章原本打算讲一讲奇幻,但我最近感觉奇幻不起来,定不下该讲什么,所以一直在骚扰别人,从他们的脑子里发掘点子。“说说奇幻吧?来点跟奇幻有关的。”于是,我的一位朋友说:“行,我跟你说点奇幻的。十年前,我到某某城市的图书馆,去儿童阅览室借《霍比特人》,图书馆员告诉我说:‘哦,那本书只在成人书库有;我们认为逃避现实对儿童不好。’”

《霍比特人》
这事让我朋友和我哭笑不得了好一阵儿,我们都同意,过去这十年间,情况已经改变了很多。如今,在少儿图书馆里,这类对奇幻作品的道德审查已经很罕见了。但是少儿图书馆变成了沙漠里的绿洲并不意味着沙漠已经不复存在。那位图书馆员口中的观点仍然存在。她只是相当忠诚地反映了某些美国人性格当中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种对奇幻的道德厌恶,这种反感不仅浓烈,而且常常攻击性十足,这使我觉得它本质上脱胎于恐惧心理。
所以美国人为什么害怕龙?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说,害怕龙的不只有美国人。我怀疑几乎所有高度技术化的人群都或多或少地反感奇幻。有很多国家的文学在过去几百年里是没有成人奇幻传统的,比如法国。不过反过来讲,我们还有写过很多奇幻作品的德国人;以及英国人,他们不仅有奇幻,而且热爱它,写得也比别人都好。所以这种对龙的恐惧不仅是一个限定在西方或技术文化当中的现象。但我不想涉足这些宏大的历史问题,我要讲现代美国人,我唯一足够熟悉的群体。

《尼伯龙根之歌》

屠龙英雄齐格飞
在思考美国人为何害怕龙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有很多美国人不单是反感奇幻,而是完全反感虚构。生而为人,我们倾向于轻视所有出自想象的作品,要么认为它们不可信,要么认为它们卑鄙粗俗。
“我妻子看小说。我没时间。”
“我年轻时读过科幻之类的东西,但现在自然是不读了。”“童话故事是写给小孩儿的。我生活在真实世界里。”
是什么人在说这种话?是什么人在用这等自信来鄙视《战争与和平》《时间机器》和《仲夏夜之梦》?恐怕正是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男人——勤奋工作的三十多岁的美国男性——那些掌管这个国家的男人。
这种对虚构艺术的全盘拒斥与几项美国特质有关:我们的清教主义,我们的工作道德,我们的利益头脑,甚至我们的性传统。
阅读《战争与和平》或《魔戒》说白了就不是“工作”——你是为了享乐才去读的。而如果阅读无法被解读成“教育性”或“自我提升性”的活动,那么,在清教的价值体系里,它就只是自我放纵或逃避现实,因为享乐对清教徒来说不是价值,恰恰相反,是罪恶。

《魔戒》
同样地,在商人的价值体系里,一个行为若是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就毫无正当性可言。因此,只有英语老师才有理由去读托尔斯泰或托尔金,因为他靠这个挣钱。不过,我们的商人倒是有可能会允许自己去偶尔读读畅销书:不是因为书好,而是因为它畅销——它成功了,挣到钱了。在钱庄主人那颗古怪的头脑中,这证实了其存在是合理的;而通过阅读,他或许也能从其成功当中分一杯羹。顺便,如果这都不算魔法,我也不知道什么算魔法了。
最后一个要素——和性有关的这点——要更复杂。我希望我这么说不要被解读成性别歧视: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认为这种反虚构的态度基本上是男性特有的。美国男孩和美国男人常常被迫去拒斥特定的美德,拒斥特定的人类天赋和潜能(我们的文化将其定义成“娘娘腔”或“孩子气”),借此来确立其男子气概。而一个冷酷的事实是:对人类来说绝对必不可少的想象力就是其中之一。

考察到这里,我赶快去查阅了一下词典。
《简编牛津英语词典》写道:“想象[1]。①设想或者塑造一个无法切实感知到的精神概念的行为;②对尚不存在的行为或者事件的精神思虑。”
很好。毫无疑问,我可以认为“对人类来说绝对必不可少”是站得住脚的,但我必须缩小定义的范围,以适配我们当前的话题。论及“想象”,我个人指的是心智在知性和感性层面的自由嬉戏。“嬉戏”意为消遣,意味重新制造,是组合已知的事物来创造新事物。“自由”指的是行为不带有直接的盈利目的,而是自发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心智的自由嬉戏背后没有目的,没有长远目标。并且这长远目标也可能是非常严肃的目标。孩童想象力的嬉戏活动显然是在练习成人的行为和情感。不这样做,小孩儿就不会成熟。成年人心智自由嬉戏的成果,则可能是《战争与和平》或相对论。
尽管如此,但是自由并不是信马由缰。应该这么说:想象的纪律实际上可能是艺术和科学不可或缺的方法或技巧。是我们的清教主义坚持认为这种纪律意味着压迫或惩戒,从而混淆了是非。依照正确的词义,对某事施以纪律并不意味着压制它,而是训练它——鼓励其发展,促其发挥效用,收获硕果。不论对方是桃树还是人类的心智,都一样。
我认为,有相当多的美国男人所接受的教育都恰恰相反。他们接受训练去压制想象力,将其斥为孩子气或娘娘腔,说它没有裨益,还可能罪孽深重。
他们被教导要畏惧它,却从没学习过要如何规训它。
说到这里,我很怀疑想象力能否真的被压制住。一个在童年彻底根除了想象力的人会长成呆瓜。就像我们所有的不良习性一样,想象力会自然生发。但它若是被否定,被轻视,就会狂野生长,一发不可收拾,会畸变。往好了讲,它不过会成为自恋的白日梦,往坏了讲,则会变成痴心妄想,如果被当真,就会非常危险。就文学而言,在清教徒主导一切的那段遥远岁月中,《圣经》是人们唯一获准阅读的书。而在我们如今的世俗清教观念之下,人若是因为阅读小说违背人性,或是因为小说不真实而不去读它们,则最终很可能会去看血腥的侦探惊悚电视片,读商业写手产出的西部小说或者体育小说,或是投身色情,从《花花公子》一路堕落下去。是他饥渴难耐、渴望滋润的想象力逼他这样做的。但他可以为这些娱乐活动辩护,称它们都是现实的——毕竟,性是真实存在的,罪犯也是真实存在的,棒球运动员也是真实存在的,牛仔也曾经存在过。此外,他还会辩称这些活动够爷们儿,意思就是女人对这些不会感兴趣。
这些门类的作品干瘪贫瘠,空洞得令人绝望。但这并非一种缺点,反而会令他感到安心。如果它们确乎是真实的,即它们发自真诚的想象,想象力十足,他就要害怕它们了。虚假的现实主义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逃避文学。而逃避现实的终极读物,或许非每日股市报告这全然脱离现实的巨作莫属。
那我们这位男人的妻子又如何呢?大概没人会要她为了在生活中扮演被期待的角色而压制她的私人想象力,但她同样也没学过该如何规训它。她可以读小说,甚至读奇幻小说,但她缺少训练和激励的幻想很可能会去饕餮那些恶心的饲料,诸如肥皂剧,“真爱”之作,护士小说[2],还有历史悲情小说,以及各种胡话连篇的东西,而非真正拥有想象力的作品。这些东西出自廉价的艺术作坊,这些作坊诞生于一个极度猜忌想象力之功用的社会。
这样一来,想象力还有何用?
看吧,我觉得我们这儿有一种恐怖的现象:一名勤恳、正直、负责任的公民,一位完全成熟的受过教育的人,会害怕龙,害怕霍比特人,怕妖精怕得要死。很好笑,但也很恐怖。有什么事大错特错了。我不知道该如何纠正它,只能尝试实实在在地回答这人的问题,尽管他问问题的语气常常富有攻击性,饱含轻蔑。“这些东西哪里好了?”他会说,“龙和霍比特人还有小绿人,都有什么用?”
不幸的是,他是听不进去最直截了当的答案的。也没人会和他说这个。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它们的作用是给你带来快乐和欢愉。”
“我没时间享乐,”他打断我,吞下一片美乐事药片来治他的胃溃疡,然后赶去上高尔夫球课了。
所以我们再来试一试不那么实诚的答案。可能也没多少作用,但也必须要说出来:“幻想小说可以帮助你加深你对你的世界、你的同胞、你自身的情感,以及你的命运的理解。”
对这个回答,恐怕他会反驳说,“你看,我去年涨了薪,正在努力让家人过上最好的生活,我们有两辆车和一台彩色电视机。我对世界的理解够多了。”
他说得对,毋庸置疑,只要那些是他想要的,而他别无所求。
你阅读一名霍比特人试图将一枚魔法戒指投入一座幻想出来的火山里,从这样的问题当中收获的东西,与你的社会地位、物质成功或收入都没有关系。事实上,就算是有关系,也是负面的。幻想和金钱呈负相关。这是一条法则,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勒古恩法则”。如果你想为勒古恩法则找一个打动人心的案例,不妨驾车捎上一位除了一个背包、一把吉他,一头靓丽红发,一张笑脸和一根竖起的拇指外别无所有的街头客。无需多久,你就会发现这些流浪者读过《魔戒》——有的人甚至能复述书中的台词。但再想想亚里士多德·欧纳西斯[3],或者J.保罗·盖蒂[4]:你会相信这些人在任何年纪,任何场合,与霍比特人有任何瓜葛吗?

亚里士多德·欧纳西斯
再把我的这个案例延伸一点,离开经济学领域:你是否注意过,欧纳西斯先生、盖蒂先生,以及所有的亿万富豪在他们的照片里的满面愁容?他们那怪异而清瘦的面孔看上去就像是在挨饿,仿佛他们在渴望什么,丢了什么东西,在思索它可能在哪儿,抑或它是什么,他们究竟丢掉了什么。
有没有可能,他们丢掉了自己的童年?
至此,我得到我对想象力之功用,特别是它在文学领域,特别特别是在童话、传说、奇幻、科幻和所有处在疯狂边缘的领域之功用的辩词了。我相信成熟并非因成长而舍弃事物的过程,而是不断积累而成长的过程;我相信成年人不是死掉的孩子,而是幸存下来的孩子。我相信成年人类的优秀能力在孩童时期便已存在,而这些能力如果在年轻时得到鼓励,便会在成年时发挥出色的作用。但它们若是在童年遭到压制和否定,则会损害成年人的人格。最后,我相信,在这些能力当中,最有人情味,最人道的便是想象力,因此,激发我们的孩子们的想象力,给予它最好、它所能吸收的最纯粹的养料,使之像绿色月桂树一样自由成长,是我们身为图书馆员,身为教师,或是家长、作家,抑或仅仅是成年人的快乐的责任。
因为奇幻当然是真实的。它并非事实,但它是真实的。孩子们懂。成年人也懂,这正是为什么很多成年人会害怕奇幻。人们知道幻想的真实性挑战了,甚至威胁到所有的虚假之物,所有那些生活中被迫维系着生存,却是伪造、多余且浅薄的东西。他们害怕龙,因为他们害怕自由。
所以,我们应该信任我们的孩子们。儿童一般不会把真实和幻想混为一谈,他们比我们成年人更难混淆它们(正如某位伟大的幻想家在《皇帝的新装》中所指出的那样)。孩子们很清楚独角兽不是真的,但他们也知道一本讲述独角兽的好书必定是真实的。这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超出了爸爸妈妈的知识范围,因为成年人否定自己的童年,也因此否定了自己的一半知识,徒留悲伤、枯燥而微不足道的事实:独角兽不是真的。而没人能从这点儿事实中得到一丁点儿的收获(另一位伟大的幻想家创作的《花园里的独角兽》[5]是个例外,这篇作品表明,执着于独角兽不存在可能会把你径直送进疯人院)。恰恰是经由“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龙”或“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这样的陈述,正是经由这些美丽的非事实,我们这些满脑袋奇思妙想的人类才得以用我们独特的方式抵达真实。

《花园里的独角兽》
译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4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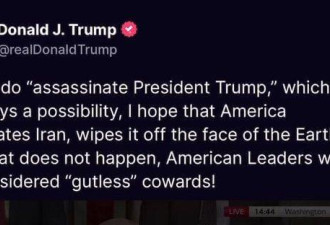

![[集市好物]沙发床](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8aee8aa1-f198-425a-88c9-f2eef9289aeb.1080x810.jpg)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