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深漂第一站,和他们消失的家园....

2019 年 6 月,号称“旧改航母”的深圳白石洲旧村改造项目启动,震动了 8 万 3 千名外来租户的命运。
白石洲位于深圳南山区的中心地段,紧邻世界之窗与深圳湾公园,是深圳市密度最大的外来居民聚集地。这片 0.6 平方公里的城中村排布着 2527 栋出租屋和 2310 家商铺,汇集了 14 万居民,其中大多数为来深务工人员[1]。这个深圳最大规模的旧改项目不仅牵动着城市命脉,更改变了在此处落脚和扎根的租户们的生活轨迹。
“城市更新”项目启动后,居民和商铺陆续收到清户清租通知:“2019 年 9 月 15 日前,结清房屋租金、水、电灯费用,凭押金单收回租房押金后,清空搬离本楼。”数万住民开始举家迁移,部分学生上学也开始受到影响,清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白石洲合计减少 28731 人[2]。与此同时,搬不出去的人面临着更大的困境:有些人为了盘下白石洲的一家商铺卖掉了老家房子,而现在他们同时失去了生活居所和谋生工具。
一个跨专业的“新流动”研究小组在这一期间自发成立。他们一边与受旧改影响的群体共同行动,从民间角度表达对于改造公共空间的意见;一边对行动中结识的白石洲租户、商户、业主、行动参与者展开访谈和研究,最终完成了一份长达 20 万字的报告。
这份报告极其难得地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在城乡关系、家庭组成、性别、宗教、户籍,甚至“个人成长”和“情感”等领域均提供了个案研究,它让人看到一场旧改涉及的利害关系可能是无远弗届的。如果旧改没有发生,这些原本生活甚至扎根在自己轨道上的个人和家庭,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不一样的成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这个社区也可能通过实践让自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样本。
单读从这份报告中摘录了部分文章与大家分享,首篇《从“他们”的白石洲到“我们”的白石洲》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以社区营造和艺术实践为线索,探究白石洲旧改的具体问题,以及在具体问题中人的处境。今天分享的首篇文章的上半部分,就从这些以具体的行动参与社区营造的人们说起。

从“他们”的白石洲到“我们”的白石洲(上)
撰文:东启
早在 2019 年以前,白石洲的旧村改造便在酝酿中,对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各方观察者也早就开始了各自的行动。
2005 年,深圳市和南山区政府便开展了白石洲旧村改造研究。2012 年,曾任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的黄伟文发起了“城中村特工队——1 号行动:白石洲”,尝试以规划/建筑业界学术课题的形式介入白石洲社区。这之后,实验艺术组织“握手 302”、独立建筑事务所“都市实践”、独立建筑实践小组“白石洲小组”等专业群体,都在试图通过实践、研究来论证白石洲作为一个有机空间的难能可贵,或是提出整体拆除重建之外的方案。
为什么一个城中村的旧改前后,会吸引这么多的目光,尤其是来自民间的多方关注?这里就要提到深圳城中村的前世。1980 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早期的深圳特区建设,工业化要超前于城市化,大多通过“三来一补”[3]建设工厂、进行生产。政府开始从当地农民那里购买大片农田,这些农民没有土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但仍然拥有自己的村庄,各村成立股份公司,农民变成股民,过去的农田也纷纷变成工厂区。在此过程中,新发展起来的工商业需要大量社会服务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临时住所,靠近此区域的村落便开始改造扩建,城中村慢慢形成。随着城市化对环境的要求,工厂开始外迁,新一批来深圳从事服务业的务工人员,需要廉价且离雇主位置相近的住所,所以像白石洲这样的城中村逐渐演变成建筑密集且交通便利的廉价出租公寓群,白石洲也因此得名“深漂第一站”。
白石洲的关注者中,不乏参与深圳早期城市建设的建筑师与规划师,城中村和深圳早期城市发展的关系,他们正是见证者和参与者。2012 年左右,他们纷纷转向关注城中村的保育,这既是对城市空间多样性的探索,也是对自己过往职业的反思。

根据白石洲学童家庭采访的词频分析生成的白石洲卫星图,字体越大代表词频越高
01
湖贝 120 城市公共计划
说起白石洲,就不得不提深圳的另一个城中村——湖贝古村,不仅因为湖贝古村于 2016 年同样陷入旧改的命运,更是因为在这一旧改项目上,深圳不同职业的人,包括建筑师、艺术家、创意人士,首次提出了保护计划,发起了集体实践。当时在白石洲进行社区营造的“白石洲小组”成员也加入了这次行动,并发出倡议:“我们是白石洲小组的成员,但是我们也关注深圳其他城中村的发展及其对于城市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老城文化得以延续。”同样延续下去的,还有关注城中村并集体实践的工作方法,这为日后白石洲的实践打了样,激活了社群通路。
湖贝古村的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 年),原住民世代相传的文化已有 546 年的历史。这里仍然保留三纵八横的村落结构,清嘉庆九年(1804 年)重建的宗祠耸立于此,门楼、水井和 200 多间民居都是典型的广府系坊巷式排屋村样式,在这些古民居的低矮门头上还可以看到清代的灰雕。

湖贝工作坊现场(朱锐/摄)
2016 年 7 月初,一批设计师、规划师携手不同领域的学者和艺术家发起的“湖贝古村 120 城市公共计划”,进入了深圳公共视野。紧接着,一批建筑师、学者、艺术家和致力于改变“被动接受城市旧改”的人士发起了“湖贝共识”联署行动,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到保护湖贝古村的“湖贝 120 城市公共计划”行动中。专业建议、公共艺术、社区参与、个人参与在行动中以组合搭配的形式出现。参与行动的人希望“湖贝 120 城市公共计划”能成为探索公众参与的实验案例,所以仅仅依靠学界和知识精英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将学术材料、专业的建筑规划信息等以通俗可感的方式向大众翻译,在翻译与传递的过程中让市民意识到原来城市更新和规划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以期慢慢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公共参与机制,为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介入城市规划提供可能。

“湖贝古村 120 城市公共计划”主题海报
2017 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邀请“湖贝古村 120 城市公共计划”在主展场举办专题展,“湖贝计划”也借机继续推进“抢救湖贝”行动,并把展览当作一次将实践进一步和公众连接的机会。展览的题目为“湖贝,生死进行时——城市更新迷宫的第三方公共参与攻略”,展览现场用直观、感性和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了自“湖贝”变成一块“肥肉”之后,围绕“她”的生死存亡展开的民间抢救行动的全貌。
这个展览汇集了尽可能多的第三方公共领域贡献的智力、心血和希望,这些机构和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可以转化为观众的指南和参考,他们的故事也将激发大家投入到公共参与行动中来。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展览,不如说这是一个“城市更新迷宫的第三方公共参与攻略”。这些真实的例子能够传递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你是一个有诉求的人,随时都可以开始你的实践,你并不是这个城市中唯一持不同观点的人。
作为一个新型移民城市,湖贝古村被人敬称为“深圳祠堂”,而保护这样一座具有历史记忆的“湖贝古村”,是流动到深圳的人通过参与公共事件完成了对共同体“仪式”的体验。这种“共同体”的塑造不同于流传社会的“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这句“招工宣言”更多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而没有考虑到人之为人,除了舒适的生活外,还需要收获尊严与价值感——我们需要和自己的过去、城市的过去取得某种从空间到情感的联系。

2024 年湖贝古村仍处于半开发阶段(东启/摄)
02
连接一切——白石洲社区营造
在对湖贝古村的保护中,“白石洲小组”习得了丰富的社群经验,并将此逐渐运用到相对微观的白石洲社区营造中。2016 年 6 月,白石洲小组成员发起了面向白石洲孩子的公益摄影工作坊“童眼白石洲”,期望在学校正规教育之外的课程中让孩子自主表达,通过相机和孩子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白石洲。对于白石洲的孩子来说,缺乏作为来自深圳务工一代的父辈陪伴是一种常态,而公益课程希望能形成一种陪伴机制。
除了着眼于白石洲的孩子,租客、业主的问题观察,白石洲居民与不同社群的连接也是“白石洲小组”的工作方向。在白石洲步行街的酒吧内,“白石洲小组”邀请客家民谣朋克“Lazy Cat 懒猫”和塞尔特民谣朋克乐队“Patti Mayonnaise 啪体·妈内色”举办了“白石洲——走心民谣朋克 live”,音乐会对白石洲居民一律免费。
“白石洲小组”还联合教育机构发起城中村寻宝方案,与精酿啤酒屋、纹身店等白石洲店铺的经营者合作,结合店铺的经营业务及自身特性,把他们的店铺变成美术馆,租赁他们铺面的卷帘门及室内墙面作为展览空间,在展览店铺的经营内容的同时,也展览城中村保护的实践方法、城中村记忆,让作品融入商铺中,使每个店铺的老板成为美术馆馆长,艺术通过“寄生”在城中村形成一种不同的社群交流方式。

白石洲小组成员面向白石洲孩子的公益摄影课
在深圳其他城中村中,“白石洲小组”还协作“重 D 音”工人乐队策划了横岗上围老村家湘味概念粉店,将粉店食物流动的质感和周遭的流动人口、流动的社群关系关联起来,利用涂鸦对“流动性”进行可视化表达。这些都和具体的空间有关,当然也和抽象的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一位“白石洲小组”成员所说:“好的建筑会解决社会问题,规划及建筑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才出现的专业分工。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形式背后看不见的东西。”
03
当常态化的社群成为紧急时刻的力量
2016 年,“白石洲小组”作为独立建筑实践小组参与“居民项目”,这是一个针对珠三角地区的社会性艺术实践项目,着眼于居民权益与居民生存空间的微观政治考察,进行相关的自组织活动。项目试图建立“第一现场”,邀请不同的实践者在社会空间中展开自己的工作。
“看不见的深圳人”是“白石洲小组”参与“居民项目”的主题,他们在项目自述中说道:“我们关心的是那些在白石洲底层的、没有文凭、目不识丁、没有户籍所以完全被隔绝在当代教育体系外的、从非工具化培训机制出来的人们。‘多余的人’‘没用的人’‘社会包袱’这些形容他们的词语也许会进入到我们头脑中,但尊重和体谅他们,向他们学习,才是我们作为‘人’而不是‘工具’的底线。关于‘人’和‘工具’分界的讨论,让我们想到今天越来越多人将‘土地’异化为‘资产’。最早土地和人的关系包含泛宗教化的习俗、宗族关系以及原乡的情感,但是随着城市的机械化及城镇化开发,越来越多人丧失了‘土地’——除了土地的所属权之外,人和土地之间的多维关系也被一刀截断。居住在白石洲的打工者有不少来自农村,他们在农村已经经历过一次土地的丧失,城市化将他们从农村驱赶到城市;而在城市中,因为‘城市更新’,他们再次丧失了对空间的权利。”


“白石洲—城中村不拆”签名拍照(部分)
在“看不见的深圳人”项目中,“白石洲小组”发起了“白石洲—城中村不拆”签名拍照活动,一个个来自白石洲的居民手持书写“不拆”的小黑板,站在白石洲的建筑前留影。
在与“看不见的深圳人”平行开展的“身边的城市系列”项目中,“白石洲小组”针对白石洲城市更新的规划方案,以及数量庞大的商户租户未能参与赔偿谈判的情况,进行了公共意见征集。白石洲居民在打印好的“白石洲城市更新规划方案意见反馈签名表”上,填上自己的姓名、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复印件。然后“白石洲小组”将收集好的材料邮寄至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南山管理局。 “白石洲小组” 希望在政府提供的流程框架外,从民间角度发起一个针对白石洲的公示意见搜集。不论你是租户、村民、商贩,还是白领、建筑师、规划师、开发商、官员、学者、艺术家,不论你支持旧改,还是对目前的旧改模式抱有怀疑或批评的态度,都可以提出意见。


“白石洲拆/不拆展”摄影展现场
沟通途径的建立亦是“白石洲小组”实践方法的建立,除了寄信、举牌拍照外,“白石洲小组”在白石洲的街头举办了一场“白石洲拆/不拆展”摄影展,将白石洲的现状以影像的方式展示在街头,和居民及来往的人直接见面。从布展到撤展总共用了半小时左右,布展加展览只持续了 25 分钟,而“撤展”只用了 3 分钟。这种快闪式的展览及其结果反证了白石洲旧改的问题。对于“白石洲小组”来说,展览是他们行动的一部分,用街头展览占领空间,宣示了居民对于空间的权利。
在创造事件之外“白石洲小组”会在日常中将自己作为白石洲的眼睛和传声筒,会像一个“闲逛者”一样收集白石洲街道上有多少小吃摊位,有什么特色小吃,老板都来自哪里;也会在第一时间对发生在白石洲的权益事件进行报道,包括在白石洲经营多年的美容院被拆,翡翠服装城三楼及华顺堂盲人按摩店在拆除中被砸等案例。而在疫情中,“白石洲小组”观察到,封闭围挡使得依靠街面生存的街头大排挡、算命摊、三轮车搬运、裁缝、手机贴膜、装修工等在沙河街边谋生的摊档完全没有了生存空间。村外的顾客无法进入白石洲,白石洲内外的经济交流更是被切断了,譬如华侨城、侨城豪苑等商品房小区的居民不能进入白石洲购买便宜的商品和服务,白石洲的清洁工也不能进入商品房小区进行小时工服务。那段时间,白石洲的饮食行业只能依靠外卖维持生计,其他行业只有本村居民消费,基本处于无收入状态。像纹身、酒吧、理发等行业的顾客基本是村外的客户,他们进不了村,店铺就无人光顾,只能靠吃老本生存。
为什么“白石洲小组”作为一群不在白石洲生活的建筑师,可以持续和这里的人产生交流,创造事情?不仅因为他们关注白石洲的空间政治、权益问题,他们也并非将白石洲的往来人事当成进行思辨和批判的材料,而是设身处地地和当地人交朋友,关心彼此的生活,甚至当地人有困难的时候,利用之前串联起来的社群,围危救困,伸出援手。
“白石洲小组”在得知生活在白石洲的 L 大姐的孩子出生不久却患病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了募捐活动。“白石洲小组”在募捐推文中写道:“这是一位白石洲的刚生完孩子的妈妈的困境与请求,一切为了孩子,请大家支持!认识这位大姐三年了,她在白石洲自己经营一个小摊档,辛苦勤劳而又实实在在地在深圳扎根生活。由于她是高龄生第一胎,同时还面对种种生活压力,小孩早产,不足二斤,医疗费用奇高,不得已求助社会。”这是生活在白石洲的一个普通移民的困境,一面是白石洲城中村正在拆迁,生活和工作都面临动荡,一面是不足二斤的早产儿刚来到这个世界就住进 ICU 病房,需要昂贵的治疗费。”

白石洲的精酿酒吧“百优”也响应了捐款行动
2019 年 9 月 14 日—10 月 8 日期间,不同渠道总共筹款 60937 元,帮助次数 1738 次,平均捐款 35.06 元。捐款结束后,“白石洲小组”成员写道:“我看到了城中村的命运共同体,新闻说白石洲将要诞生 1878 个亿万富翁,但我记住的是向 L 大姐捐款的 1738 个白石洲老乡。”

马师傅参与“白石洲—城中村不拆”签名拍照
扶危救困的行动也发生在马师傅兰州拉面馆的拆迁事件中。马师傅来自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马师傅的父亲除了种地之外,主要的生意是贩牛,但马师傅觉得自己的身体和性格不适合干贩牛的营生,所以 2013 年从老家来深圳打工,在来深圳之前他也曾考虑过去江苏、浙江发展,但感觉深圳更加繁荣,可以赚到钱,就决心来深圳做拉面生意。
马师傅刚来深圳的时候,曾在一家拉面馆打工,有了一定的积蓄后,他决定自己创业开兰州拉面馆,于是马师傅一有时间就四处考察店铺,最后看中了白石洲一家要转手的店铺。在决定接手这家店铺以前,马师傅结合之前打工的经验与考察的结果算了一笔帐,在白石洲经营一家牛肉面馆每月至少有一万块的收入,做几年再把店铺转让出去,还是可以赚不少钱的,而且他还可以把太太和两个儿子从家乡接来团聚,大儿子未来可以帮忙经营店铺,小儿子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店铺转让的费用要 20.5 万元,但是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马师傅朝老乡借了一部分钱,又卖掉了家里的宅基地,2013 年 5 月 10 日盘下店铺开张。可惜好景不长,2016 年 3 月收到拆迁通知,2016 年 9 月断水断电。9 月份几乎所有的租户都走了,马师傅是仅存的一户。这里要说明的是,他坚持不走,不是因为和拆迁单位有什么矛盾,而是他们一家人确实无处可去,前几年的生意所得基本上在偿还之前的借款,卖掉在家乡的宅基地,也切断了他在家乡的根。

胖鸟兰州拉面微店界面
马师傅因为不是业主,也就不会有拆迁的补偿,走投无路的他在朋友的微信群中,甚至透露了轻生的信号。马师傅需要一笔资金重整旗鼓,救事也救命。
2016 年 9 月 15 日中秋节下午,戏剧导演/湖贝 120 的发起人之一胖鸟杨阡通过 G+ 平台发起捐款 。2016 年 9 月 17 日晚 20:39,胖鸟杨阡兰州拉面微店开张,发出“吃面人召集帖|让马师傅给你做碗面吧”的帖子。对于马师傅来说,“他不反对城市更新,但不应该让他成为牺牲品”。然而,马师傅因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坚决拒绝了微信的慈善捐款。所以胖鸟杨阡想到马师傅之前梦寐以求的社区公共项目——“请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吃上他做的面”,于是富有烟火气息的消息在那年的中秋通过 G+ 平台传递了出去:“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拿出你在中秋节打算给家人或者朋友买月饼以及礼物的钱,帮助马师傅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愿望——请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吃上他做的面。我相信你的朋友和家人不会反对你帮助实现这个梦想的决定。我们活动的起始报名费是 10 元,一碗牛肉拉面的钱。而如果你想多给,没有上限。”
这个活动在 15 日下午由 G+ 机构推出,不到 5 个小时,就卖出了 3 千多碗“牛肉面”,胖鸟杨阡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师傅和他的家人之后,他的太太泪流满面,因为她知道马师傅有活路了。他的小儿子则跪在路边祈祷,保佑所有的好心人。然而就在此时,胖鸟杨阡的活动因“意外原因”突然被下架了,G+ 的负责人打来电话解释,最后还说:“再次表达抱歉,我个人捐赠 1000 元,支持这个面店。感谢老师的理解。若后续有任何决定,可以提前通知我们,协助你们实施。”
当初胖鸟杨阡选择 G+ 平台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它是非常透明的第三方托管平台,所有人的面款都不会和发起人有关联,而是由 G+ 机构在活动结束后转交给马师傅一家。但是这个扶危济困、帮助弱者重新创业的项目,却遭受下架停售。因此,胖鸟杨阡不得不开设一个微店,目标金额 18.6 万元,一万八千六百碗兰州拉面的费用。2016 年 9 月 17 日晚,兰州拉面馆还举办了兰州拉面音乐之夜,让围观拥有了音乐的气氛,或许这也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陪伴感。

兰州拉面音乐之夜
可以说胖鸟杨阡开设的兰州拉面微店,是一个线上线下互动的参与式剧场,马师傅在废墟中的兰州拉面店和线上的兰州拉面店,彼此投影,相互观照,观众既通过马师傅的遭遇对旧改一叶知秋,也通过捐赠让自己从观看者变成一个参与者。旧改的“挖机”轰隆隆向前一寸,一碗碗虚拟的兰州拉面争分夺秒抬高一尺。2016 年 9 月 19 日,马师傅获得补偿,兰州拉面馆被拆除。9 月 21 日胖鸟兰州拉面微店谢幕。

东北菜馆的张姐是白石洲项目的同行者,2019 年后东北菜馆变成了大家聚会的首选,和张姐的聊天话题也从旧改多了些家长里短。
在白石洲的实践中,我们的合作者有杂货店店主、饰品店店主、互联网创业者、餐饮行业从业者、散工、网约司机、快递骑手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商铺主参与合作?这里有两重原因,第一重和它的空间属性有关,美国社会学家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曾提出过第三空间(Third Place)的概念,他称家庭居住空间为第一空间,职场为第二空间,将在宽松、便利的环境中可以自由地释放自我定义为第三空间,比如酒吧、咖啡店、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这个概念被逐渐演绎为现代商业业态的战略规划,全球连锁的咖啡店星巴克就依此指导自己在社区中的定位和店面的空间设计。白石洲有酒吧,咖啡店没几家,其他公共空间几乎没有,杂货店、凉茶铺、大排档、快递小站等个体户的门脸(建筑中的灰色空间)和半开放的就餐环境就成了社区的第三空间,相较于城市商业综合体中的第三空间,白石洲更加开放,路过街边的聚会和酒局,即使不去消费,也可以和话题投机的食客或店主聊上几句,说久了,人多了,也就渐渐成为松散的论坛,久而久之,人情的连接逐渐产生,白石洲大大小小的铺面也就发挥着社区非正式公共空间的交流作用。
另一重原因即自白石洲清租以来,各路实践者通过艺术、写作、情感支持、捐助等方式和白石洲居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私人信任关系,不仅仅是把“他们”当作调研的“目标群体”,更是让萍水相逢的“我们”以朋友相称,一些外来实践者甚至被居民以“兄弟”“战友”相待。“我们”亦可以视为一个跨阶层、跨区域的“社区”或“社群”。




![[集市好物]便捷餐椅](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7c8eda13-667b-4295-a2a3-8e3d48b201c8.750x75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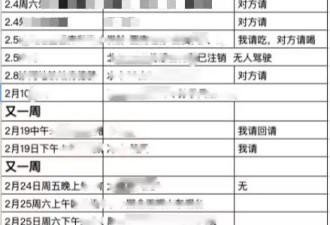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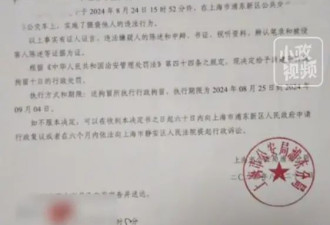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