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混校生”靠打架和谈恋爱成名 把同学堵厕所扇耳光
在这个学校,好像没人敢欺负我。”
初二的杜清在做自我介绍时,着重强调了这一句。我立刻知会了她话里的意思——在这个学校,杜清是女生中的老大。
如果单从外貌上来说,你很难把杜清和“女老大”这个标签联系起来。杜清很瘦,扎着一束马尾,两颗眼睛大大的,浑身散发着一种文静的气质。陈涵形容杜清“笑面虎”,看着很温和,但捅起刀子来最狠。
陈涵说自己曾经喜欢上年级把子的“龙头”,也就是年级帮派中的老大,但是知道杜清也喜欢这个男生后,陈涵果断放弃了。“惹不起,斗不过”,陈涵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杜清的爸爸是‘地头蛇’。”
提到自己的爸爸,杜清显得有些自豪,她坦言自己的父亲曾经是当地镇上的“四大天王”之一,黑白通吃,混社会的几乎没有人没听过她爸爸的名号。即使早已“金盆洗手”多年,但当初的人脉依然保留着,“我爸跟我说过,如果有人欺负我直接告诉他,他找人来教训欺负我的人。”

杜清所在的中学。作者拍摄
杜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是一根羽毛轻轻飘落到水面上波澜不惊。这在杜清看来,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她的世界因为父亲的这层关系,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灰色的社会资本,同时也拔高了她在学校江湖中的地位。学校一些想混的女生故意靠近杜清,想要融入她的生活交际圈,借此共享杜清的符号资本和社会关系。
杜清倒并不是很介意,在她看来,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以及在校园江湖中占据绝对性的优势,“抱团”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抱团和建立帮派不同。相比于具有男性特征的帮派“利益集团”来说,女生的抱团具有非正式性的特征。她们的连接更为松散。女生的抱团带给女生更多的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以此弥补生理武力上的不足,用人数上的优势来彰显自己的权威和强势。
杜清说,自己的小团体现在已经有六个人,但想要加入她们团体的远远不止六个人。杜清有自己的一套筛选标准,对于那些性格懦弱,扛不起事的女生,杜清压根不会考虑。在她看来,如果把这些人纳入团体,只会拉低她们的档次,甚至被别人笑话。
周彤和我说,杜清的厉害远不止于此。杜清正在和年级把子的“龙头”谈恋爱,这个男生既是帮派老大,又练跆拳道,参加过跆拳道比赛,拿了很多奖。“在学校里没有人没听说过”,男生的“不好惹”辐射到杜清身上,自然也就没有人敢惹杜清。
一个随时能够“罩着”自己的父亲,一个具有强势地位的小团体,一个在年级帮派中稳坐“头把交椅”的对象,合力将这个看起来瘦弱文静的女生捧上了校园江湖的“神坛”。
陈涵则和杜清完全不同,她既没有人脉,也没有背景。我第一次见到陈涵,她的班级正在上物理课。陈涵从教室后门溜出来跑到我的面前,笑着说道:“老师,你要想聊天找我聊,我什么都知道。”我用眼神示意她现在正在上课,她依然笑着:“没事,物理老师允许我不上他的课,反正我在班里他也闹心”。
提到杜清,陈涵一脸不屑,直言杜清的“发家史”全靠有一个能干的爹,“离了她爸,杜清什么也不是”。而对于没有背景的女生来说,要想混,或者说想要在年级声名鹊起,最快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打架,“耳光扇得越响,名气就越大”。但是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被打的女生报告学校,学校再通知家长,最后总会弄得自己也不痛快。所以,在陈涵看来,第二种方法最安全,也最省时省力——谈恋爱。
而且是和不同的男生谈恋爱。在陈涵的“恋爱史”中,时间最短的一次是中午刚确立关系,到晚上放学时候就分了。
不只是陈涵,周彤也谈过好几次恋爱。她们的择偶标准很简单,一是“长得还行”,二是“有实力”。我问周彤什么叫做“有实力”,周彤眨了眨眼,故作神秘地说道:“就是有人脉,会打架”。换句话说,“就是能给自己长脸”。
恋爱谈得越多,说明女生越厉害已经成为乡镇中学想要混的女生们的一个衡量标准。对于这些女生来说,她们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圈,大家即使不对付但也都相互认识。在这个圈里,谈恋爱是她们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往往有人刚确立关系这个圈子里的其他女生就都知道了。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陈涵所说,“长得不错又有实力的男生一共就那么几个”,所以一般一个女生刚和男生分手,另一个女生就会继续续上。还有可能昨天晚上两人刚分手,今天就又重归旧好。
当然,在乡镇中学女孩们的恋爱坐标中,她们绝不仅仅局限于同一年级的横向延伸,还会把目光投向年级之间的纵向拓展。陈涵自觉自己很聪明,“谈不了本年级的‘龙头’,那我就去和其他年级的‘龙头’谈。”因此,在陈涵的恋爱史中,和初三的年级老大谈过恋爱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它足以让自己在整个学校场域的谈资中声价十倍。

同学们课间聚集在走廊。作者拍摄
其实不仅是女生,我在和一些男生聊天时也会发现,他们对于“面子”“名气”这个东西看得很重——学术上叫做符号资本。成绩好的同学,他们的符号资本自然就是成绩排名。而对于成绩差的同学,怎么挣得面子,能够在年级甚至是校园场域中享有名气,“一炮而红”,男生和女生所采取的方式其实各有不同。
对于男生来说,他们为自己赚取面子的方式就是建立或者加入帮派。被帮派吸纳本身就是一种对能力的认可,而且帮派之间的互斗也是一种男性力量的彰显。
如果说男生是靠武力赚取面子,那幺女生则是通过情感。
在女生混校生(指的是在校园里混的学生)的游戏规则里,情感是硬通货。不论是通过拉小团体,用集体性的力量构建个人的优势地位,还是和有背景的男混校生谈恋爱,情感都是她们的“杀手锏”。
但有意思的是,这里的情感并非都是出于真心。杜清和我说,她们团体六个人也只有在“教训”惹事的人的时候才会“合体”,平时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多时候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
谈恋爱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谈着玩,不是真的喜欢”,陈涵感觉很无所谓。
女生的攻击方式更恐怖?
杜清是踩着上课预备铃的尾巴爬上三楼的。她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面前,略显惋惜地跟我说:“老师,你刚才错过一场好戏”。
见我面露困惑,杜清全然不顾语文老师已经进班,饶有兴致地跟我说,刚才的课间,她和小团体里的另外两个女生把一个初一的女生堵在厕所里,三个人轮流扇那个女生的耳光。
“谁让她背后讲我坏话,还犯贱犯骚,勾引别人的对象。”杜清极为平淡的说了出来。充满成人化和性意味的语句就这么裸露直白地渗进了一个初二女生的话语里。
但这绝不是我听到的个例。其实在杜清扇初一女生这件事之前,我就听到一些男生跟我开玩笑:“我们男的打仗跟女的比起来真不算什么,女生更猛,她们直接扇脸”。
美国作家蕾切尔·西蒙斯在其著作《女孩的地下战争》中指出,女孩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攻击文化,在面对冲突时,女孩们会采取非肢体接触、间接、隐蔽的形式来攻击彼此,比如拉小团体搞孤立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在实地调研中我发现,在一些乡镇中学,女生之间的战争绝不仅仅只是局限于非肢体性的隐形攻击,已经扩展到具有明显羞辱性质的肢体冲突,比如扇耳光。这也是女生的校园暴力最常见的方式。相较于男生的肢体暴力,女生的校园暴力则更倾向于羞辱性,也就是让被暴力的人“没有面子”,或者说是“社会性死亡”。
我问杜清,如果那个女生不去厕所或者去报告老师怎么办,杜清笑着摇了摇头,蜻蜓点水似地说了句:“她不敢。我们会直接到教室门口堵她,她也嫌丢人。她要是敢报告老师,我们就在校外等着她。还有她做出来那些丑事,全都给抖落出来”。
在杜清的视角里,她是主持正义的一方。对方先骂自己,行为不检点,被扇耳光是“罪有应得”。但在陈涵的眼里,就有点儿“全员恶人”的味道了。
“即使初一那个女生骂她,也完全用不着轮流扇人家脸,这样做还不是想炫耀一下自己多么牛吗。”陈涵觉得,像杜清她们故意选在厕所扇别人耳光,就是看中厕所的公共性和人员的强流动性,一个耳光下去,全校皆知,人就出名了。
周彤曾好几次在现场围观过几个女生扇另一个女生耳光的场面。按照周彤的说法,每次在“教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女生在厕所门口放风。一旦有学校老师往厕所方向来,放风的女生就会立刻进去“通风报信”。“扇耳光”这样的越轨行为也愈发变得有组织性和严密性,分工明确,学校的监管手段就在这样的“合作式分工”中被消解。
除了扇耳光,女生之间还有一种攻击方式——带有浓厚性意味的语言攻击。某一次,我和杜清走在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女生,杜清拉了拉我的袖子,然后轻声说了句:“这个女生跟好几个男的上过床”。
陈涵在形容这个女生的时候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我无法考证他们所说是否属实,但是这种直白赤裸的语言已经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对其他女生的歧视不仅局限于校内,一些校外认识或者辍学不上的女生也会难逃“虎口”,成为她们咀嚼的谈资。陈涵和我说,他们级有一个女生辍学不上了,去外地一个多星期,回来之后显摆自己赚了三千多块钱。“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女生,一星期赚三千,肯定是去卖了”。
我深感诧异。性文化在这群初中女生的观念里就这么明晃晃地被涂上了污名化的色彩,成为羞辱别人的利器。此外,这种具有成人世界性质的性语言已经很深地浸透进这些女孩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她们审视、评论别的女生的量度。

杜清和她的朋友。快手截图
但是,更让我惊诧的是她们作为女生,对同为女生的其他人恶意竟如此之大。通过毁坏对方的尊严和面子,从而达到报复的目的。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其著作《厌女》中指出,女性对自我以及其他女性的偏见也是“厌女症”的一种表现。这些乡镇中学的女生混校生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收编进厌女文化中,成为惩罚别人,但可能同时也是困住自己的帮凶。
我问陈涵:“你觉得背后有没有人这么诋毁你呢?”陈涵想了想,然后歪了歪头,“可能吧,无所谓”。
女生更容易自我放弃?
邢老师很遗憾地跟我讲了他之前教过的一个女生的事情。
那个女生成绩不好,也不怎么喜爱学习,但也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学生。有一天,女生家长给邢老师打了个电话,说他们的女儿想要辍学,希望邢老师能帮忙劝一劝这个女生。邢老师好几次把女生叫到办公室,苦口婆心劝她,“哪怕考不上高中,上个中专也能学到一些技术。况且你这年龄这幺小,去外面打工也没人敢要啊。”
但是女生执意要辍学,理由是自己想学美容美发,反正也上不成学,还不如早点出去学点手艺赚钱。后来,女生好几次无故旷课,“家长眼看着她进了校门,不知怎么的人就出现在了台球厅”。实在没办法,家长只能给女生办理了退学。
邢老师想来,还是觉得有些可惜。他心痛的是一个女生为何如此轻易的就放弃自己。况且她的家人还没有选择放弃她的时候,她先亲手关掉了自己的前程。
我在镇上的一家奶茶店见到了李星。三周前,李星和家长签了自愿退学的承诺书,“自愿退学,和学校无关”,便来到了镇上的奶茶店打零工。镇上人对于奶茶的需求没那么大,闲了的时候李星就窝在店里的沙发上打游戏、刷抖音。
零碎的生活伴随着时常袭来的无聊枯燥并没有改变李星的想法。在她看来,自己不适合学习。“一上课就犯困。每次考试都是垫底,学习真的没意思”。
我问李星她的父母是怎么想的时候,李星吸了吸鼻子,“他们比我还想我辍学。他们一心扑在我弟身上。我不读了,他们还可以少花点钱”。李星有一个弟弟,在刚刚过去的月考中考了年级第九。
因此,在父母向李星表达想让她不继续读书的想法时,李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她接受父母的说教:“以后去学门手艺,然后嫁个好一点的人家,女孩子这样就挺好”。
李星现在找了一个男朋友,比她大一岁,初一的时候就辍学了,染了一头黄毛,现在在镇上的一个快递点收发快递。我曾见过李星的男朋友,手臂布满了纹身。当时他在中学门口等学生放学,嘴里叼着一根烟。猛吸几口后,用手掸了掸烟头,一撮烟灰“啪嗒”掉在了地上。

李星。快手截图
教导处主任吴强告诉我,在他处理的退学的学生中,女生比例要比男生高得多。吴主任也觉得有些纳闷,他思来想去,给出的解释是,男生更受家庭的重视。也就是说,男生的性别属性本身就包含了对家庭的责任,男性是家庭再生产的主力军,承担了家庭延续和流动的责任。因此,家长一般不会轻易同意男生退学。
而女生则不同,女性的社会流动很难辐射到整个家庭,从而带动整个家庭“飞升”。当投资与回报不成正比时,家长就会决然地切断对女生的教育投资。
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女生会选择自我放弃?就像邢老师的学生,家长还在尝试着挽救女儿的前程时,女生却先放弃了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为什么有些女生会轻易地接受“女孩读太多书没有用,学门手艺,找个好人家也可以过得很好”这种传统迂腐的观念论调,并把它当作辍学的一个理由呢?
我们或许需要一个答案。
我们,更需要关注乡镇中学的女生群体
我在进入乡镇中学调研的时候,面向的议题是乡镇中学男生帮派问题。我并未把女生群体的问题纳入考量,或者说,我并没有想到女生群体竟然是一个更需要关注的“黑箱”。
是杜清热情地找我搭话,讲诉自己的经历,才慢慢把我引到了这个群体的身上。我无法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篆刻她们每个人的人生画像,但通过她们的只言片语,也足以让我一窥乡镇女孩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对于女生混校生来说,她们叛逆,偷偷谈恋爱,搅动学校秩序,倡导反学校文化,成为校园纪律当之无愧的越轨者;她们善于表达恶意,在厕所扇耳光,背后用成人化的性语言污名化别的女生,用羞辱性质的攻击手段让别的女生“社会性死亡”;同时,她们更容易自我放弃,在学业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更容易抛弃学习,被传统思想规训的同时又反过来自动践行着传统思想,彻底成为小镇生活的“守门人”。
作为一名调研者,我的任务是将调研到的现象事实客观无误地呈现出来,但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多次还是感到错愕与无奈。
我惊诧于她们世界中流行的具有成人化的游戏规则,注重地位、看重面子。但也深感无力,因为好像无法改变她们的观念,也无法挪动她们的人生轨迹。就像我在和李星访谈的最后,尝试劝了一下她,“学校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李星依然麻木地重复着那句“但学习没意思”;就像邢老师在面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辍学的想法后,想尽力拉她一把但被无情拒绝,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走入黑暗。我们看似能做的事情很多,但重重拿起,最后只能轻轻放下,我们又能多大程度影响这些女孩们的人生路线呢?
或许,想找到这些女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可以先看向她们的背后——也就是她们的家庭。
杜清的父亲曾经是“地头蛇”,公然告诉女儿自己有人脉,可以充当女儿的“保护伞”;陈涵和周彤的父母都在外务工,只有爷爷奶奶负责照顾自己;李星的父母则把全部的重心和目光都投向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女儿成绩不佳且出现厌学情绪时不及时干涉反倒“撺掇”女儿退学……这些女孩的家庭教育都是失败的,甚至是空白的。
学校也应该多把目光投向女生“后进生”。当她们挑战教师权威和学校秩序时,要善于倾听她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然后逐步引导她们走出反校园文化。当她们用羞辱性的手段报复别人时,也要恩威并施,既要了解她们这么做的原因,做一名知心的朋友,告诉她们这样做的不当之处,也要给予一定的惩罚,给她们树立“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人生观念。
当然,学校和家庭更需要合作。教育,从来不是学校一方的职责,而是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的事情。在家能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在学校也能感受到老师的关注,或许,她们就会觉得,这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恶意。

某一堂课,班级里的同学睡倒了大半,只有少数同学在听课,作者拍摄
在我结束调研的两周后,陈涵也退学了。听周彤说,是被杜清带人在厕所轮流扇了耳光,“谁让她一直对杜清的男朋友心怀鬼胎,天天想办法勾着他,还在背后说杜清的坏话。她活该”。话音刚落,周彤就开着电动车“呲溜”一下冲了出去,带起了一阵风和阵阵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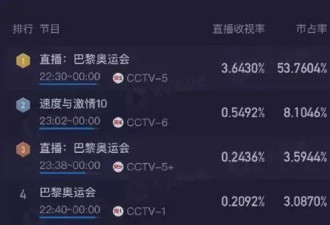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