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90后留学青年谈爱国主义:留美“公知”

当地时间2015年9月25日,美国华盛顿,侨胞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外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016年,蔡英文上台、南海问题升温、特朗普等美国大选候选人对中国的攻击及中美对抗的戏码在国际舞台上轮番上演。中国的爱国主义因为一件件事情,被推向了新的临界点。上月,为抗议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中国十多个小城市发起抵制标志性美国品牌肯德基的示威活动。而本月,在里约奥运会上,因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霍顿获奖后讥讽孙杨是“使用药物的骗子”,中国的年轻网民潮水般涌向霍顿的社交媒体账号,要求霍顿道歉。
网络的沸腾反映了新世代越来越强的声音以及他们之间越来越远的隔阂:“小粉红”与“反华青年”的碰撞;海外的精英爱国者对庞大弱势人群与种种社会弊病的选择性无视;直言尽意者常常被民粹主义者污名化;底层“爱国贼”通过网络暴力宣泄对现状的不满;中港台三地的矛盾激化,认知鸿沟变宽;年轻人对身份认同的迷茫……
纽约时报采访了三位分别在台湾和美国受过教育的90后年轻人,“在华府”(周镭)、“刀哥”(余泽霖)与杨思羽。他们在微博或Facebook的简短文字中练成了对热点事件反应极快的健笔。他们曾在台湾与美国的课堂上介绍自己所认识的中国,也曾经在严肃媒体工作过或撰过稿,但他们常在无须庄重的场合,拿出手机打字,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发出或者嘲讽,或者搞笑,或者愤怒,或者认真的评论。
爱国主义,在这几个年轻人的眼中,是一个叠加了多重意义与情感的词组,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克制而适度,仿佛与小粉红或“谩骂中国者”的暴怒格格不入。他们对国家的关注与批判,有时因为小粉红们的体量庞大而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他们绝非“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与传统媒介叙事方式的差异,恰好是这一代人渐入主流的方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之外的生活学习经历,让他们在思考时,无须遵守一个官方给予的范式。多元的社会使他们的价值观重构,让他们难掩与国内读书的同龄人不同的想法。
留学青年谈爱国主义(一):留美“公知”

网名为“在华府”的周镭,成长于深圳,他是一位刚刚从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毕业的学生。在华盛顿就读大学期间他主攻国际关系,现在在华盛顿的一所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助理。周镭的网络角色是一名“公知”,他的微博账号“在华府”有近两万的粉丝。他比较关注中国的维权抗争及中国与世界的网络空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微博上,他常常发一些被墙的新闻、评论、学术文章等——他说,他希望尽量弥补双边因为信息不透明而造成的差距。
在前几个月“悉尼大学吴维辱华”事件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的华裔教员吴维,在取得澳大利亚国籍后,在微博上发布了焚烧自己中国护照过程的视频,由此引发了许多爱国青年对他的声讨——周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认为烧掉中国护照的吴维受到的爱国青年们的攻击与他本身的行为不成正比,于是在微博上,周镭和网络世界中的小粉红曾经有过一场正面的冲撞。他举报了其中一名小粉红的作弊行为,并且直播事情的后续,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事后他说,他会从道义的角度去做对的事情。
受访人在华盛顿通过电话与邮件接受了采访,内容经过了编辑和删节。
纽约时报中文网:作为海外留学生,请你谈谈对最近的热点事件,比方说对肯德基的抗议事件的看法。
周镭:首先肯德基的抗议事件,一线城市都是没有的。基本上都发生在三四线、四五线城市。那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平时对全球化与对西方的认知都非常局限。因为他们信息比较闭塞,所以相对激进一些,认知上也有很多断层。虽然现在可能已经不会有非常极端的事情出现了,比如说现在如果砸日本车,你更多招致的是批评。但是稍微小一点的城市里,可能这样的思想还是被周围的人认为是可取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海外上学的背景对塑造你的世界观与对中国的看法有多大的影响?
周镭:我对世界和中国的认知在国内就已经奠定了,但在国外社会生活的经历让我的认识日趋完整。小时候我一直关注时事和政治,但离狂热的政治仍然保持着距离。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崇高的国家话语不过是文艺汇演上强行背诵的红歌,和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国家”对于那个年龄的我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远在北京的一个符号。
转折点发生在初中时期,我偶然看到杂志上提及了“那场风波”。在父母没能给出完整答案后,我花了一整晚读完了维基百科上的相关词条(当时维基中文还能自由访问)。我当时恰好在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书里无所不在又让人毛骨悚然的“老大哥”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看到那场历时几个月的政治事件消失得无声无息,不少参与其中的普通人再也没走出那一夜,我发现奥威尔所描绘的那个可以随意篡改历史甚至让人凭空消失的世界,离我竟然如此之近。
而后我慢慢意识到,我所认识的中国,只是这个庞大国家和复杂社会的1%。第一次翻墙上推特,我发现推特上的中文圈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呼喊:维权人士光天化日下被套上塑料袋装进面包车,妻离子散的上访户被打断了腿……对于一个出生在沿海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来说,我生活的世界里从来不会出现这些事,但他们都是这个国家不会被关注的角落,黑暗但又那么真实。
如果在国内单单生活在大城市和消费主义围绕的泡泡里,的确很难建立起对中国庞大底层的感知,取而代之的是主流媒体上那个强大的世界第二经济体。并不是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高楼大厦,大家都吃得饱,可以上B站的。
家境优渥的留学生带着这样的认知出国,进入西方社会接受思想和生活上的不适与撞击,很容易建立起“出国更爱国”的民族自豪感,或者说自己思乡之情的政治投射。把国家表面上的繁华和国际上的“流氓”当做自己的底气。但我害怕的是,这样的爱国情绪会让一个人离现实中国和底层社会越来越远,作为中国的1%身处海外为全中国代言。因此身在国外思考中国的时候,比起那些一线城市的繁华泡泡,我更愿意提醒自己,这个国家还有不少看不到的角落和真实的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然后,进入了美国的课堂,你是如何适应的?
周镭:美国的课上课下经常会讨论到自己的国家。美国同学不用说了,美国仍然存在种族问题是广泛的共识,每次讨论社会正义也都能激起他们热烈的讨论。就连来自拉美的同学谈到自己的国家也不由自主地痛斥腐败。但不少中国同学在课上都不情愿回答这类问题,我曾经听到过不止一个教授私下抱怨,跟不少中国同学无法心平气和地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
美国的课堂是一个开放自由的言论空间,大家都是平等的,尤其来自非美国本土的声音更受教授欢迎。一个来自“弱国”的非主流观点可能在课堂上更有价值。课堂不是安理会,不用依靠祖国的地位争夺“话语权”。把课堂当做外交舞台,像外交部发言人一样“怒斥”听众与提问者,一味辩护而不交流,颠倒了课堂讨论的根本意义。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曾经被你的老师请入美国的课堂,分享你在“墙内的生活经验”,当时你美国同学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你是如何应对的?
周镭:我所在的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Judith Shapiro (夏竹丽),她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到中国生活的西方人之一。大四那年她新开了一门课,目的是让美国学生从中国人的角度了解中国。她想找到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跟她的学生分享中国网民的生活,便让我去讲了讲中国的互联网。
这是一个开给美国大一新生的课,那堂课的学生也全部出身成长于美国。这些大一的美国学生,很多人对中国互联网的认识就是:中国的网民被洗脑了。但是我试图让他们理解:第一,这是怎样一个过程;第二,那些“被洗脑”的中国网民具体在想什么。很多美国学生就觉得,中国人的网络世界被墙,(他们)是非常被动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主动的过程。国家控制了你的信息来源与四周网络,控制了这些过后,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网民,如果你没有翻墙习惯的话,那么你就会生出“我有自由意志”的幻想。好像你身边信息很丰富,好像微博、各种媒体、B站上的信息都很透明。但其实你还是在很小的一个圈子里面打转。
我试图让美国学生理解,如果一个人常年生活在信息控制之下,常年生活在与自由的网络世界相隔离的一个状态中,那么他/她会是怎样一个想法。我希望美国学生对“洗脑”这件事情思考地深入一些,把它当做一个动态的、相互的过程,所以他们以后遇到中国学生,就不会对他们的印象那么平面。(但)作为从小生活在信息自由世界的互联网一代,他们很难想像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近乎独立的网络世界里。美国学生们无法想像一日没有谷歌、Facebook等一线网站的生活。听到中国对境外网络的限制后,他们都表示如果自己是中国人,不可能过上不翻墙的生活。但我问道,当你的所有家人朋友都在微信、微博上,翻墙的技术门槛越来越高,而国内的替代品能满足网络生活的基本需求时,选择不翻墙的生活是不是也变得情有可原了?
讨论的结果让课堂十分悲观,大家都认为在墙内似乎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听到多元独立的声音。对消息本身和来源多思考,尽可能获取多方面的信息,是美国学生认为墙内的网民最该拥有的技能。
纽约时报中文网:很多人会在你的微博下指控你或者是抹黑你,你是如何处理这些一触即发的口水战呢?
周镭:小粉红们偶尔会给我发私信,但是他们发给我的内容我都不怎么看。因为我觉得他们说的东西都很同质化,所以你每个回复,是回复不完的。而且很多小粉红是不能被说服的,就像是士兵一样,他们过来就是要厮杀的。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要争得你死我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争论没有意义,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有时,你也不知道小粉红为什么愤怒。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的发言和行为,考虑的更多是从道义上来说,这件事不是应该做的,不一定会去考虑小粉红这个群体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如果你做什么都要思考那些极端爱国者的反应的话,这也是一种自我审查,是要避免的。
社交网络不是一个学习思考和获取新知识的地方,它是一个交流不同声音的平台,而建立自己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的过程最好在严肃阅读和个人经验中完成。但如今前后者的角色被颠倒,越来越多人选择在微博和知乎上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学到的更多是人云亦云和浑身戾气。这样的人在评论中自然留不下什么有意义的文字,只会用表情包、流行语和粗俗言论表达观点,或是跟着乌合之众洗版或“人肉”。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你的“不爱国”而和你的家人、朋友有过摩擦?
周镭:我基本上和家人朋友没有摩擦,但是我听说过有人在我背后说坏话。但是基本没有正面冲突。我觉得原因是因为如果你长期没有把你的政治立场表明清楚,但是偶然突然对一些热点事件表态,那么大家就容易和你有摩擦,大家会觉得,你怎么是个这样的人啊。但是如果你一直保持着一个立场,那么你对一件事情表态以后,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吃惊。
当有争议性的事件一发酵,在朋友圈中很容易就观察到多元对立的声音。我觉得本质上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大家对公共事务还抱有热情。
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一旦自己表达了和国内主流稍有偏差的异见后,便会换来朋友家人的许多失望甚至谩骂。现实中价值观撕裂所带来的打击是不可能没有的,我的做法是把它们当作鞭策自己思考的契机,从多角度想想自己表态的缘由,反对的声音来自于何处。当你对世界的认知、知识体系和个人经验在思考中都达成了逻辑自洽,做到了百分百的真诚,我觉得对那些声音就只剩下宽容了。因此我觉得在个人生活中,经常思考、怀疑、表达和交流,从长远来说都是有益的。
Afra Wang(王曌)家住北京,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电影传媒与历史专业,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世界历史。
留学青年谈爱国主义(二):夹缝中的陆生

余泽霖(Anderson Yu),江西九江人,是一位在国立台湾大学学习政治学的研究生。他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在网上他被人称作“刀哥”,在台湾的媒体上,时常以陆生身份发声。六年的经历模糊化了余泽霖的身份与认同感,在网络上,他说自己是一个“两岸认证边缘人”。


作为2010年“陆生三法”修法通过以后第一批赴台读书的大陆学生,赴台读书对他而言已经绝不仅仅是一个对教育的选择。他的学术研究可能也承载着对自己的经历与困惑的反省和审视。他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呼吁人们关注陆生无法享有的台湾全民健康保险(在健保中,陆生是被排除在全民健康保险外的学生群体,而侨生与外籍生都可享有健保)。陆生的健康与安全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忧虑的来源,同时,因健保开支巨大,陆生的健保也时常成为台湾两党争论的议题。面对台湾对陆生的种种误解、抗拒、不友好,余泽霖仍希望以陆生身份和台湾社会和解,他一直致力于陆生权利的维护与促进两岸的交流。
受访人在台湾通过电话接受了采访,内容经过了编辑和删节。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的Facebook主页的个人简介是“两岸认证边缘人”,你为什么这样评价自己?
余泽霖:其实我是随手打的。但是这个“边缘人”也的确折射出了我的身份危机,尤其是这几年来我越来越担心了。现在两岸关系问题很多,大不如以前那么友好。两边现在都在煽动民族主义。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学生就会有一些困惑:有人会因为我是大陆学生而条件反射认为我会选中国。但是,在台湾待久了,说对这片土地没有情感是假的。所以自己还是非常不希望看到两岸发生对抗。而且,在台六年,我觉得对台湾社会的观察还不够多,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毕后我还选择留在台湾,也希望以后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纽约时报中文网:先谈谈最近,民进党执政以后,你作为一个陆生感受到了怎样的政治氛围的变化?你有感到压力吗?
余泽霖:有,而且这个蛮明显。但也不敢说是民进党政府上台直接带来的。民进党的重新执政是几年来的社会演化的一个结果。整个社会的风气,从开始民众支持国民党到现在支持民进党,我是确实能感觉到的。这也是这个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民进党上台后,对抗是变得激烈了一些。
举个例子,去年大选年的选战期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国民党想要转移选战焦点,那个时候突然把陆生的健保问题引出来去审。在台湾的政治中,关于陆生的议题可以被拿来导风向,两党都会把这个拿出来炒作。这也是为什么陆生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群体的原因。陆生在这里相当于一个纸牌人,大家都来攻击。早期是民进党一直在攻击陆生,之后是国民党。你说国民党一直是在帮助陆生吗?其实也没有。两党为了争抢民意,都把陆生视为靶子。因为健保是台湾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因为它关系到钱,关系到社会福利。现在欧美国家也普遍面临这个情况: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给外国人提供健康保险?陆生在台湾的身份很奇怪。因为台湾的学生分四种:侨生、陆生、外籍生以及台湾本土学生。你就会发现,陆生既不能被归类为侨生,也不能被归类为外籍生。陆生只能被拎出来单独放在一个种类里面。而侨生是有健保的。
我想说一个关于去年十一月份,也就是选战时期的健保争议的例子。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陆生学长更新了一条状态,他说,我不需要台湾人的健保,也不需要台湾人来可怜我。然后他的脸书账号竟然就被检举和封号了。因为很多台湾人不喜欢他的说话方式。这非常夸张,也是消灭异见言论的一种方式——你们自诩的言论自由也不过就是这样。但是我的确理解这种社会氛围。台湾对中国大陆有着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恐惧的趋势。
也许一个陆生没有得罪任何台湾人,但是因为你带着这样一个标签进来,你就会变成那个“纸牌人”,被打、被攻击。他们打的并不是你,打得是你背后那个强权。于是有些台湾人会把这样的恐惧转移到你身上。
纽约时报中文网:当你回顾一下过去六年,在台湾做陆生对塑造你的政治观点与两岸的看法有多大的影响?
余泽霖:来了台湾之后,我发现台湾与我作为一个陆生的想像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来台第二年发生的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陆生,曾经在英国读过一个硕士,后来又来台湾师大准备再读一个硕士。但是他读了三个月之后就退学了。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为什么要退学。他坦言自己受不了在台湾人人都是“政治控”:在搭计程车的时候,司机听出来他的口音是大陆人,就开始和他战(辩论)统独问题;他去市场买菜,老板娘听出来他的口音是大陆人,就开始和他战统独问题;然后他去上课,老师听出来他的口音是大陆人,就开始和他战统独问题。他忍受了三个月终于受不了了,于是就退学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一个笑话,但是事实上在台湾,这是会经常发生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会让你对一个政治议题表态,无论你是支持统一还是独立。而且你表态后,后果也是不明确的。虽然并没有上升到“如果你不支持什么什么,我就会把你怎样”的程度,但是在日常交往中,这些问题别人都会问。而也不知道你的答案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几年前有一个陆生,蔡博艺同学,去竞选台湾淡江大学学生会会长。当时她就被人逼着去表态。更有意思的是,我遇到的大陆网民也常常逼着我去表态,甚至有时更加极端,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生活在夹缝中。国人长期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教育,“台独”并不是一个必须要被理解的事物。他们不需要知道台独的成因,也不需要知道台独到底有没有市场,他们只需要知道台独是一个必须要消灭的东西。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和台湾人有过一些正面冲突或者比较极端的对话吗?
余泽霖:其实有。像之前蔡博艺选举淡江大学学生会会长这件事的时候,我蛮支持她。我帮她说过很多话。我们在不同的大学,她在淡江大学,我当时在台湾文化大学。她的竞选对手甚至会到脸书主页上来攻击我,骂我是一个收了钱帮她说话的人。还有一个学长过来和我说,你现在终于知道台湾在国际上是怎样的地位了吧?我们说什么都被打压,所以你们陆生在台湾被打压也是活该。这位学长还是在台湾的一个研究大陆的研究所学习的学生,所以他相对了解大陆。在那个情境下看到这个学长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很震惊。后来我把这样的事情形容为“弱弱相残”,就好比今天狐狸被老虎抢了一只羊,但是狐狸又没有办法向老虎讨回这只羊,于是恼羞成怒又杀了一只羊。
这样的情况,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台湾学者的一些观点来看,这种“反中”的意识,其实是奠定了台湾的国族认同和国族想像。蔡英文上台的时间太短了,才两个多月。她的上台并不是从零变为一的过程。而这个从零变为一的过程其实是延续了很长时间的。并不是因为蔡英文上台事情才变糟的,而是两岸关系已经变糟很久了,蔡英文上台只是多补了一刀而已。
纽约时报中文网:蔡英文声明不认同“九二共识”后,你的身边有什么声音?
余泽霖:我身边很多人说,蔡英文不认同“九二共识”会很麻烦。有个台湾朋友和我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现在看看窗外,游客还不是照样来?该做的事情还不是照样要做?台湾不会因为这个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我觉得这个变化可能一时半会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这在台湾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事情,对一般的台湾人影响没有很大。台湾还有很多内部问题要处理。比如说最近在审核国民党的党产,刚刚通过“党产条例”。蔡英文刚刚上任,说不好听的,就是要去给很多事情擦屁股。而“九二共识”这样纠葛了多年都没有搞清楚的事情,她可能并没有放在首位。但是大陆又急着让她去表态。
我自己是积极的,我觉得两岸还是会找出一条路。民进党上台之前,有个朋友邀我写了一篇稿子,我当时就写了自己对民进党政府的期待。我说,我希望把陆生群体当做一个试验场,两岸是否能够继续去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试验场。因为两岸都是大体量的社会,如果正面交锋,那你也看到了,两岸的网民都会剑拔弩张吵个不停。但是难道我们要因为他们这样吵,就完全不交往了吗?也不会。
我认为陆生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平台,我之前和很多人说,作为一个陆生,希望和台湾社会和解,哪怕我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但是这个社会对你的看法还是很死板,两岸的问题解决起来还是很艰巨,比如说偶尔就会爆一下“D8网友来战,因为你的立场逼你道歉”这样的新闻。你生活在台湾这边,可能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就觉得你很力不从心,没办法改变一个群体。所以很多人很沮丧,读完书后会感觉很绝望。这种无力感和挫折感很明显,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既不想坐视这些事情继续变糟,也尝试过用一些方法去沟通改变,但是你做来做去还是这样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今天两岸对我来说最无解的情况,这个和是不是要坚持“九二共识”没有关系。
纽约时报中文网:既然这么看事情,你认为“九二共识”还有什么意义?
余泽霖:“九二共识”意味着“一中各表”。在很早之前,我们两岸的人都认为能够模糊掉两边的对抗,但是这个“九二共识”其实只是两边都看着爽而已。事实上“九二共识”在两岸最初的几年收获了巨大的效果,从前没有对话的两岸走到了一起,这是很了不起的历史成就。但是时过境迁,随着两岸之间的局势不断变化,“九二共识”原本让大家消磨对抗达成对话的目的遭到滥用。渐渐地大陆这边只看到“一个中国”,台湾只看到“各自表述”。当我们以为能够通过“九二共识”模糊掉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变成了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这件事情从来没被解决过,只是通过“九二共识”变成了一个搁置的争议。搁置了这么多年,这个争议也不会消失。当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两边又只会骂对方。作为一个游走在两岸的人,我没有看到两岸想要改变现状的决心,也看不到正确的努力方式。这也是我觉得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2011年,没去台湾上学的你对台湾的理解是什么呢?你后来发现大陆人对台湾有什么误解?
余泽霖:我当时是完全不了解台湾的,甚至都没去过。去台湾念书并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单纯就是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如果留在大陆的话可能只能去一个不三不四的学校。当时觉得去台湾是一个机会。
进入台湾的课堂以后,就会时常遭遇老师与学生的一些挑战。当时让我惊讶的是,台湾存在着几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教育脉络。就学期间我听过很多针锋相对的观点,是源于两方服务的政治立场不一样。来了台湾以后我看过很多台湾本地学者写的书,去了解更多台湾的背景。因为在大陆,没有人卖这种书,也没什么人去关心这些问题。中国总是对台湾的历史不理会,也不愿意去了解。比如说有部台湾电影叫做《KANO》,是魏德胜的”台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部电影讲日治时期的一个棒球队打入日本甲子园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在大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里面的台湾人要说日文?说日文我就看不起你!但是如果你了解当时的情况,1929年,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因为殖民教育的原因,当时的台湾人都用日文沟通。
往往很多时候,先天的一些偏见就会让你把真实的台湾拒于千里之外。台湾对于日本的情愫是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明白。她对日本不是单纯的喜欢,也不是单纯的讨厌。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纠缠着很多历史在里面。
很多人觉得台湾政治混乱的原因是两党内斗,老实说,我有个朋友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两岸之间的任何政治问题都是统独问题。你今天如果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那你还有什么可讨论的?无论是吵服贸,吵一些经济问题,还是吵对“九二共识”的态度,其实归根结底都在问:我到底是谁?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台湾塑造起来的政治观点对你回大陆之后,与家人朋友相处造成过摩擦吗?
余泽霖:也还好,因为我不是一个政治观点很鲜明的人,所以我没有因为我的想法和家人朋友有过摩擦。我并不是一个支持独立的人,但我对现在大陆主导的统战方式也有很多怀疑。我大学是读历史的,了解过两德走向统一的过程,但今日的两岸情况却截然不同,如果大陆还是想要透过经济达成统战目的,让我有点怀疑这样的方式是否真的有效。
然而台湾支持独立的一些人,很多时候并不是在真的追求独立,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中国人”或者“我没有中国也能活得很好”。比如说蔡英文的南进政策,起码是一个十年到二十年的规划,但很少看到台湾真的重视东南亚,从台湾社会对待外劳和外配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今天的台湾对东南亚还是有很重的歧视意味在里面。
纽约时报中文网:最后,请你谈谈最近的肯德基抗议事件。
余泽霖:我觉得肯德基这个事件很有趣,一开始我以为这是网上的一个笑话。后来没想到真的有很多人去抵制肯德基,还去游行。后来我甚至还听到一些阴谋论,说这其实是肯德基在背后主导的一场暗黑营销。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看似很普遍,但是我在怀疑这是不是这个社会的真实民意。很多人说这样的民族主义会影响到决策,但是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你看多了类似的事件,你就会找到很多相似点。这是一种全民的现象吗?我觉得也不是。可能只是网络上的一些辩论的热点被媒体捕捉到了,然后被放大。这并不是一个非常“中国”的事例。我觉得不能通过这件事去看中国。但是老实说,很多港台甚至国外的人,都会去通过这件事去定性中国。
我觉得这里有件事情需要探讨:网络民意是不是等同于真实的民意?网络民意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这个社会的声音?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不发声的。发声的总是少数人,而发声最激烈的,也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于是我还是宁愿相信这个是肯德基的一次暗黑营销,有点类似于“望梅止渴”的道理,让你看到肯德基的招牌,就想起来原味鸡的味道(笑)。
Afra Wang(王曌)家住北京,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电影传媒与历史专业,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世界历史。
留学青年谈爱国主义(三):常春藤的一只啄木鸟


杨思羽是山西太原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读应用数学与政治学。她曾经在财新传媒做过一年的实习记者,最近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实习,做数据分析新闻。在她一度非常活跃的问答社区知乎上,杨思羽积累了近5万的粉丝。她关注中国发展、伊斯兰教、性别平等以及美国大选等等社会议题,也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分析。比如,她反对人们将伊斯兰教的不同派系一概而论,也反对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在政论类播客《选·美》中,她曾经作为嘉宾与一个女权主义者,参与了关于单身女性政治力量的讨论。在知乎上,她曾经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啄木鸟,把国家比喻成一棵大树,因为“不想推倒这棵大树,却在树上啄啊啄。一次一个洞,一个洞一个虫”。杨思羽对这棵树,有无限耐心。
受访者在纽约通过电话接受了采访,内容经过了编辑和删节。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美国已待了五年了,期间发生的使你对中国的看法改变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
杨思羽:我在读大学时看了一本书,叫做《China's Second Continent》(《中国的第二块大陆》,Howard W. French/著)。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我在二线城市长大,太原。比起北京上海的孩子,我们感受过物质匮乏是什么,比如你买一辆自行车还会和爸妈想半天。这种匮乏,让我一直觉得中国更像非洲,而不是美国。但是,看完那本书以后,以及”一带一路“的规划和中国向外走的那一批政策后,我意识到,中国现在确实是一个大国。是一个问题非常非常多的大国,但是它是一个大国。大,是它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拿着一手好牌。中国有问题,不代表你看衰这个国家。在之前,我心里“中国”这个概念代表着弱国。我现在觉得中国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定义的国家。它一定要做很多大事的。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幸运就在于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生在一个正在上升的国家,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虽然你可以说它有股灾、资本不稳定,或者说这个社会的narrative(叙事)还非常混乱,但是它是一个大国,大国就是多元,难以被定义。体量摆在那里。因为它有足够多的财富,所以会有财富不均,因为它有足够多的人,所以有足够多的生命,因为它大,所以会产生比较健康的多样性,而这个多样性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焦虑的来源。
你有很多担忧这个国家的理由。担忧是因为中国大,而且中国不像美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narrative。中国政府在尝试建立一个对这个国家体系的共识,但是共识的构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什么不容易?比方说?
杨思羽:中国之前善用一个“us vs. them"(非此即彼)的体系,但是这次南海的事情,让大家意识到大家已经不买“us vs. them"的账了。为什么纯粹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一件让大家不快的事情?因为大家意识到“us vs. them”所号召的彻底对国家的牺牲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这也不代表很多人不爱国。
我觉得中国人的爱国,就是看好这个国家。很多人看好这个国家的表现是无意识的,无论从消费也好,还是在投资上也好。比如上一代有钱的人会想把资本放在美国,但是他们人还是在中国,还是会在中国投资。他们带着焦虑,带着矛盾,甚至带着不信任,在建设着这个国家。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觉得你是一个爱国者吗?
杨思羽:爱国者这个词被污名化了。很多人觉得,爱国就等于小粉红。我没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因为毕竟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但是我觉得,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投胎投得很好。我可以说我自己是理智爱国。对我来说,将来我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会在我以后有一天能够回国后体现。但是现在有种种条件的局限。比如现在很多搞金融的人不回国,是因为国内的金融业的市场变革非常得快。我认识的在纽约的一批中国年轻人,采取了一个蛰伏的态度——伺机而动。他们会挑选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回国。在回国之前,可能还会积累:知识和经历的积累。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认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更强烈,还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更强烈一些?
杨思羽:不分伯仲。我刚刚来到康奈尔的时候,我就被套入了常青藤的liberal bubble(自由派小圈子)中,因为康奈尔是非常liberal的。我当时有一个错误的感觉,那就是美国人更加国际主义一些。他们会更加开放。但是随着自己出来工作,以及关注大选一系列事情,把很多其他层次的美国人,通过社交媒体也好,通过对川普的争论也好,把他们的不满摆到了社会的讨论中心。我作为一个学习政府研究的学生,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美国人的民族主义还是非常强的。原来总觉得美国因为多元,又因为长期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能随时接纳外来人口的状态中,所以不会有很封闭的民族主义。但是后来发现我错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网络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中国对于性别平等努力的程度,是不是让你觉得自己对“中国人”这个概念疏离?
杨思羽:没有,我反而对中国的女权这个事情抱有希望。女权、LGBT,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年轻一代的接受速度非常快。举个例子,两三年前的“女生节”,你会看到清华北大都有很多“我要当你的小公主”这样的横幅,但是今年你会看到,比如汕头大学、中山大学,打出来的标语都很女权。而且包括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female empowerment(女性赋权)的沙龙也好,文章也好,一个“强壮的、独立的女性个体”这个概念在男生和女生中,慢慢地被接受。
我觉得大家,尤其是这个世代的人都非常思想开放。也有一些非常直男癌的人,但是“直男癌”这个词语流行开来,就是恰恰因为这段时间这个问题被提到了讨论的中心。虽然有一批人很保守,很固执,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占主流。整体的趋势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它。
虽然这个事情没有一个indicator(指标),如果你去社交网络上扒“女权”这个词,很多人不会愿意很犬儒,不会愿意把自己和“女权“绑在一起。但是她们在生活中的表现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自己不是中国传统女性,并且以此为傲。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康奈尔的美国与中国精英同学中,对美国大选有怎样的态度?
杨思羽: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康奈尔的中国学生,本科生里面,很大一部分人对政治非常冷感。大部分都是“哦,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或者是“这个我不是很懂”。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每次和我们学校学金融的同学吃饭时,就会有一个人和我说,“杨思羽,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美国大选”,或者是“最近新闻里都有什么呀,能分析一下吗”。然而,我讲两分钟,就会所有人都开始玩手机。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人对种种政治议题不了解。还有一大部分人非常liberal,他接入了康奈尔的社交网络,接入了这个社区,他会消极地接受女权,接受种族平等,接受法制(rule of law),接受宪法,接受equal protection(平等保护)等等概念。但他也没有很刻意地去关注一些事情。他可能上过一两节课,质疑过它们。所以川普上来以后,很多人不理解。没有想到美国还有这样的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么,在你康奈尔的同学里,对国内各种热点议题也很冷感吗?
杨思羽:他们之中,黑小粉红的人居多。但是这是一件非常“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因为留学生本身是跑到国外的一批人,都是“反贼”。所以他们有意或者无意,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narrative。但是动不动因为这个国家就生气动怒,在他们看来,会太cynical(愤世嫉俗)。
我举个例子,因为我在我的朋友圈和Facebook里会经常发一些和美国大选以及中国一些时事相关的内容,我发的都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东西,是一种分享的态度。但是,昨晚,我收到一条微信,上面说,“杨思羽,你最近的政治X装到飞起啊。”他其实只是在开一个玩笑。但是他觉得,我关注政治,特别是在社交网络上关注政治,是在make a statement about myself(自我声明)。那么他对于别人关注政治事件的想法是,“that's not cool”(那是不酷的做法)。
大部分人,特别是更优秀的一批人,大部分心里都是很关注的,只不过,有些东西让他们过于失望。所以他们选择不去趟这个浑水,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没办法去表明立场。比如说,你如果公开表示拥护女权,那就意味着你认可女权的各种东西。你在南海事件上表明了立场,那么你可能就把你和小粉红们放在了一起。所以,因为有猪队友,所以很多人选择冷嘲的态度。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喜欢用知乎分享你的政治立场和对女权主义的支持,很多人说你在网络上宣扬美国左派的价值观,你怎么应对网络上的质疑?
杨思羽:我在康奈尔也会遇到类似的不快。即使我是一个希拉里的支持者,我在康奈尔的政治光谱中,尤其是与最根深蒂固的左派对话时,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偏保守的。包括一开始,我对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是美国的一个维权运动,旨在反对针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与暴力行为——编注)也好,对于川普现象也好,我在康奈尔的同学圈子里,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resident xx(骂人话)。因为虽然我支持Black Lives Matter,但是我也认为这个抗议运动内部也有很多问题。当有人说,支持川普的人脑子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也会站出来说,美国估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产业转型的时候,把转型被迭代下来的一群人叫做xx的国家。我觉得左派媒体确实应该反省了。他们是一个经济现象的产物,他们无论多傻,无论受教育程度多低,你也不能管他们叫做xx。我觉得川普的支持者是一种现象,而且他们需要被尊重。他们因为现在没有representation(代表),所以他们才焦虑。所以你不能继续剥夺他们的representation。我觉得批评美国的自由派和希拉里的支持者表现出的自私,让别人认为我不那么liberal。
我当时无论在财新工作也好,还是学习也好,都很关注中东问题。我不急于把伊斯兰教徒分门别类,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我是“圣母”,我被左派洗了脑,我拿了左派的钱。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有时在知乎上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人总是在阅读他想看到的东西。我把这个归咎于我写的不够明白。网友对我的不理解,给我的负面影响很大。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何评价这次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霍顿(Mack Horton)说孙杨是”药物骗子”后,网民攻击霍顿、支持孙杨的事情?奥运会激发了全民爱国主义,你又怎么看?
杨思羽:我觉得不是网民集体攻击霍顿或是集体支持孙杨。只要这个事情不仅有一种声音,我就放心。对峙,会让两方分别更加极端。这不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网民的关注点和道德以及三观的切分,好像每两个月就要换一次。我的态度是,只要这个东西还在动,这颗心还在跳,这个话语体系还包括着各种嘈杂的对话,甚至有好多正面和负面的情绪,它就是好的,说明这个国家是活的。什么样是死的?你现在看看土耳其的社交网络。
中国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开幕式是一个声明: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了。它希望展示的历史也好,科技也好,人也好,回过头看,是告诉世界,要该认真对待中国了,我们要开始进入你的地缘政治版图了,我们要变成世界小棋盘的主要玩家了,我们要升级了。巴西也要说类似的东西。他们要透过这场奥运会,改变世界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因为我们对于巴西的看法都是:美酒、美女。但是巴西的开幕式是在说,我们是一个有科技、有时尚、有知识、有历史、有文化的一个大国。开幕式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这个不能和中国的举国体制比。尤其是中国排练节目的形式,我不觉得任何一个国家能驱动这么大量的人来集体表演。
Afra Wang(王曌)家住北京,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电影传媒与历史专业,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世界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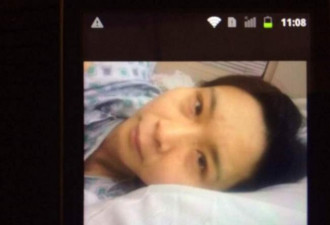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