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计划:花8万美金冻脑袋 真能获不死之身?

在一个盛满液氮的容器里漂浮,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把控力,听上去有点儿没劲,但这总比被虫子和细菌啃个精光好吧?
美国最大的人体冷冻中心的办公室,从外面看起来更适合美剧《办公室》里的Michael Scott(Steve Carell扮演),而不是美国科幻小说家菲利普迪克(PhilipK.Dick)。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位于亚利桑那州斯克茨代尔市(Scottsdale,Arizona)的一处宁静的蓝灰色产业园区里,背后紧邻一条商业街,有农庄和射击俱乐部。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如同落日美景般宽阔而绵延不尽,仙人掌点缀其间。但事实证明,如果我要找人聊聊冷冻人体和宠物的话,还是得去人迹罕至处一探究竟。
人体冷冻是一种用低于冰点的温度来保存人体的科学技术,寄望于可以在未来复活——尽管无神论者认为这完全就是骗人的勾当。一进入阿尔科的办公室,我也变得对他们将信将疑起来。这个非营利机构的九名工作人员一边对我致以微笑,一边忙碌地穿梭于银光闪闪的幕墙之间,墙上挂着已经冷冻于此的人们的照片。那种感觉,怎么讲,有点像是在《星际迷航》中的深空九号宇宙飞船上开了一家诊所。总计有149具躯体和脑袋以零下三百度的低温存储在阿尔科。
其中包括一名中国科幻作家(重庆女作家杜虹)、一名泰国小女孩、还有棒球名宿泰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但有悖于流行观点的是,工作人员说华特?迪士尼并没有长眠(冷冻)于此。基金会正准备扩大规模 ——已经有超过1100人表示愿意进行同样的深度冷冻。阿尔科说,这些人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从事于科技行业,大多愿意在自己40多岁的时候就进行冷冻,而不是等到花甲之年。他们将自己的身体看作是可二次开发的机器,只需要在未来重启一下就好了。
但是除了光鲜亮丽的高科技太平间外,人体冷冻的前景究竟怎样呢?

1972年与妻子琳达共同创建阿尔科的弗雷德张伯伦(Fred Chamberlain)被冷冻在冰库里。团队成员相信这张大脑扫描影像表明,他的记忆很有可能还保持完好。本文所有照片均由马克彼德曼(Mark Peterman)提供。
对人体冷冻持反对意见的人形形色色,并且善于制造舆论。人体冷冻目前在某些地方是非法的,包括法国全境以及加拿大的部分地区。许多人认为阿尔科这样的机构为那些无力抵抗悲伤痛苦的人提供了虚假希望,并且是一个庞氏骗局——通过从新成员手中敛财来维持老成员的冷冻状态。最近在英国,一名14岁就离世的孩子的母亲打了(并且打赢了)一场官司,支持她女儿要求在死后被冷冻起来的遗愿。为《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撰稿的神经科学家迈克尔?亨德里克斯(Michael Hendricks)称人体冷冻是一种“伪科学”,还说“那些凭此获利的人理应被我们斥责和蔑视。”2006年,人体冷冻遭受了挫折:两名冷冻人的儿子发现有一个冷冻舱存在故障,他的双亲解冻了。并且同样可怕的“悬架故障”使得人体冷冻至少退回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但是,对于在1972年联合创办了阿尔科的琳达张伯伦(Linda Chamberlain)来说,人体冷冻的观念是“解脱”。张伯伦告诉我,她自己愿意在死后被冷冻,而且她的丈夫弗雷德自2012年死于癌症后,已经被冷冻进了阿尔科的冰库里。“因为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便你遭遇到了什么不幸,”她说,“你还能有一次机会重新来过。”
张伯伦和她的丈夫相遇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加州举办的某次早期的人体冷冻大会。在他们46年婚姻生活中的许多年,他们都服务于接纳遗体并进行冷冻处理的阿尔科救疗团队。她现在是阿尔科的兼职特别项目经理。“我能够离他更近些,照看着他。”她对我说。
张伯伦身型矫健如飞鸟,国际化谈吐溢于言表。她坐在阿尔科办公室里悬挂的那幅长长的《人体冷冻史编年表》前,补充说:“弗雷德和我一直想要互相厮守,我无意再嫁或有其它任何打算,我就是想把他弄回我身边。”
墙上的编年表始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773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这样的话他们还有可能复活。”之后是学者罗伯特艾丁格(Robert Ettinger)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不朽的展望》,然后时间线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人体冷冻受到了艾丁格那本著作的不少启发。红头发的马克思摩尔(Max More)是这一机构的英国籍首席执行官,他告诉我说,除了基金会名字中包含的略有煽动性的字眼外,阿尔科并没有承诺参与者会长生不老。
大体的概念是这样的,现在活着的这些人都对我们未来的后辈一无所知(如果人类到时候还存在的话),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未来的朋友’”(艾丁格这么称呼他们)比我们更好、更聪明、更灵巧。他们会对我们现在的世界充满好奇,并想要让我们复活,就好像是一部更有人情味的《沉睡的野人》(Encino Man),或是现实版的《飞出个未来》(Futurama)。对摩尔来说,冷冻人既不是什么邪教成员,也不是奸商或怪咖,他们只是被误会了并被人类的潜能所迷惑。“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摩尔说,“拥有二次生命的机会。”
“我们谁都不想这样,”摩尔指的是死亡这件事。“漂浮在一个盛满液氮的容器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听上去太没劲了,但这总比被虫子和细菌啃噬,或者在一个大烤炉里被火化强得多。”但他告诉我,人体冷冻是“一次机会,并且伴有不确定性。我们无法保证这项技术将会一直得到发展和进步,但这似乎是有可能的。它没有违反物理法则,只是技术进步的问题。”
根据你所需的不同服务内容,阿尔科的收费标准会有很大变动。全身保存的基础价格是20万美金,如果只保存头部(“脑神经系统”)要花费8万美金,同时还提供宠物冷冻服务。阿科尔公司收取的费用中大约一半会被分配给一个病人护理信托基金,这一基金的存续时间要比阿尔科现任管理团队更长久,并能为被冷冻人抵御未来金融的不确定性(即便没办法知道复苏需要花费多少钱)。“有误解认为人体冷冻是有钱人的游戏,但并非如此,”摩尔说,“如果你用人寿保险的形式来付费,就跟每天喝一杯星巴克花的钱差不多。”

马克思摩尔(Max More)是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他说人体冷冻复苏在50到150年内“就应该可行了”,“冷冻人”不是怪咖,他们只是被误解了。
在我参观期间,摩尔把我带到一间类似手术室的房间里。在类似便利店里那种明亮的灯光下,他给我演示了阿尔科的工作人员在病人被宣布死亡之后是怎样处理尸体的。他说阿科尔有一份列有绝症患者的“关注清单”,会尽量缩短死亡与冷冻之间的时间,以减少任何潜在伤害。签约的外科医生,工作人员,和其他志愿者构成救疗团队,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住在斯克茨代尔,但他们也能被派往别的地方。摩尔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像电影里那样处理不省人事的病人,”我们站在一张轮床边,床上那个橡胶制的真人大小的假人身边摆满了塑料冰块,“现在还不行。”
一旦被抬上轮床,尸体就会被注射大约16到17种不同的物质——包括抗凝血药和制酸剂,第一种物质被用作强效麻醉剂。Go Pro摄像机会把全程都记录下来,寄给家庭成员和其他研究人员。在某些情况下,病例研究会被公开。
尽管看上去和普通医院差别不大,但感觉上仍然非常奇特。我问摩尔是否认为人们对人体冷冻的态度会逐渐正常起来。他说,主流社会正开始逐步接纳体外受精和器官捐献这类曾经无法企及的革新,这也有助于医生和病人接受人体冷冻的概念。
“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跟李奥纳多达芬奇设计直升机翼和其它飞行器的时候差不多。当时的人们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异想天开,但他是对的。他没有造出那些飞行器只是因为缺乏工具和技术,但大方向是对的,”摩尔说,“又或者,比如1960年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把人类送上月球。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没有足够强劲的火箭,也没有生命保障系统,没人知道该怎么办。但最终不到十年就实现了。”
我好奇的是冷冻人复苏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而且假如他们活过来,还能保有多少自己原来的个性?如果我被冷冻后复苏,我的记忆——银行ATM机的取款密码或者与我挚爱的人共同度过的珍贵时光,是不是还会停留在脑中?
摩尔抽出一张弗雷德?张伯伦的大脑扫描成像图,放在平板显示器上,指着一堆不同区域里的亮粉,亮紫和亮蓝色的杏仁状部位说,“很容易判断出他的全部记忆都保存完好,什么都没丢。”
在摩尔看来,低温冷冻和解冻“应当是可行的,”尽管很难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他说或许要50到150年。然后他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在那里透过防弹玻璃我看到很多大型的落地金属贮存罐。在放置冷冻舱的房间里,有十几个这样的金属罐。它们全都亮得能倒映出人影,摸上去冰凉光滑。目前条件下,阿尔科可以容纳接近1000名冷冻人。
每具冷冻的躯体都用一种类似睡袋的东西包裹住,放置在一个铝制的冷冻舱里,然后跟不锈钢储藏罐里的其他三具躯体和中心罐里存放的五颗大脑放在一起。这些不锈钢储藏罐都可以被看成是“巨型的,异常昂贵的保温隔热瓶,”摩尔边解释边把灯打开。可以看到墙体经过多层电镀处理,而且尽管这个房间配有备用发电机,但摩尔向我保证冷冻的人体在停电的情况下也不会解冻,至少几个礼拜没问题。
当我继续漫步在阿尔科的大堂里时,无论我感受到多少太空时代的元素,还是很难不被更加不同寻常的事物所触动,那就是乐观主义。不管从科学上讲是不是有点疯狂,人体冷冻事实上是寄望于一个比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更好的世界。在一个犬儒主义和不确定性盛行的时代,这是一种假设的描述。无论从逻辑,科学还是叙事方面给自己讲过多少有关死亡的事,我还是毫无缘由地迷上了这种想法。

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的会员,也就是所谓的“冷冻人”都存放在照片中的这些闪闪发亮的金属圆筒里零下300度的液氮中。
站在这些冷冻舱中间,想到所有那些冷冻起来的脑袋和躯体就安放在金属的另一边,我问摩尔要想成为一个冷冻人是不是必须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我不认为我们的全部会员都是乐观的,”摩尔说,“我知道有些非常可悲的人总是觉得事情会变糟。你必须至少要对科技保持乐观,并相信它会进步。否则的话,你就会钻到牛角尖里去。我觉得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比大多数文化要乐观,因为大多数文化只会片面地看待长期展望。”
“人们总是抱怨现在的一切有多糟糕。‘是史上最糟糕的年代。’胡扯。只要把这帮人扔回往100年,或200年,或500年,或1000年,或10000年前,让他们看看那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想回到自己不能拥有任何财产的年代,还是你属于你丈夫的时代?奴隶时代?没有止疼药或者防腐剂的时代?还是四分之三的孩子死于分娩的时代?不了,多谢。”
在送给我几本阿尔科的人体冷冻期刊和一套申请表后,他与我握手告别。回程路上翻阅着那些资料时我想,未来可能并不完美,但在一个疾病肆虐的时代,以一种超越生死界限的长远眼光来看待问题,总是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心态——无论你是否选择冷冻自己的身体。
作者:玛丽皮隆(MARY PILON)
译者:威廉老杨




![[集市好物]仓库处理](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487e4dbd-998d-4bd9-8d31-a8f90a7c37a4.900x195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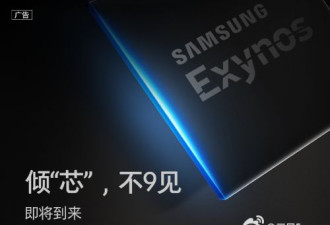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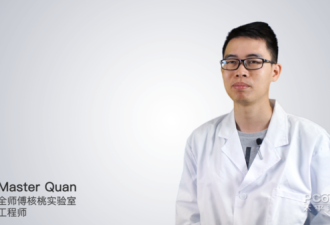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