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触目惊心!离不开的“雾霾源头”

河北省唐山市木厂口镇松汀村,钢铁企业巨大的烟囱不停喷吐着灰色的浓烟,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将污染的爪牙伸向空气、土地与河流。村民们深狠企业带来的环境恶化,也担心“工厂黄了没饭吃”。抗争与妥协、冲突与困顿交替出现,这里成了他们离不开的“雾霾源头”。 郝文辉 冯中豪/摄

迁安市(县)是唐山市的“钢铁一隅”。位于唐山市迁安市(县)木厂口镇的松汀村,最鼎盛时期周边有十四五家钢铁厂,空气中常年弥漫着类似臭鸡蛋的味道,被大量的报道称之为“雾霾的源头”。图为2016年12月30日,迁安市松汀村,林立的烟囱包围着旧村居民低矮的平房。

污染已经深入到村庄的骨髓里。松汀村村民杨和元的家,一年四季是不开窗的。家中的墙面上总有一层厚厚的粉尘,用手一抹,全是黑色油状物。这一天,他和儿子杨非文坐在床边,电脑桌面的蓝天草地,和居住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五年前的脑梗塞给杨和元留下了后遗症,双手偶尔不听使唤,腿脚不太利索。坐在床边剪指甲的时候,杨和元小心翼翼。63岁的杨和元在妻子去世后跟儿子杨非文相依为命了十二年。目前松汀村剩下的一百多户村民,大部分都是留守的孤寡老人。

杨和元晒在屋外窗台上的红薯干早就不能吃了,厚厚的脏污层上,还散落着许多反光的金属物质,“根本洗不干净”。

松汀村和周边工厂交叉路口,一家旅馆养的白鹅基本看不出本来的毛色。

村里的水也出了问题。村民打上来的井水,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油花,烧干后锅底全是白色的残留物

目前,迁安中化焦化厂开始委派松汀村村委会从新区锅炉房运水供给旧村的留守家庭,每天送一次,并承认地下水“污染超标”,不能再喝了。图为杨和元将接来的水倒入容积四十斤的塑料桶中,桶上附着浓重的黑尘。”他说:“光是吃水,不洗衣服,两口人一天至少也要一桶水。”

疾病在松汀村蔓延。吴济住在松汀村西头,是离村西几家厂区最近的住户之一。心肺不适、头痛、鼻炎常年困扰着他。他的脸上总有洗不干净的黑色灰土,时间久了,他的眼睛干涩难忍,眼角也开出了一条红色的口子。

69岁的张翠兰因为脑梗已经有五年没有下床。丈夫赵鑫全每天在家中照顾她。“翻身都费劲,没他照顾我一天都活不了。” 在松汀村,心脑血管疾病很常见。一份广为人知的松汀村村民死亡登记报告中,25个死去的村民,除2人因乳腺癌和输尿管肿瘤死亡,其他全部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与肺癌。

村民们困顿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放大了疾病的威力。65岁的徐卫国7年前得了脑梗塞,留下的后遗症让他腿脚不便,行动迟缓,捋不顺舌头。每天,徐卫国都会在附近两家钢铁企业门口守候,等待着每一辆满载或者卸完焦炭的卡车经过。他期盼着在他早已熟悉的道路坑洼处,卡车会因颠簸掉下来几块焦炭,捡来卖点钱或者自己烧。

在钢铁产业繁盛时,村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捡50斤焦炭,卖25块钱。限产令颁布后,掉落的可捡的物件越来越少,已经没有多少人指着“捡破烂儿”过活了,曾经热闹的铁轨沿线也日渐凋敝。

王有财所在的津安钢铁厂就倒闭在限产的大潮里。发了四万多块钱后,王有财开始串庄(在几个村子间奔走)卖辣椒酱。小罐的五块钱,大罐的十块钱。去除成本,每天平均挣不到六十块钱。

王有财当年在厂里工作时的安全培训合格证。2011年的他并不胖,但自五年前的得了脑梗之后,王有财开始不间断服药,副作用让他胖了一圈。“吃药给人吃胖了,但药没法停。”

限产大潮影响到的,不仅是在厂子里工作的职工。2017年2月25日,松汀村西口马路一侧的饭馆大都停业。村民称,“老东北菜馆效益太差经营不下去了,老板走的时候还欠着房东的债,旁边的台球厅店面已经换了好几家铺子,都开倒了。”

松汀村口为数不多的餐馆里,70岁的陈海富和老伴还经营着自家的生意。如今工厂职工少了,往来的客源大多成了大车司机。“生意好的时候每个月能过万,现在能挣个6000块就不错了。”

自2003年厂区搬迁占地以来,松汀村的村民们就没有地可种了。2017年2月17日,西沙河畔,72岁的刘军在烧荒。他自2014年来开荒三年,慢慢地在污染的西沙河边的荒地上开出了几分地种植玉米,赖以为生

更多的失地村民,选择了打零工和拾荒,聊以为生。图为2017年2月17日,村民吴济正在做一份帮人照看老家的临时工作:看家、喂狗,每个月能多拿几百块钱维持生计。

对于留守在村里的年轻人来说,谋生和娶妻皆是难事。杨和元的儿子杨非文今年26岁,初二辍学后曾去矿场学过开挖掘机,又去钢厂打短工,不停地在工厂之间寻一些杂活。年迈的父亲没有任何积蓄供他娶亲,在当地,娶媳妇需要的花费至少在八万元左右。

2017年2月18日,杨非文在已被荒废七八年之久的松汀小学旧址拍摄录制短视频。和老一辈不同,杨非文关心社会民生、娱乐八卦,他尤其关注雾霾的新闻,认为“到2050年,这个雾霾才能治理好”。

杨非文的邻居——今年30岁的徐建成刚刚和比自己小6岁的女友分手。“有代沟,感觉谈不到一起。”作为松汀老庄几十位单身男青年之一,父母也曾多次给他说过亲,但找不到对象似乎是整个村都有的问题。

现在,徐建成给朋友打工开大车运送货料,每天往返在料场和厂区之间,凌晨3点从家里出发,两个来回后,已是第二天凌晨。他每周开车近80个小时,“以前在厂里干活,挣不到两千,现在开车能挣五千多。但你要天天开,时间久了真的很枯燥。” 他和哥哥徐建才的收入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 图为跑了一夜车后,徐建成在京唐港外的小吃摊买了一份煎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环境变迁让老村人困苦不堪,饭菜剩下后放到橱柜里,热了再吃的时候就已经沾上了一层灰。2014年,信访无门的几户老人采用了极端的抗争方式:截车。最终在最后一次截车时,吴济在撕扯中断了三根肋骨,被派出所关押9天后,才得以赔付治疗,而杨和元在里面度过了61岁生日。此后,松汀村再无“有声”的抗争。图为2016年12月30日,杨和元与吴济站在两家屋子中间的空地上。

杨和元说:“不是希望钢厂黄,钢厂黄了大家都别活了。只是家里太穷了,买不起新区的房子,希望政府能给搬到那边,离厂子远点。” 图为2016年12月31日,杨和元外出办事,路过一座新坟。远处,是雾霾中隐约可见的工厂散热塔和烟囱。松汀村的大多数坟地在厂区建设的时候被占了,如今只有村子南边留了些田间坟头。

“杨和元们”向往的“淞护新区”距老村约3公里,距焦化厂直线距离2公里左右,这里的部分楼房是以前九江线材的宿舍楼,房价每平米1500元左右。自新村小区2008年建成后,松汀村大部分村民或买或租涌入,8年间,原有1300多户家庭、3500多人口的松汀村只剩下了100多户。

姚占友一家是松汀第一批搬至新区的家庭。如今,姚占友每个月能拿到180元低保,一个月偶尔能去帮人装一两次除尘袋,一天赚100元;老伴今年60岁,在社区打扫卫生,一个月工资900元。姚占友27岁的儿子今年刚去松钢当临时工,工资一个月2000多元。姚占友说虽然家中有房,但没收入,“儿子现在也说不上媳妇儿”。

姚占友和不少新村居民一样在小区门口一块空地里种了点大豆、麦子和红薯。“村民以前有口粮地能解决吃饭问题,现在没地也没工作”。“这地都不是我们的,今天种了,说不定明天就给扒了”。

姚占红2009年时从老村搬迁到新区。19年前,姚占红开小拖车时不慎翻车,脊椎骨受伤落下残疾。他在新区的房子是4楼,因为腿脚不利索,上下楼麻烦,现在以400元每月短租给别人。

45岁的姚占红至今未婚。2010年,村大队安排姚占红在新区看守北门,工资一个月450元,每个月还有300元左右低保。“最害怕有病,身体不允许其他的什么也干不了,一生病就完。”

多数时间,姚占红都独自一人待在门卫室里熬日子。“2009年到2011年,新区楼层好的120平米大户型以前能卖到二十五、六万。因为空气污染、水质太差现在连20万都卖不到,条件好点的都去市区里买房子。家奉献了、土地奉献了,健康风险了,到头来我们有啥回报?”姚占红说。

傍晚时分,坐落于新区西侧的工厂烟囱不断往外排放气体,从新区居民楼底下望过去显得“触目惊心”。

2017年2月24日,木厂口镇中心完全小学学生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玩耍,孩子们身后不远处就是林立的烟囱。孩子们称平时并没有佩戴口罩的习惯,但“空气实在太糟时学校会放假”。

2017年2月24日,松汀迎来难得一见的好天气,杨非文坐在新区旁边的空地上忍不住打起了盹。不少亲朋好友被占地后搬到新区,但他如今很少来这,因为他家“地没被占,想搬也搬不来”。

有时候兴致来了,杨非文会到村旁的西沙河里钓鱼。

钓上来的鱼,杨非文喂了鸭子,他说村里人都不敢吃。村民刘文贵说“外来的人吃不了我们这儿的饭,觉得灰太大水没法儿喝。其实没事儿,吃习惯就好了。人最能活了,你看,我们屋外河都是什么色儿了?里面还有鱼呢。鱼身上都发臭了,还在里面游,鱼都能活,人还活不过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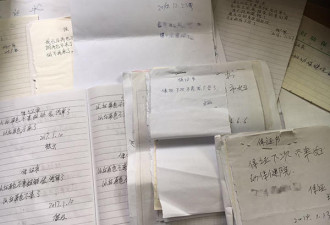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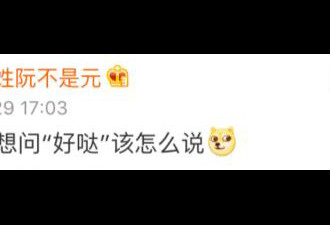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