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者:儒家眼中的“刘晓波困境”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正经历着痛苦的精神选择,这种痛苦是自我困境与“家国困境”的嵌套,也掺杂着模棱两可又看似明晰的“普世”认知。这种痛苦与困境究竟来自何处,是一个亟待澄明的问题。
就此,多维新闻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朝晖,在他看来,西方的自由、平等在中国缺少现实土壤。
多维: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那套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意义,以前温家宝会强调与西方普世价值靠拢,习近平上台后强调中国理论,所谓“四个自信”,你认为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念是不是普世价值,那些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有没有道理?
方朝辉: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比如自由、人权、民主、法制,这些东西作为普世价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够成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没有普世性吗,没有普世价值吗,关键在于这些东西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比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否定真善美是普世价值,但是有几个民族把真善美当做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来对待,恐怕很少。西方人当然也崇拜真善美,但是他们在社会生活当中,社会制度方面,他们认为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更有实际可操作的价值。
所以承认某种东西具有普世意义,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一个民族的社会制度与建设,民族的社会生活层面,什么样的东西是有力量的。
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不等于印度人会放弃印度教。说一个东西具有普世的意义,但是在一个民族的实际生活、人的精神价值信仰、社会制度建构、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如果只有边缘的作用,没有根本作用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普遍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他们想象当中认为有一种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普遍原理理解的基础之上,基于这种理解推出普世性,这是他们犯的一个基本错误。

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的大师,包括哈耶克、托克维尔在内的一些人都强调法制和民主必须要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之前有段时间我也注意西方的日本研究,因为日本是二战后全世界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所以西方很多学者研究日本的现代性问题。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战以后的日本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完全是照抄美国,但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专家将日本现代化的成就归功于民主、法制和自由。
他们认为日本所取得的成就,是日本这个民族自身的文化所决定的,比如有些西方学者深入地发现“礼”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方面发挥多么强大的作用。
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似的,中国如果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的进步,靠学习民主、自由、民权是很可笑的。但也不是说要反对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作为普世价值没有问题,但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它身上。
多维:既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解决方式不对,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方朝辉:我是讲西方这套自由主义的理论不是根本性的力量,当然它有它的价值。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一种好的法制、宪政如何才能建立起来,这是比喊几个口号困难多的事情。
就中国实际而言,党员的信仰世界要不要重建,还有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国家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没有把社会的争议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在出现很多坑蒙拐骗的时候没有及时地加以制止,引导整个社会的潮流就是向经济利益发展,经济利益成为衡量一个人成败的最重要的标准。
当社会的标准一旦形成,它就会直接影响千千万万官员的思维模式。90年代我家乡有很多中小学老师都选择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按理说老师这个职业在公务员体制里是比较好的职业,为什么大家都放弃了呢,因为都禁不住金钱的诱惑。
在这个逻辑下,当官的自然也要搞钱,是因为社会巨大的温床才培育了大批的贪官,再好的社会制度,也抵挡不了社会的风气,不解决这些问题,只讲民主法治,能解决贪腐吗。我承认中国新闻信息的不够透明,包括政治制度的不够民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多维:刚才你提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困境、迷思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对此能否展开说明?
经过我的研究,发现有一个东西是被忽略的,就是过去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三个预设的基础之上。
第一个预设就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世界,也只相信这一个世界,不以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为虚幻,天地六合不是假的,有了这个寄托,中国人的希望和生死都在其中。
第二个预设是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中国人既然不相信死后的世界,就不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看得最为重要,所有最重要的关系都来自这个世界当中的关系。
人们会很自然地倾向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来源于关系世界,你的关系世界给你最大的保护和依赖,由此产生的正面效果就是中国人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亲情如果按照儒家的方式来引导,它可以把一个人培养成君子,如果不受引导,它就会让人做坏事、拉关系、走后门,就像文革时期表面上都在喊共产主义多么高尚,实际上背后都在搞关系,关系就变成了一种负面的东西。
但是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他都是关系本位的。过去儒道法三股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潮都是在围绕关系本位做文章,儒家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礼制的等级秩序来塑造,法家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当做权谋之道来加以利用,道家是对人情面子的锁链非常厌恶,要逃脱这种关系,回到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个还是一个关系世界。
之所以儒道法三家在世俗世界里占统治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决定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礼大于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自由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庄子、魏晋玄学家都很重视自由,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自由当作核心价值来追求,因为每个人安全感来自于他的关系网络世界。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想把庄子所讲的自由变成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所以他们在行为方式上放荡不羁,终日喝得烂醉,结果这些人绝大多数寿命都非常短。中国近代史上倡导自由主义的,像胡适、陈独秀、鲁迅,几乎也都是不长命,只有胡适活到了71岁。你会发现秉承自由主义的人在中国由面子和人情构成的网络中难以生存,精神世界非常痛苦,因为他们协调处理不好各种关系,结果自己痛苦,也没有办法做成什么事情,会感到特别孤独。鲁迅把阮籍、嵇康看做自己的精神典范,但只活了五十几岁就去世了。
阮籍、嵇康硬要把自由主义还原到现实当中来,与无比庞大的人情面子的网络对抗,是对抗不了的。

儒道法在中国一直不衰,是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法家虽然不是经常被提起,但其实都是儒表法里,法家深得统治者的欣赏,它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透了,它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人际关系加以利用。道家是一种逃脱,儒家是一种规范,都是人对关系本位的处理方法,这个传统决定了礼大于法,礼比法在中国社会更有价值,法从来是不讲面子的。
为什么讲礼大于法,礼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礼是对人情一种规范和处理,怎么恰到好处把人情处理好,丧礼就是礼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礼,它就是处理在丧的过程当中情感的发泄和收敛的方法,它是处理这么一个问题。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制在中国文化行不通。我曾经专门写过文章,我们不是天天讲法治,官方文件也是讲法治,但谁要是今天写问题反对法治,连官方都是不接受的。
但是我一直认为法治虽然在中国也是必要的,但是它永远不会礼治更重要的。儒家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一个社会秩序的真正基础在于人的情感调适,整个社会讲所谓的仁爱德让这种人情的实践,这把这种人情的实践给创造出来,从官方的角度来善于引导这种人情的发展,让人和人之间都有一种互谅互让互爱的意识,一切制度和秩序都很自然就会生效了,就是没有制度也会有秩序,不要老是想不断的创造新的制度,老是想怎么创造新的制度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不相信这个东西,中国人永远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因为法治是现代性最核心的因素之一,但是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以关系为本位的,这个关系就是以人情和面子为核心的,就是人和人为关系为核心的文化,你会发现法治在中国文化当中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个预设是团体主义。“关系”并非总限于与单个对象的关系,还可以指与一组对象的关系,而这组对象构成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所以许烺光称中国文化是“处境中心的”(situation-centred,与美国文化“个人中心”相对)。
当一组对象构成一个团体时,就形成了文化团体主义(collectivism)。所谓文化“团体主义”,是与文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相对的,常常指把个人当把集体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的实体,因而更关心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和形象,而我则认为文化团体主义指个人本能地认为集体是个人人生安全感的主要保障或来源之一。
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集体的强调,包括今天从正面讲的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之类,以及从反面讲的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之类,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源头是一样的,即体现了他们追求个人心理安全保障的集体无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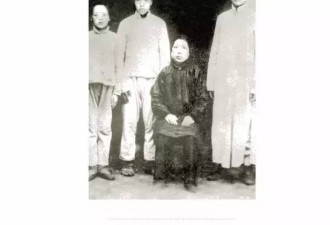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