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中超赛场唱摇滚 如今却被骂上热搜
梁龙的一天开始得很早。
“7点钟肯定醒,要是不喝酒6点多钟就醒。”他不睡懒觉,睁眼就起,这个习惯从上学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有很多事要忙,头衔一大堆:二手玫瑰乐队主唱、艺术家、演员、美妆博主,这两年又多了个“导演”。
用东北话讲,梁龙“精神头儿特足”。他的好友、导演耿军评价他,“兴趣点多,干什么上来就弄”,而且“干什么都不奇怪”。
梁龙刚开始钻研怎么当“美妆博主”那会儿,耿军一度怀疑他是在“搞笑”甚至“丑化自己”,又觉得“以他的智商,总不会在这件事上把自己弄成傻瓜。”耿军相信,梁龙要做什么自有道理,也知道他一直想拍一部电影,“他心里有故事,可能用音乐表达不了。”剧本沥沥拉拉写了两三年,改了五六稿,迟迟没能等来开拍的时机。

《导演请指教》节目组听说梁龙有拍电影的念头,说服他来试试,结果,他成了最先引来争议的嘉宾,作品惨遭“停映”。参与录制期间,乐队还在巡演,每到一站基本都是后半夜,忙忙叨叨收拾完,所有人都准备休息了,梁龙还得继续写剧本。“写着写着,梆,脑袋摔桌上了,再写,梆,再摔。我一看不行了,再摔两下,脑瓜子要摔坏了。”梁龙憨憨地笑着,盘起一条腿斜坐在沙发上,亲切得像坑头的东北大舅。
他清楚,自己的身份是跨界导演,“得付出跨界的代价”。这代价,包括时间、精力,也包括批评、质疑甚至谩骂。
01 练习
梁龙非常清楚《导演请指教》邀请自己的原因,“他们想要我这个符号”。他也纠结了一会儿,“轮到你挨骂的时候,是比比口才,还是比比智慧,就有点辛苦了。”最终决定去参加的理由也很简单——“人家拿钱,咱们拍片”,“说白了,就是个练习的机会”。
2020年《明日之子》第四季之后,梁龙陆续上了几档综艺,但始终“不太适应”。节目录制第一天,他环顾四周,谁都不认识。“又不想装有个性,又不太会很快融入。”他孤零零地找了个地方坐下,旁边的嘉宾主动凑上来聊天。聊到最后梁龙也没弄清楚对方是谁,“后来我才知道是毕志飞。”
导演组向他介绍几位嘉宾,他“云山雾罩”的。他听说过毕志飞是“现象级导演”,但对不上号。制片人李冀弢讲过梁龙不爱混圈子的细节:在西宁参加FIRST影展时,大家吃完晚饭准备转场,当晚很多导演和演员都在酒吧聚会,李冀弢提议一块过去。梁龙摆了摆手。他不爱去那种人特多的场子,李冀弢说,“倒是熟悉的几个哥们在一块,找个小马扎、撸个串,他挺愿意的。”
在《导演请指教》里,梁龙得到了两次拍摄短片的机会。第一次,他翻拍的《疯狂的外星人》在公映时被现场观众投票按停。制片人、影评人和现场观众的意见针锋相对,有人认为拍得很高级,有人认为是在故作高深,论战一直延续到节目播出后的几天。第二次,原创短片《烙花散》总算是播完了,但依然有很多人表示“看不懂”。
那是他2007年写下的故事,写了两三万字。原本是打算做一出融合二手玫瑰音乐的舞台剧,但故事的尾巴一直没收好,就搁置了。节目第二轮录制时,他想起了这个故事,凭着记忆,写了一版短片剧本。拍摄现场,美术置景空间和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只能又临时修改方案。摄影师提醒他,现场的空气密度不够,需要放烟,否则拍出来会很假。但梁龙想要的影调是“透彻的冷静”,一点烟雾也不能有。他告诉摄影师,假就假吧。
影评人杨超说,梁龙营造的古装情境是“反电影”的舞台小品式情境,这导致观众无法代入其中;制片人郝蕾称梁龙的作品“像行为艺术”,让她“看到了不一样”,“梁龙可能不了解电影艺术,但他是了解艺术的”;演员李诚儒则气呼呼地放狠话,警告梁龙“不要做导演,该唱歌唱歌去”……

梁龙没有解释。他站在银幕前,双手握着话筒自然地垂在身前,脸上挂着笑,虚心承认自己“能力有限”。在场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孟中建议他,“如果要做导演,还是应该多看看电影”,梁龙大方地表示“完全接受”。参演这支短片的《奇葩说》辩手傅首尔说,自己和梁龙都很幸运,因为擅长一件事,得到机会去做另一件想做又不太擅长做的事。
02 换一种方式讲故事
梁龙的长片计划,叫做《大命》。故事从他1998年在哈尔滨国营宾馆当保安的某个夜晚开始。那个晚上有点离奇,他遇到了几个人,每个人都在找另一个人,亦真亦幻,半真半假。在这部电影的招商PPT里,梁龙试图努力描述他概念中这部电影的感觉——有《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那种江湖气,也有《风雨云》的小神经质,还有《花样年华》里那种两性的画面感……不过,经过这么一番描述,大概就真的没有人能想象这部电影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了。
创作者的使命是去构建他自己感受到的空间。曾经那个空间主要由音乐构成,而现在,他希望也可以用影像去表达。转向的契机是几年前,梁龙发现自己记忆开始模糊,喝完酒就忘事。比如他印象中,某天酒桌上应该有某个人,和人家一聊,发现和实际情况对不上。他不禁想到,那些更遥远的记忆,是否也曾真实发生过,“你以为20年前你是那么一个角色,但也可能并不是。”
这种感受是音乐无法表现出来的。那曾经是他最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年轻时的农村体验、内心矛盾、感情纠葛,早就变成了歌曲《采花》《伎俩》《征婚启示》。记忆中的那些故事,经过时间沉淀和时空转换,在他脑海中也产生了新的思考。他决定以电影为语言,记录自己当下的感受。
2007年的一个夜晚,雨下得很大,30岁的梁龙无事可做,呆坐在16层的家中。那时候乐队几乎处于半放弃状态,演出不算多,但也够活,“租得起楼房了,两室一厅。”他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突然有些迷茫。他想,除了音乐,应该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讲故事。他把电脑打开,灯一闭,伴着雨声开始敲字:闻名东京的歌姬烙花儿,在黄粱客栈驻唱,这里每天人满为患……这就有了后来《烙花散》的故事。

《烙花散》以梦境为载体,前半段讲述男女主人公在古代发生的故事,后半段场景转换到现代,延续二人的情感纠葛
写剧本多少是出于想安定下来的念头。在那之前,2000年初,二手玫瑰在北京一炮而红,广告牌上第一次出现了摇滚乐队的名字。他们一度接到中超足球联赛的邀请,请他们在中场休息时上去唱歌。
生活喧嚣又热闹,梁龙感觉自己“混入了某种圈子”,但是记忆一片空白。2003年非典爆发,乐队的势头一下子被斩断,咬牙坚持了几年,但“有车无路”——“没有音乐节,没有Livehouse,你去哪演出?”他心里清楚,自己的歌不具备“往主流转”的气质,“许巍、汪峰转型很成功,零点乐队当时也很成功。跟他们几个老哥哥比,我还是偏另类,不具备大流行的可能性。”乐队虽然没脱离,但总是有点懈怠:市场就那么大——北京就那两家Livehouse,不能天天演吧?梁龙回忆,那两年乐队成员上班的上班,无事可做的无事可做,都没有太好的出路。
茫然四顾,梁龙将目光投向了当代艺术。他在北京798开了家画廊,“整天跟一帮画画的一块儿玩,搁家就自己寻思东西。”琢磨得多了,性格也变了,变得礼貌,“没有那么躁动了。”
直到2008年之后,市场大环境好了,哥儿几个跟他说,你不能光当艺术家,乐队不能扔了。他们开始积极排练、写新歌,2009年音乐节井喷,二手玫瑰正好赶上这波红利,演出从一年几场加到几十场,2012年达到上百场。“哇,太夸张了。”梁龙说,市场一下子就掀起来了,“我们晃晃荡荡的,也就开始走起来了。”
03 一个新人
“走起来”就会遇到新的危机。“大家好像是这个音乐圈里或者是社会的存在感之一了,你不想让它很容易地down下去,想保留它的艺术气质,每天都对这些操心,反正也没停过。”
而音乐最大的问题是复制性太强,总要一遍一遍去唱——《采花》这首歌,梁龙一唱就是20多年。“再好的作品,永远都有激情吗?”他自问自答,“多数是OK,但确实会有审美疲劳。哥们儿喝多了,点一首《采花》,你唱不唱?还好我没有大金曲,否则到卡拉OK永远那首歌。”

二手玫瑰乐队演出现场
相比之下,拍电影最吸引他的部分,是没有复制性。一部电影从开始孕育、筹备、拍摄、剪辑,到最后面向观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犹如十月怀胎,“这个孩子生完了,可以再去生下一个。”
在拍电影这件事上,梁龙是个新人。他承认自己没什么阅读,也没看过多少电影。双雪涛送书给他,他得用软件念出来听。耿军他们一群人聊电影的时候,梁龙就坐在那听一听。他是耿军口中的“烂剧王”,那些众所周知的国产大剧,他一有时间就看。失眠的夜晚总是这样打发的,开一瓶干白,边喝边看,76集的《甄嬛传》一集不落地追完了。
他的自信来自感受力。他这些年不怎么听歌,但很清楚自己要做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他做艺术品,艺术史不看,流派也不了解,“觉得哪个好就搞哪个”。拍片子也是一样,虽然阅片深度和任何一个电影青年比都捉襟见肘,但他想拍的片子,他知道它该是什么模样。
但是,仅凭感受,一个新人导演很难得到他人的信任,“啥招没有,就得靠你自己偷偷摸摸努力。”拍摄短片《疯狂的外星人》时,第一镜是过场戏,摄影指导压根儿没给梁龙发挥的余地,直接把机器架好了。“梁导过来看一眼,这个角度OK不OK?我说OK,他们说‘开’,过会儿又喊‘咔’。”等到下午拍第二镜,梁龙开始主动控制节奏,聊美术设计、聊演员调度,“他们说老梁学得还挺快。”
参加节目之前,梁龙拍过一支短片《老铁》。那是电影《大命》的先导片。2020年,他拿着《大命》的剧本报名第十五届华语青年电影周“猎鹰计划”项目创投,入围十强——当时一同入围的,还有徐峥监制、邵艺辉执导的《爱情神话》。

所有入围的剧本都要先拍一支短片。梁龙找来文学策划刘兵,一合计,干脆就拍一拍《大命》主人公“梁子”年轻时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宾馆经常组织员工搞联欢,逢年过节,梁子就上台表演。他有一股子小傲气,总想干点啥,同事也鼓励他去北京追寻音乐梦想。有一天俩人喝多了,打了一架,梁子被开除,临走之前,他们握了握手,留下一句“你的手很凉”。
拍摄时,摄影师王维华不解地问:“老梁,你长得跟个社会人儿似的,怎么找了这么个文绉绉的男演员?”梁龙一脸苦笑,“你们对我有误解,我那会儿就是文绉绉的。”他给制片人李冀弢看过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挺文静一小伙,人很清瘦,小分头,一双丹凤眼。李冀弢开玩笑说,“可能现在年龄大了,皮松了,眼睛变得特别圆。”
回忆那次为期两天的拍摄,梁龙自嘲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连开机都不知道怎么喊。”剧组班底有一半是从电影《没问题》“端”过来的。《没问题》的导演蒋佳辰也到场助阵,他觉得梁龙“很有数”,“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蒋佳辰第一次见到梁龙,是2017年的《父子雄兵》剧组。他这样描述那天的梁龙:一头圆寸,两条大花臂。花臂是假的——梁龙刚下戏,还没来得及卸妆。在这部由大鹏和范伟主演的电影里,他客串出演“狗哥”,一个狠人。在以往参演的影视作品中,他常常以这样的形象出现。

梁龙在《父子雄兵》中饰演凶狠的狗哥
但蒋佳辰偏偏看中梁龙身上儒雅的一面。他看过梁龙上访谈节目,“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斯文”,与摇滚舞台上“癫狂、张扬、骚浪的劲头”反差极大。蒋佳辰想邀请他客串出演电影《寻狗启事》中一位丑闻缠身的大学教授,但由于时间原因没合作成。2019年筹备电影《没问题》时,他又想起了梁龙,这次是主角,一个“窝囊”的中年人。2019年12月,《没问题》剧组在沈阳开机。杀青后第5天,疫情爆发。
04 不懂别装懂
《没问题》中的“老左”,是梁龙在表演上的一次突破。100多场戏,梁龙从头演到尾,过后才跟蒋佳辰提起,拍摄过程中“老紧张了,心里没底”。经纪人栗子安慰他,“没事,龙哥你就演吧,演不好还演不坏吗?”

梁龙在《没问题》中饰演一名东北父亲
他似乎演得不赖。尽管这部电影还没有公映,但在2021年连续入围了“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单元”和“第37届华沙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圈里好多人都惊讶,“老梁还能正经演点戏。”
大家对梁龙的评价出奇一致:宽广、敏感,哪怕面对自己不懂的事,他也是打开的,没什么局限性。他拍短视频,“完全是团队说怎么弄,就怎么弄。”在这位摇滚老炮的价值观里,任何形式的存在都是改变、甚至重写这个时代的审美。“我们不能用以前的时代语言去评价这个时代的存在方式。短视频有什么不好呢?”他承认自己不想过早地退出舞台,一直在思考如何去存在,如何跟市场对话,“跟时代对话,让人感觉你是一个有活力的乐队。”
2021年7月底,他随《没问题》剧组去了趟西宁,参加FIRST影展。回到北京,小区因疫情封闭管理,梁龙被迫在家待了21天。“估计他全年就那完整的21天在休息。”李冀弢说,隔离期间梁龙也没闲着,每天写剧本。在《导演请指教》贡献了几次热搜后,他又转身扎进情景喜剧《黏人俱乐部》剧组,和李雪琴、老四一伙东北人飙戏,一拍就是50天。乐队已经迈进第3个十年,岁末年初,梁龙一边忙着发行第五张录音室专辑,一边录制综艺《闪光的乐队》,累得人都浮肿了。回首这一年,他说自己有点拼,拼到了极限。
巡演、拍戏、录综艺、拍短视频、筹备新专辑……李冀弢称他为“时间管理大师”。“没想到一个70后能有这么旺盛的精力。”李冀弢又佩服又羡慕,“一个月干一件事都累够呛,但是龙哥一个月能干5件事,而且干得都很漂亮。”
前两年团队要给他拍美妆Vlog时,栗子对梁龙提的唯一要求是,“不会就不会,千万别装。”有一期要贴双眼皮贴,“我是真不知道那个小绿叶子是正贴还是反贴,自己比量比量,贴反了嘛。后来他们剪辑乐得都不行了,网友笑得差点把饭喷到屏幕上。”梁龙挺受鼓舞,“我也不是那种高级演员,能演到那种程度,那就是不懂。他们就要这个真实的反馈。”
无论搞摇滚,还是拍电影,他都坚持一个原则——不风格化。“刚开始做摇滚乐那会儿,我不知道什么叫朋克,甚至分不清爵士和布鲁斯的区别。”梁龙两眼睁得浑圆。他告诉自己,“不懂就别装懂,就按直观感受去做。”拍电影也是如此,他不想定义自己是文艺片导演或者类型片导演,“太恐怖了,我又不懂。”
梁龙很知足,“在这个年纪能选择自己想干的事,而且还能去干,那还要啥自行车?”他特别赞同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好作品是靠命来赌的”。疫情没完没了,《大命》的拍摄计划一拖再拖,眼瞅着这个冬天又荒废了,“冬天一旦荒废,只能等第二个冬天。”他希望赶紧把这部长片处女作拍出来,盘算着2022年开春先把夏天的戏份拍了,之后就“看命”了,“一步一步做吧。”








![[集市好物]2019 Toyota Sienna](https://storage.51yun.ca/auto-car-photos/310fa3ac-49ed-4cb1-8541-d63924a416fc.444x33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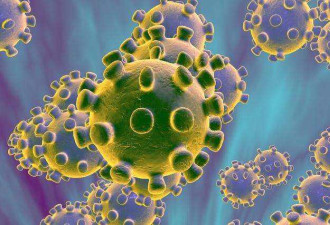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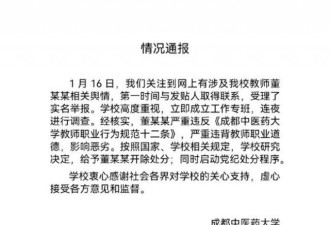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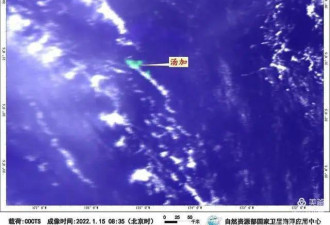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