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争吵30年 我被家暴的丈夫推下楼
他一次次威胁说,“放火把家烧了,大家一起死。” 直到他把她推下了三楼。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她还在心疼他,不希望他受到过重的惩罚。
撰文 本刊记者 李慧琪 编辑 谌彦辉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周崇辉决定把前妻杨青兰从三楼推下去,这个想法已经在他脑海里盘桓了很久,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
他和杨青兰都年过七旬,两人都患有糖尿病和并发症白内障。周崇辉的病情更严重一些,离人一米远,看不清对方的五官轮廓。他说话也不利落,有时候吭哧了半天,也想不出“餐巾纸”这样的简单词语。
周崇辉却总是挑衅杨青兰,两人在一起时常拌嘴、吵架,“我们的恩怨已经十来年了。”他说,如今两人已离婚八年,仍住在同一屋檐下。
2021年2月的一天,上海阴沉的天出了太阳,杨青兰准备在自家卫生间窗户外撑晾杆,晒一下狗的被褥,她养了两只泰迪,还有一只小土狗。
这一天,她没有一点防备。拿竹竿的间隙,杨青兰感觉到后背被一把抱住,她开始以为是狗,转脸看到周崇辉的眼睛,他正用力往外推。很快,周崇辉一手把她往下按,一手伸至脚底,将杨青兰整个搂起,推了下去。
杨青兰当即放弃了挣扎。她想,在上面很可能会被他掐死,还不如到下面搏一把,是死是活,这是她的命。她手一勾,屈膝抱紧大腿,像乌龟缩进壳里,垂直自由落体。幸运的是,落下七八米后,她掉在了一楼的雨棚上。恰巧,雨棚上还放着一个铝合金框的防盗窗,她的身体陷在了纱窗里,紧接着,后背着地。
她一动不动,在等110的十几分钟里,杨青兰穿着拖鞋,上身只有一件单薄的毛衣。她向三楼窗户望去,周崇辉始终不见人影,甚至都没敢伸出头确认她的死活。“我爱你,我想死了,我想把你杀了,然后我也死。”事发两个月后,他恶狠狠地对杨青兰说。
说起家暴,人们常以为只是丈夫打妻子,实际上,家暴阴影下的老年人群体是目前尚没有被大众看到的“更隐秘的角落”。
老年人被施以暴力的状况被大大低估。全国妇联2013年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有14%遭遇过家暴。
这一“恶劣情节”在一年后引起了曹艳梅的注意,她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庭的法官。2022年春节前两天,曹艳梅受理了杨青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在24小时内审理并送达了裁定书。
老人被家暴,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但大多数老人不愿意求助或者报警,他们认为子女打父母,都是自己的错,一是没有教好孩子,二是“家丑不可外扬”,他们害怕报警后让脆弱的亲情关系趋向决裂。
杨青兰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中少见的老年女性,她说,“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已经触犯了法律,就是因为没人跟他讲清楚,导致他一次次伤害我、威逼我、压迫我。”
24平方米内的积怨
周崇辉和杨青兰住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临街的一条弄堂里,冬天的街边是光秃秃的银杏和悬铃木。四周高楼环绕,三排公租房像是一片洼地。
他们的房子是建国后铁路职工的公租房,一共24平方米,现在被分成了八个房间。因为三楼是顶层,离婚之后杨青兰找人隔出了一个两层“小复式”,她和儿子住在上面。
打开客厅门,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卫生间的盥洗盆,有人来访时,家里的脏乱让杨青兰有些尴尬。
除了门口的老式洗衣机、微波炉和迷你冰箱,家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油盐酱醋,用完的纸盒、塑料袋等杂物塞满了整个屋子。地板上有大片污渍,还有三只狗便溺的痕迹。两位老人的床比标准单人床略窄一些,刚能容身,过道只够一个人侧身站立。他们的儿子只能在阁楼间打地铺,站着直不起身来。
周崇辉说,房子承租人是他的父亲。几十年过去,房子的租金仍然是每月六十多块。自打结婚后,他们和父亲一家就住在这里。母亲自杀后,父亲和第二任妻子搬了出去,只剩下他们一家三口。

杨青兰和周崇辉居住的公租房。(本刊记者 李慧琪供图)
他和杨青兰都是“老三届”(1966-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人生方向都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周崇辉去黑龙江插队时是高中生,杨青兰去安徽插队时在读初中,他们后来都没有再去上学。十多年后,知青返城,周崇辉去了一家国营食品厂,杨青兰顶替了父亲在国营商场的饭碗。
两人经人介绍相识,杨青兰对周崇辉没有什么好感。三天之后,他们再约见面,就吵了一架。杨青兰说,周崇辉不想和她逛街,她觉得两人没有共同语言。周崇辉说,当时自己已经三十多岁,该结婚了,其他印象不愿多谈。
杨青兰记得母亲当时劝她,“我看这个男人比较老实,蛮好的。”周崇辉的父亲曾是上海东站的站长,家里条件不错。杨青兰嘴上反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结婚后,两人关系还不错。杨青兰觉得他很“忠”,不会耍小滑头,本性是好的。三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人都认为没有过不去的原则性问题。

数据来源:上海法院从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至2022年3月前在网上公布的全部裁定书,涉及老年人(60岁及以上)的家暴案一共有42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上海约有100万工人下岗,他们也是其中之一。下岗之后,要供儿子上大学,杨青兰和周崇辉分别去做过24小时保姆和证券公司保安。现在的生活主要靠四五千块的退休工资。
“以前和他做夫妻的时候,什么事都是我去解决。我这个人嫁老公就和没老公一样,什么事都靠我自己,我既是女人又是男人。他只会张嘴巴讲,‘杨青兰这个东西坏了,那个东西该修了’。” 杨青兰最近又跟儿子提起,“都是外婆害我的”。在她看来,这段婚姻是被逼出来的。
“当时说一句‘爱’,事情也就了了”
说起离婚的原因,周崇辉只讲了一件事。
刚结婚的时候,他们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他觉得理应把36块工资都交给家里,补贴家用,但当时杨青兰每个月的工资都拿去自己花了。她的同事背后悄悄说,他们家这么有钱。在杨青兰看来,不交钱,周崇辉从来没说过什么,说到他当时对自己很好,她还会用这件事举例。
周崇辉觉得杨青兰爱慕虚荣。后来时间越长,她和家里人闹的矛盾越多。直到分开住之后,杨青兰逼着他离婚,他考虑到孩子还太小,始终没有同意。
杨青兰列举的离婚理由太多。最让她心寒的一件事和装嫁妆的车有关。有一天,她从结婚介绍人那里得知,他们结婚前,装嫁妆的车刚办过白事,上面装过黄花、白花和黑绸缎。按他们的规矩,这件事是“触霉头”的。结果他们的婚礼当晚,杨青兰的小哥就去世了,她非常痛心。

杨青兰被周崇辉从三楼推下去后出具的伤情鉴定报告。(本刊记者 李慧琪供图)
“我不会怪你,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知道我的性格,你跟我讲清楚就好了,你爱过我吗?”杨青兰说,如果当时他说一句“爱”,事情可能就了了,可他就是没有说。
从那以后,杨青兰觉得自己的心死了,两人时常发生争吵,矛盾日积月累。下岗之后,杨青兰时常觉得他没能力,事情“拎不清”。儿子也说他,脾气不好,不讲理。儿子上大学时,学费都是靠杨青兰当24小时保姆挣来的,周崇辉的保安工作也是她帮忙找的,每个周末她还得回来把冰箱塞满。
那些年,他们不再有夫妻生活。她说,周崇辉还埋怨儿子。儿子说,由父亲照顾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杨青兰也检讨自己,她要强,要脸面。她觉得世界上的女孩没有哪一个享受过她父亲那样的爱,从小放任她做所有想做的事,连她母亲都吃醋。她插队时每次回家,临走前都要在父亲额头上亲一下。
“这是我的弱点,是我不自觉地拿父亲的好,当作一把尺去衡量前夫。”杨青兰说。2014年情人节那一天,他们终于协议去离婚,两人想着儿子也工作了,可以好聚好散。
儿子今年38岁,在押运公司上班。搬出去住过一个月,后来因为生活不好,又回来了。一个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劝杨青兰,“你要让儿子出去独立生活。”杨青兰听了,没好气地说,“你不懂,别说了!”
杨青兰认为她的婚姻让儿子受到了情感伤害。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就跟她说,不到35岁,不要和他提结婚的事。杨青兰做到了,现在依然不提。她就想着把儿子照顾好,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让他吃上热乎乎的饭去上班。
“受什么委屈也要守住房子”
上海的冬天刚刚过去,周崇辉穿着一条单裤,那是他十几年前当保安时发的,红色棉服和内里马甲的对襟上都是污渍。他说自己眼睛看不见,已经两年没洗澡了,每天早上只用冷水抹把脸。弄堂门口小卖部的邻居说,看他确实觉得挺可怜的。
离婚时,协议书上没有约定双方的居住问题。周崇辉说,当时杨青兰自说自话,字也是她代签的。但比对其他文件,字迹确实是他自己的。周崇辉自己去派出所写过分户申请,请求把他们的房子进行物理隔离,但申请没有被批准。
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在前些年动迁过一次,当时给的政策是,“现在是24平,也只会返还24平,一平方米都不会多。”杨青兰说,当时租户们都不同意,没有动迁成功。但他们都知道,房子总有一天会拆迁。
杨青兰曾去咨询过律师,虽然没有买断,承租人还是周父,但现在的房子她有使用权,只要一离开就相当于自动放弃。周崇辉和儿子的关系已经恶化,她不光为自己也为儿子,受什么委屈也要守住房子,不离开一步。“在上海能拥有这么大的一间房子,我已经很知足了。”她说。

上海市虹口区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曹艳梅将保护令发给街道派出所。(受访者供图)
但周崇辉一直想把她赶走,没有成功,杨青兰的日子也过得不太平。 “你嫁给我,就是我的人。你死了,就是我的鬼。我要死了,也会拉你垫背一起死。”周崇辉曾威胁她说。
杨青兰则牢牢记住了律师对她说的话,“你不要和他发生正面冲突,不要激起矛盾。如果他打你骂你,你就要一次次报案,一次次立案,一次次拿证据。”
离婚后,周崇辉仍然大事小事依赖杨青兰去办。杨青兰会不动声色地说声“好的”。他们买鸡蛋的钱都会均摊,也会互相指责对方偷自己的衣服和东西。杨青兰觉得,周崇辉心理不平衡,他的生活逐渐不能自理,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所以他总是要“作”。直到他把她推下了三楼。
出事当天,杨青兰“啊”的一声掉下来,邻居们闻声赶来时,她已经砸在雨棚上。有人找来梯子,让她从棚顶下来,有人帮她报了警。
警察当天带走了周崇辉。杨青兰验伤后,鉴定报告上写着“左侧第2、3前肋骨折,已构成轻伤二级”。目前,这起人身伤害案已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但暂未开庭审理。
周崇辉不懂法律,出事当晚办理取保候审,他以为就没事了,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审判是什么。杨青兰说,离婚前,周崇辉从来没有对她动粗。“他讲都讲不过我,更不敢打我。” 但现在,杨青兰对他的每一次威胁都心生恐惧。
“把家都烧了,大家一起死。”周崇辉时常放出狠话,杨青兰不得不小心提防,她把家里的煤气关了,把长的、短的绳子,所有能伤人的凶器都收起来。有一次,她在狗窝旁看到一把生锈的剪刀,她心里一紧,赶快藏了起来。
每天早上八点,她会赶在周崇辉出门时下楼。如果周崇辉在家躺床上,她会立马关上门离开。下午五点左右,他上床睡觉了,她就感到安生。一旦听到他在卫生间走来走去,她就高度警惕,害怕他来找麻烦,然后把门一锁,赶快离开,直到晚上儿子下班回家。
杨青兰在外面“晃荡”,无处可去,她就去坐地铁。地铁上不冷,她的心也是安定的。一趟一趟地换乘,三小时一过又要付钱,杨青兰说,她就这样过了一年“流浪”的生活。
被家暴的一方很“强势”
杨青兰烫了红色的泡面卷发,眉毛还是从前那种细细弯弯的样式。她说起话来,声调高,思路清晰有条理,看上去没有一点怨妇的模样。不管是邻居、法官,还是居委会工作人员,都会用“强势”来形容杨青兰。
16岁那一年,杨青兰的姐姐精神病发作,父母不敢面对,她从安徽回来把姐姐送进医院,还懂得嘱咐医生“不要电疗”。
结婚当晚,小哥去世,她和领导谈条件,落实好了嫂子的上海户口、母亲的养老和侄子18岁前的抚养费。周崇辉也记得,当年她代表商场去打官司,法官夸她“这个口才,可以考虑转行了”。
杨青兰没有读过很多书,她会说“女人读书没用”这样的话,但她对待事情“拎得清”,善于摸门道。

电影《相残》剧照。
“强势”是她善用的一个生存武器,她会用愤怒和痛骂去压制对方,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居委会、派出所、妇联、法院,每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和她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摩擦。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听到杨青兰的名字,就直摇头,不愿多说什么。
在面对各个部门的要求时,周崇辉采取各种抵制和不配合的态度。杨青兰觉得,在第一次被抓后,没有人去给周崇辉做思想工作,没人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导致他一次次变本加厉。
像杨青兰这种家暴案,法官曹艳梅也见得少。曹艳梅说,从经手的案子来看,一般年轻夫妻离婚案会多一些,老年离婚的案子也多,但涉及暴力的不多。在2016年《反家暴法》施行之后,曹艳梅明显感觉到,以前受害的女性还有点遮遮掩掩,或者认为被打很正常,现在大家的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都有了很大提高。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什么,能起什么作用,一年前的杨青兰一无所知。被推下楼后的第三天,居委会的一个小姑娘给了她一份指南,上面有家暴庇护所的电话,也有保护令的申请。当时,她只是稀里糊涂地装进了包里。
直到2022年1月23日,周崇辉再次扬言要放火烧家,杨青兰又去找妇联的人。她说了几句重话,嫌他们迟迟没有给出有力的解决办法。对方当天就帮她联系了法院,约好1月28日下午两点在法院见。当天下午不到4点,杨青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就在十六庭开庭审理。

纪录片《文庙坪老人的家暴晚年》剧照。
“不希望他受到过重的惩罚“
目前,上海市虹口区法院设立了家暴案件审理的绿色通道。曹艳梅介绍,家庭暴力涉及老年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法官会优先处理,及时去查事实,杨青兰的案子就在24小时内审结。
“杨青兰已经年过七旬,马上就要过年关,如果不给她一个安慰或者定心丸,那她这个年一定过得非常不安。” 曹艳梅解释说,周崇辉从三楼推人下去,这一恶劣情节已涉及刑事,公安、检察机关目前已经介入。
尽管两人离婚后不属于家庭成员了,根据《反家暴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曹艳梅认为,周崇辉经常辱骂,言语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
但被申请人周崇辉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也联系不到。曹艳梅只得通过居委会,让他们帮忙确认他是否在家。第二天曹艳梅决定上门,与周崇辉进一步确认事实。到了现场,周崇辉态度一直很强硬,他承认推人的事实,却很不服气。他说,“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帮她?”曹艳梅一边释法一边劝解,不管怎么样,“你打人骂人是不对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核发之后,曹艳梅还专门去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和妇联做工作。在她看来,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家暴,居委会、妇联、派出所的反应其实更快捷有效。法院作为最后一道保障,主要作用在于引起各联动部门的重视,起到震慑被申请人的作用。只要当事人再去报警或者投诉,各部门都应在第一时间响应制裁施暴者。
现实中,很多夫妻申请保护令之后,是要去打离婚诉讼官司的。如果法官认定了家庭暴力,那么就认定了婚姻过错。民法典颁布后,婚姻过错是要额外赔偿的,所以法官在审理中会尊重事实,审慎核发。
另一方面,因为人身保护令的使用也可能会产生隔绝亲情往来的作用,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修复有时也不完全是正面作用,法官在核发时也要根据每个申请的具体情况,综合作出判断。
杨青兰很感激曹法官能够亲自上门,“我的命一半是她拯救的。”杨青兰说,不管案子的结果如何,她其实并不希望周崇辉受到过重的惩罚,只希望能有一个第三方在场调解,帮他们梳理一下矛盾,解开彼此的心结。
“我跟他结婚以后,从不能接受他,到后来慢慢接受他,心疼他,直到现在他来伤害我,我还在心疼他。因为我知道,他在自己父母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爱。我现在又恨他又气他,但还是想能搀扶他一把。”杨青兰希望,他们不做夫妻做邻居,好好过日子。
* 文中杨青兰和周崇辉为化名







![[二手好物]自行车(158 x 85厘米)](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a553b6b3-4872-4547-b88f-a5dcb5873bb9.1080x81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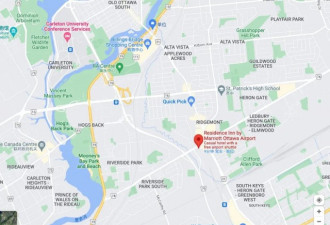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