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回不去的国 奔不了的丧

图为示意图。(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上
我爸在国内病得很重,帕金森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经失去了吞咽和咳痰的功能。
我19年回国时,他虽然说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饮食行动如常。之后跟姐姐姐夫视频通话,看上去身体还没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今年过年时,病说来就来了。
看到他双目紧闭、口鼻插满导管的照片以后,我流了好久的泪。自己老爸病成这样,作为儿子怎么可以不回去看他。但跟家人商量下来,回国集中隔离加居家隔离总共要28天,在这期间根本无法入院探视,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筹办移民时本来想,如今交通如此方便,想要回国一天也就到家了。这场疫情改变了一切,高昂的机票已经是末节,最难跨越的是国境线的鸿沟,国际旅行的暂停键已将许多短暂的重逢定格成了永久的诀别。
跟国内的医生通过两次电话,说他的病况预后很不好,还举了好几次总设计师的例子。但按照现在的国际形势,发生再大的事我可能都没法回去了,除非抛开澳洲的一切长期回国。
幸好我还有个姐姐照料一切,如果跟好多八零九零后一样是独生子女,那势必要面临极其艰难的抉择。
即便如此,我也时常对独自承担重任的姐姐姐夫心存愧疚。过年时老爸发病,医院请不到护工,是他们24小时不间断轮流看护,一把屎一把尿地擦洗。
那时候我就天天想着,要是自己在国内,就可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们也就不用这样劳累了。
现在老爸一直在重症室,不需要家人陪护,但他们也必定会时常接到医院电话告知病情的反复,一颗心也会一直悬着,想象着姐姐平日的表情,应该就如同奥斯卡提名片《父亲》中那个憔悴无奈的女儿。
正如影片所揭示的,国内国外,无论社会保障的高下,子女如何安置高龄父母都是一个难题。风烛残年的虚弱,子女分居的孤独,尤其是失智以后无法厘清现实与记忆的恐慌,都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
“父母在,不远游”自然是断章取义,但“父母老,怎奉养”应该是横亘在许多移民心中的一道坎。《父亲》中那个女儿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从伦敦搬去了巴黎,但好歹路程不远,还能时常回养老院探望。我们这些万里之外的游子一年探望一两次也就算尽力了。
搜了一下新足迹论坛,面临这类困境的一代移民还真不少,尤其是没有兄弟姐妹的那个群体。有毅然放弃身份回国的,但多数人思前想后,还是安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在忠实理想和孝顺父母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事业也就罢了,但除非自己的儿女已经可以独立生活,否则怎么也不甘心让孩子回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坑里爬行。
我离开时,有亲戚说我是为孩子牺牲了父母,当时觉得言重了,如今想来其实是言中了。父母身体好的时候感觉无所谓,等到病来如山倒无法在床前嘘寒问暖时,才发现自己曾经是如何的铁石心肠。
想起来也是自己出国前考虑不周,没有仔细关心老爸的病情,只知道他在按医嘱服药。如果对帕金森有详细了解的话,可能会帮他找到更好的用药和疗护,恶化起来也不会这么快。
从前听说西方人家庭观念淡薄,子女成年后两代间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澳洲才发现也不尽然。我见过祖孙三代同堂、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的,也知道不少子女就近照顾高龄父母的。
我公司的前CEO就在他父亲病重时住在一起,照顾了两年直到去世。我女儿同学的父母为了照顾生活不便的奶奶,不惜举家从悉尼搬迁到四小时车程之外的偏远小镇,大人的事业和小孩的教育都重新开始。
人心都是肉长的,再怎么佛系都逃不脱良心的折磨,再怎么解放都解不开距离的困局。
如果想穿了,每个人都要面临生老病死,很痛苦,很残酷,也很无奈,但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渡过最后那一段痛苦残酷无奈的日子,亲人在旁至少会有些内心的慰藉。
年纪慢慢大了,关于父母反对出国移民这件事,我的观念也有了些改变。如果父母年逾古稀,自己又是独生子女的话,“说走就走”之前的确要筹划周全才是。年龄越是上去,老年人需要照顾的那个时间点就越来越迫近,脑子可能说糊涂就糊涂了,身子可能说倒下就倒下了,总要有个信得过的人照看的。
有条件的当然可以安排父母移民,但如果父母本来健康状况不好的话,体检也是很难通过的。对我爸妈来说,听到十几小时的舟车劳顿就立马退缩了。而对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而言,移过来以后语言难沟通、生活不适应也是个巨大的问题。
带着孩子跟父母远隔重洋,一边是难以割舍的过去,一边是想要创造的未来。这道选择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得不做,却也只能硬起心肠自私地勾选那个更容易的答案。
世间安得双全法,别时容易见时难。在父母这件事上,找再多的借口我们都无法做到问心无愧,这恐怕就是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吧。
下
我爸去世了,离我写《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一年零一个月,世界已天翻地覆,被各种边界阻挡的归心也慢慢心灰意冷,每一次相会似乎都有可能定格为永别。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跟我妈通电话的时候,我还是控制不住眼泪。对帕金森晚期的病人来说,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病情时好时坏,谁也说不准这一天是哪一天。这些日子来我听着纷至沓来变幻莫测的防控消息,看着日历上的数字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如何加减假期、去程、隔离、回程的天数才能赶上那个点。
一年来,我爸身体各种功能都已退化,吃不了饭,说不了话,意识似乎也已模糊不清。每次我在视频、照片里看到他身上插满导管的样子,就会想象他种种有苦说不出的痛楚,为他感到憋屈难受,却又无能为力。如今这样,也算是一种解脱。要是上海式封控也在这里降临,天知道又会是怎样一种结果。
我通过视频观看了出殡,也远程作了答谢。幸好老家没有病例,但吊唁人数也有限制,流程走完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先去吃丧筵,而是先做核酸。为了预防疫情的变数,五七的仪式也要提前到二七匆匆做完。
亲友都谅解我的无可奈何,劝我不必担心,不要难过。越是如此,我的愧疚越是不能自已,耳中不时响起一句歌词——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出国这件事本身,当然已经是最大的不孝。一年来,我一直在想,到底能够做点什么来弥补自己对上一辈的薄情寡义。想来想去,理性强迫症之下总免不了在脑海里斤斤计较各种利弊得失,始终无法把自己当作无牵无挂的单身汉那样不顾一切说走就走。何况疫情之下,医院重症室只允许偶尔的探视,到了门外也使不上什么力气。
上个月,美国薛律师那篇《我在中国三个月的魔幻之旅》更是打消了我仅存的回国念头,也让我找到了继续铁石心肠的最后借口。
我爸生前其实是个挺孤独的人,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做事的风格,单纯,正直,却不为多数人所理解。
他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人,读书读到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乡下算是高学历,但他也因此跟小学没读完的我妈没有共同语言。他不是个会哄女人的男人,每次吵架他只撂一两句狠话,我妈就哭。
他在乡里的校办厂做了半辈子的电工,四十多岁时因为技术过硬,被校长指定为厂长。他当厂长那几年,我们家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是他干活也更卖命了,每每跟手下的技术人员研发新产品直到深夜。他在电工技术上确实很有天赋,自己设计的验电笔,还申请过专利。
只是他这人没有什么物质占有欲,干活常常自掏腰包买了工具也不报销。我妈说,人家当厂长,都是把厂里的东西拿回家用,只有我爸会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厂里用。
他厂长当了几年,就决定要提前退休,说是激流勇退。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齐声反对,都觉得他的位子坐得稳稳当当,大把的人都跟在后面眼巴巴地讨好他,这么早退休毫无道理。但他执意要退,谁的话也不听。
后来,接任的厂长很快把厂子转制为私人所有。如果我爸能这么干,我现在的光景也一定大不一样。但任凭别人怎么说,我从不觉得我爸有什么错,内心深处也没有一丝的埋怨。他只是去过自己想要的清静生活,他已经把我养大成人、供我读完大学,给后辈留下财富名位并不是他的义务。
俗话说,多个朋友就多条路。但我爸的说法是,多个朋友就多点麻烦。是的,他不热衷场面上的社交,不喜欢酒桌上的朋友,用世俗标准来看,他就是个孤僻清高的怪人。因为做厂长而带来的那些朋友,在他眼里并不是资源,而是负担。可以想象,当年他每天收到多少巴结奉承,心里就会有多少别扭难受。他其实就是干活的命,不是做这个长那个长的料,更别提生出要将工厂占为己有的野心。
后来,我听人说他在六七十年代那场运动中吃过苦头,更加明白了他对“朋友”这种麻烦的畏惧。那时由于跟他交好的一个老师被批斗,他也受到了牵连,各种游街、毒打。他自己从没跟我说过这些,但书柜里有一本他老师的回忆录,种种斗到报纸贴满全身、打到短裤粘连屁股的细节,不忍卒读。
有些创伤,注定一辈子无法完全愈合,这也使得他在这个人情社会里小心翼翼,始终不敢用力拥抱任何一个成年人,害怕伤口在挤压下再次敞开。
他看上去严肃古板不可亲近,却从未对我和我姐说过一句重话、动过一根手指,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要求都没提过半句。就算是我出国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对我万分不舍,却也没有激烈地反对。他就是那样,较真而又大度、固执己见而又与世无争。
只不过跟很多传统的中国父亲一样,他关爱我们,却从不挂在嘴上,所以我很长时间内浑浑噩噩无知无觉。直到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献血体检,我打电话跟他说我测下来血压偏高,他第二天就坐火车过来带我去医院复查,发现并无异样才放心回去。我送他去火车站,看着他转过身一步步走向入口,弓着背脊,满头白发,猛地想起朱自清的《背影》,不自禁地鼻子一阵酸痛。
只是少年心性的一时触动,阻止不了成家独立后的心生异志。他最终用他沉默的宽厚,成就了我任性的凉薄。
再见了爸爸,但愿天堂里不再有病痛的折磨,不再有斗争的狂热,不再有疫情的阻隔,却有更多懂你的灵魂。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荞爸的澳洲来信)






![[集市好物]2012 Fiat 500](https://storage.51yun.ca/auto-car-photos/cb37e2e1-d5b7-419c-8157-79f465cb524a.1080x144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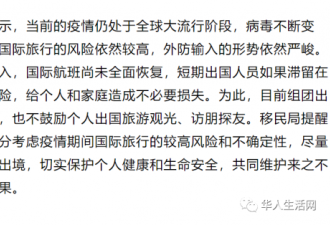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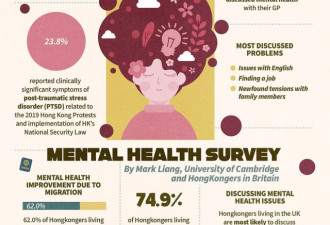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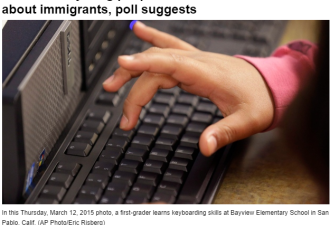





病毒不会人传人。。。中共说过的
病毒来自鲜活市场。。。中共说过的
病毒来自意大利西班牙。。。中共说过的
病毒是美军带来的。。。。中共说过的
病毒是美国实验室出来的。。。中共说过的
世卫第一次调查,不让接触武毒所实验室人员。。。
武汉病毒爆发时,对内封锁武汉到国内各地航班;却同时让武汉飞往世界的国际航班运行,故意将病毒散播到全世界。
从来不敢公开因搞封城动态清零而造成的其它病患(癌症手术,化疗,肾脏透析,心脏病等等等等)无法就医而死亡的人数
一切,都是习包子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一切,都是中共在造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