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境城市的第九次封城和解封


早上八点半,腰酸背痛的林珊回到家,脱下鞋袜,大拇指外侧磨出了硬币大小的血泡。腿上的牛仔裤遍布污泥,黄色薄外套的右胳膊肘被树枝划开了口子。
已经在边境线上巡逻了24小时的她,匆匆洗完澡,一头倒在床上。补完五个小时的觉,她还要去社区上班。
守边,本不是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内容。瑞丽接连暴发疫情后,林珊和同事们接到去边境值守的通知。
彼时,瑞丽正经历第一次封城。林珊和同事们被调往边境线,每人负责守卫1.5至1.8公里,24小时轮一次班。从早上八点到次日八点为巡逻时间,下午三点回到办公室再继续工作。
身为女士,林珊每周轮值一次;单位里的男同事,则需两三次。
严峻的防疫形势源于瑞丽独特的地理位置。从地图上看,瑞丽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像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镶嵌在中缅之间。
两国边境没有明显的地理屏障作区分。田间地头、村舍两岸,都可能是中缅的分界线。“一寨两国”普遍存在:村寨东侧属于中国,西侧属于缅甸。瑞丽市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防疫难度大。特别是位于瑞丽东侧的姐告贸易区,只需步行一分钟,就可跨越边界,入境缅甸。
疫情暴发前,瑞丽具备发展外贸行业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当病毒来袭,复杂的边境线却成为险象丛生的烫手山芋。
“边境线难防。”精疲力竭地回到家,林珊忍不住向丈夫感叹。
为了守住防线,不仅是林珊这样的基层公务员要值守,其他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员工也接到了分包边境线的任务。瑞丽规模较大的私企员工,也被动员去戍边。据2021年11月25日《中国日报》报道:在长达169.8公里的边境线上,瑞丽共设一线执勤点631个,目前投入各方面力量8821人参与“守边”,24小时轮流值守。
林珊和同事们分到的守边环境相对艰苦——靠近瑞丽江畔的一段山路。潮湿粘腻的南方城市,蚊虫蛇蚁遍地。即使穿着长袖长裤,她露出来的脖颈和脚踝仍躲不开蚊虫叮咬。被分配到山上和河边巡逻的男同事,“胳膊和小腿惨不忍睹。”
巡逻路上,林珊见过1.5米长的蛇、比成人拳头还大的鼠、成群出没的硕大蚂蚁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昆虫。
第一天晚上去守边,林珊由于缺少经验,穿了常穿的黑色皮鞋,三个小时走下来,两条腿疼得迈不开步子。巡值完两周,林珊身上多了三块膏药。
轮守了几次,大家攒出了经验:在边境线上巡逻,手电筒、木棍和驱蚊水是必备之物。
林珊并未接受过系统的体能训练。和其他穿着迷彩服的官兵相比,光是体力这一块儿,她就落下许多。
体能落后的另一重困扰是精力不足。一到深夜,轮值人员开始双眼朦胧。为防犯困,林珊和同事们随身携带着风油精。到后半夜,迷迷瞪瞪的他们依靠来自太阳穴的刺鼻味道提神。
缅甸动摇的局势也是威胁。2021年2月初,缅北爆发了军事政变。靠近缅北的戍边人员和村民得随时提防流弹的袭击。在夜里,他们常能听见枪炮声划过夜空;碎裂的弹片有时直直落下,砸在草丛中。
更不要提六月后 ,公安督促远走东南亚的中国籍诈骗分子回国自首,个别省份发出公告:限期回国自首,否则注销户籍。
自首的流程是:待入境的中国人直接去边境处告知守边人,然后在边境线上——也就是铁丝网一侧等候核酸检测,之后乘救护车去集中隔离点,解除隔离后返回自己的家乡。
一时间,多达上万人排起了长队,等待回国。林珊亲自接手过近十位申请入境的人员。
一旦遇见偷渡者,运气好的,可顺利将他们驱赶;运气差的,容易发生肢体冲突,受伤在所难免。林珊听说过一个案件:在姐告贸易区的中缅街,伺机偷渡的缅甸人曾用啤酒瓶袭击边境上执勤的巡逻人员。
对边民来说,穿越中缅做生意、讨生活是走几步路的事情。而在特殊时期,这一切都变了味:白天刚拉的铁丝网,夜里就被剪断;木栅栏被人连根拔起;围墙两侧,时不时冒出一条简陋的地下通道。
最难守的是河流,总有人装作游泳漂在缅甸一侧的公河上,巡逻的人刚走开,就趁机游过来。林珊想起男同事讲的段子:“半夜四点拿手电往对面一照,黑漆漆的一个人脸,等着跑过来呢。”

■ 2021年4月2日凌晨,封控人员值守在中缅界河瑞丽江的河滩上。
外防输入,瑞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为达到“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五十米一个执勤点”的防疫要求,普通百姓也参与到守边任务中来,比如公办学校的教师、私人商铺的老板、刚成年的学生,通过社区和村委会报名,都可领取值守任务。在守边路上,林珊遇到过好几个稚气未脱的高中男孩结伴巡逻。
除了值守边境线,大家分配到的任务还包括对城区街道的值守。铁丝网一拉、木桩一打、小板凳一放,就是一个守卫点。
“难,真的是很难。”林珊深感疲惫,却无能为力。没有别的选择,大家只能硬扛。

瑞丽总共封城九次,累计封控时长达160天。居民的生活被按下漫长的暂停键。
魏秋在瑞丽长大。疫情两年,她没怎么出过门,对这座城市已经感到陌生。
第一次封城长达35天。最开始的一个周,夫妻俩还焦虑地刷抖音,获取疫情的近况。闷在家里久了,实在无事可做,魏秋的丈夫报名做了志愿者。
他的志愿服务任务是“守卡点”。身穿防护服坐在马路中央,防有人出门随意行走。马路已经被铁丝网分段阻隔,每一个路口,就是一个“卡点”。
魏秋的丈夫和其他志愿者三班倒,吃政府统一配送的盒饭。遇上人手不够,连续执勤的时长达到三天。
犯困的时候,他和相邻不远的志愿者轮流靠在椅子上打盹;没有盒饭配送的时候,全靠泡面和火腿肠充饥。疫情期间物价跟着上涨,一桶泡面和火腿肠,加起来卖到15元。

■ 2022年3月2日,瑞丽市一小区门口,一市民把方便面等生活物资递给里面的朋友。
魏秋的女儿快三岁了,由于频繁做核酸,产生了稚嫩的肌肉记忆。看见身穿防护服的人,孩子自动张开嘴巴,发出乖巧的一声“啊”。魏秋心疼女儿:“大部分时候,我抱她出去,都是排队做核酸。”
不过,比起孩子单调的童年,更让魏秋一家人糟心的是生存本身。封城之后,小两口经营的饭店停业了。
店铺在姐告贸易区的主街道上,是一家人的收入来源。饭店五十平不到,放得下十张桌子,门外的走廊上还能再摆三张。一到饭点,几乎没有空余的座位。单价基本在10-30元之间,以售卖各类快餐为主,面粉饭都有,炒菜种类多。
店里三名服务员,其中两名是缅甸籍。魏秋家的客流得益于边境的繁荣,将近一半的食客是从事外贸生意的缅甸商人。据新华网报道,姐告贸易区在疫情封闭前,每天通关过境人数超过4.9万人次。这是全国陆路查验外籍人员最多的边境口岸。
魏秋从没想过,在如此优越的位置开店,也会陷入经济上的困窘。往常里,小店每日流水达到3000元以上;再算上外卖平台提供的生意,每日营业额有4000元左右。
封城之后,一切都变了。
出现在姐告贸易区的缅甸面孔一下子少了很多,店里的生意随之降低了60%。两个缅甸服务员返回家乡,归期未定。
第一次宣布封城时,魏秋还记得自己并没有太当回事:“关门几天嘛,影响也不大。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在家陪孩子待几天。”
确诊病例持续上涨,来自缅甸的偷渡客也未消失,“清零”仿佛看不见尽头。第三次封城来临,魏秋意识到“不对劲了”——封城,似乎有常态化的迹象。
暂停堂食后,餐厅的入账更少了,一天500元不到。外卖平台倒是能接单,但是生意惨淡到连水电费也覆盖不了。最心酸的一天,线上营业额只有23块。
一旦饭店没有进账,经济上的压力,就无法避免。魏秋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营业。善解人意的房东答应减免40%的租金,但加上房贷后,每个月接近一万元的固定支出依然让她感到举步维艰。魏秋不得不遣散了剩下的一名服务员和厨师。
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让家里的气氛也不似从前。有一天中午,吃完饭的女儿哭闹不止,一定要出去玩。魏秋哄不住,一旁的丈夫忍不住发脾气,一巴掌拍在孩子的屁股上:“闹什么闹,没看见爸爸妈妈都快烦死了!”
姥姥一把夺过孩子,带着哭腔说:“大家都难过,你冲孩子撒什么气?”
解封的间隙里,店铺曾短暂地开过几天,但禁止堂食,营业额也不及之前的三分之一。
魏秋抱着孩子出门转了转。这座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已经变得陌生——街道是空的,没有人也没有车,学校里寂静无声,商场和影院都关门了。
街道上的铁丝网和路障依旧没有拆除,每一个路口都有木桩和围栏,想要抱着孩子稳稳跨过护栏,有一定的难度。

■ 2022年3月4日,瑞丽一街道上难觅行人车辆,居民居家隔离,严禁非必要外出。
魏秋熟悉的几个做外贸的朋友全破产了。人们不得已开始求助。境况最艰难的时候——2021年10月份,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上,与瑞丽有关的民众留言超过600条。
2021年10月28日,曾任瑞丽市副市长的戴荣里发表了《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一文,获得十万以上的阅读量。评论区里,众多瑞丽市民感激他勇敢发声。
市政府和民政局先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支持政策》和《进一步做好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实施方案》,推出99个政策:“将从房租减免、资金拨付、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民生救助等方面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保障民生”,“对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的,按户给予临时困难救助、适当放宽低保认定条件等保障”。
魏秋询问做生意的朋友是否收到补助,得到的回复往往是:“大家都差不多,政府也没钱了。”余下的话,没人继续讲下去。

有人留守,便有人离开。
2021年4月,瑞丽公布的全市核酸检测总人数38万;到2022年4月,这一数字降至19万。瑞丽市的一位政府官员向《中国慈善家》杂志表示:“网上流传的‘常住人口从 50 万降到 10 万’的说法有些夸张,20 万人还是有的。”
人口迅速外流的背后,是当地产业的萧条,其中受创最重的是瑞丽的珠宝行业。
瑞丽是东南亚重要的珠宝玉石集散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瑞丽的珠宝街,被誉为“全世界最富有的街道”。
2010年,瑞丽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被寄予厚望。玉石行业进入第一次快速增长期。繁荣时期,整条街无论白天黑夜,灯火通明。瑞丽珠宝商的主要聚集地在姐告边境贸易区,遍地的商铺都与玉石有关。
直播的兴起给瑞丽珠宝行业带来第二次繁荣。据人民网报道,截至2020年5月,直播从业人员超过6万人。
在瑞丽做了三年珠宝主播后,汪恬恬决定离开,“总要想办法挣钱啊。”她负责直播的商品是翡翠手镯。
从晚上七点到十二点,出现在直播间里的汪恬恬妆容精致、嗓音清亮。手边,是一杯温水和打开的咽喉含片。灯光一打开,翠绿色的镯子在她白皙的手腕上投下暗绿的光影。
为了避免被隔壁的主播压住气势,汪恬恬必须提高嗓音,卖力地跟顾客保证:“假一赔十哈,各位!”屏幕另一端,往往有数十位买家争先问价和竞拍,一块上等的翡翠镯子能卖到上百万元。
汪恬恬的主要收入靠分成,鼎盛时期月收入超过10万元。在珠宝直播基地,有超过3500名像她一样的主播。基地关停前,他们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对着镜头展示、叫卖自家的翡翠制品。
繁盛的贸易带动了大大小小的服务产业。簇拥在姐告贸易区周边的是数不清的小酒吧和餐馆:在这里,每天有上万人在流动和交易;这里的人,从不缺生意做。

■ 2019年6月8日,在瑞丽姐告玉城市场里,上万名玉石直播销售人员正在交易。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外籍人员来到姐告经商、务工,形成了聚集区。姐告常住人口为1.5万余人,外籍人员就有5000多人。缅甸人是最常见的外籍面孔,原因简单:缅北矿带是世界公认的高质量翡翠原石产地,瑞丽珠宝城的玉石大多来自那里。
疫情带来的冲击迅速而激烈。出于对输入病例风险的担忧,第一轮疫情出现后,跨国贸易被暂时搁置。官方也下达了明确禁令:2021年4月1日起,瑞丽全市珠宝交易市场、直播基地和所有线上线下的经营活动叫停。
姐告贸易区两轮疫情后,姐告与瑞丽主城区之间唯一的通道——姐告大桥禁止通行,姐告片区人员原则上不进不出。上万名商人先后离开了贸易区。留守的,只剩下看管贵重资产的300多人。
刘国平是离开的商人之一。他在姐告做了十多年玉石毛料生意——从缅甸进口毛料,直接售卖珠宝原石或简单处理后的翡翠给下游加工商,业务覆盖线上和线下两部分。他不愿详细介绍个人名下的资产规模,言语之间,透露着昔日的辉煌与富庶。
线下交易停止后,仓库里的玉石毛料无法发货,之前预定的货物也卡在关外。营业额骤降至零元。线上的直播也没法继续售卖。
为了留存粉丝,刘国平让主播开直播跟顾客聊天,也亏本卖过一些小商品。主播很快提出辞职,准备去广州找新的工作。刘国平没有阻拦。
政策规定,离开瑞丽需要向所在区域的网格员申请,经同意后去指定地点(或酒店)自费隔离七天,再自费做三次核酸,第三次还是“双采双检”(鼻咽拭子和口咽拭子)。复杂的隔离程序未能打消人们离开的决心,办理《离瑞证明》的人在政府大楼前排到数公里。
“与其守在这里等‘死’,不如出去看看。”停市七个月来,刘国平亏损高达七位数。不愿多谈的他,感叹了一句:“活着都难。”
姐告的珠宝街里,背着玉石毛料的缅甸人回家了,卖手抓饼的小推车消失了,酒吧也不再有生意。麻辣烫、江西瓦罐汤、广东猪脚饭、傣族鸡脚,这些平日里熙攘的小店全都关门了。姐告大桥变得空空荡荡。
汪恬恬算过:离开瑞丽自费隔离,机票、酒店等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是,不舍得花钱,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积蓄见底。离开瑞丽那天,她发了一条忧伤的朋友圈:“再见了,我奋斗过的地方,我爱的瑞丽。”
没有准确的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到底有多少人离开了瑞丽。但是,如林珊和魏秋的形容:“肉眼可见的,快变成空城了。”
解封日终于到来。2022年5月1日,瑞丽市的珠宝玉石市场宣布恢复营业,只是缺少了从前的盛景。开门营业的商铺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珠宝店,卷帘门上仍盖着厚厚的灰。

■ 2022年5月9日,瑞丽市德龙珠宝夜市恢复营业。
魏秋抱着女儿,和母亲一道出门。街上出现了人群,商场和电影院也开门了,不过进出需要查看核酸阴性证明。
听着街上的人声与车声,林珊有种奇异的感动:大家似乎慢慢的,从长期居家的状态中缓过劲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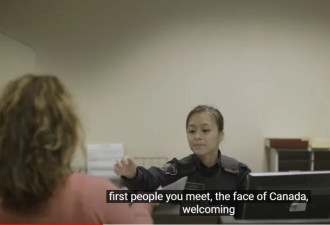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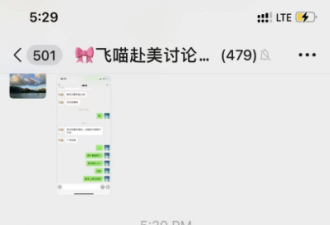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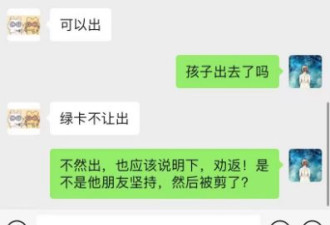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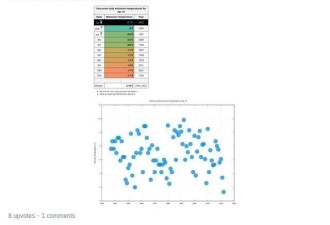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