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给我最令人愉快是对不同文明的吸收

许知远,男,1976年出生,江苏灌南人,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现任职于《生活》杂志。
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他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曾出版《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历险》、《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
“美国人最幸运之处在于
他的历史是一张白纸”
大约171年前,确切的时间是1831年4月,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博蒙动身去美国。仅仅一年前,托克维尔刚刚结束在巴黎的学生生涯。在校期间,他深受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后者认为,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将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胜利。
英国左翼思想家拉斯金后来认为,导致25岁的托克维尔最终决定前往美国考察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托克维尔的自由理念与他的贵族家庭发生了冲突;二是面对混乱的法国政局,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尽管在那个讲究辩论的时代,他的口才太糟糕,又太不适合于权力游戏与煽动民心。
去美国的一个直接目的是,他希望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因为法国的实在太糟糕了。但从1830年11月起,他开始想写作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因为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又人人无法说清的话题。
拉斯金在20世纪40年代说,在19世纪初谈论美国,就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谈论苏联一样引入注目。或许我还应该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谈论中国与毛泽东这一现象,因为当时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个陌生的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会说,“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能为现实提供参照,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在现实中,我们会通过观察别人而反省自己。同样地,在努力理解其他国家与民族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找自己的弱点或是优势,寻找改进的方式。
托克维尔带着“改造法国”的愿望前往美国,在当时横穿大西洋需要38天。托克维尔尚不知自己赶上了了解美国的好时刻。纽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路易斯·P·马瑟在2001年出版的《1831年的日蚀》中将1831年视作美国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建国之后,内在冲突在这个年轻国家里愈演愈烈:蓄奴者与废奴者、宗教与政治、州政府与联邦制、机械力量与自然力量……此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个人特性似乎正暗示了这种混乱,这个总统一直到结婚前都不识字,他的妻子后来教会了他。他还曾经与人决斗,并杀死了对方。这样一个人竟成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所以,托克维尔很自然地发现,在这个年轻的国家里粗俗与活力同样显著。
这次旅行持续了9个月,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拜访了上千人,他们用同样的方式与总统和平民交谈。这次旅行的结果演变成《论美国的民主》,它在1835年出版了第一卷,迅速为托克维尔赢得了名声,却并未给他带来更理想的政治生命。他和写作《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一样,都善于在书中表达政治智慧,却从来不会运用。
仅仅依靠9个月的旅行,一个人就能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吗?当时法国最伟大的批评家圣伯夫在表示赞扬之后,仍不无刻薄地补充道:“他还没有学到什么,就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时至今日,《论美国的民主》依旧是该领域中最权威的作品,就连美国人自己都这样认为:托克维尔希望在美国的发现能够为法国带来生机,而美国人则在这个内心倾向贵族制的法国人身上看到了自己。


托克维尔与他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
关于美国与美国人的特性,托克维尔用“缺乏传统”与“民主制度”来解释。他写道:“美国人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历史是一张白纸。”最初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的那一群人渴望摆脱欧洲令人烦恼的教会冲突与种种束缚,他们没有多少追求,不过想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生活。而当时间到了1789年时,第二场严峻的考验摆在美国人面前。詹姆斯·麦迪逊、本雅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创造了《权利法案》的过程,仍旧是历史中的一个谜团,他们的确创造出一种能够让“自由与秩序”并存的制度。政府受制于人民,而非人民由政府控制。当时主要的美国政治家几乎都是启蒙运动的传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这些最初的立法者——是不同势力间的彼此制衡确保了民主制的延续,在孟德斯鸠那里就是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
好了,回到1831年的美国。总之,它已经具备了现代美国的一切特色,人们在民主制度下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生活习性,包括后来人们总是谈起的“对金钱的迷恋”、“对公共生活的热爱”、投身于工商界更甚于政界与军界,还包括他们为什么热衷于要别人夸奖自己,如果别人不说,就自己夸奖自己。托克维尔对此的解释是,美国人实在没有历史,更没有贵族传统,在英国这样的贵族传统中,贵族们认定自己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此从不心虚,而美国人则缺乏这种自信,他们必须不断重复,才能相信自己。
托克维尔也提到过分民主化的危害,比如人的平庸化、缺乏伟大事业心、群众的暴政等等。杰斐逊在1789年时也有这个担心,所以他强烈要求设置贵族色彩浓厚的参议院,以便与平民色彩为主的众议院抗衡。
但不管怎样,这种美国的民主制让人看到了生机。尽管1831年的美国,除了制度,没有任何令人骄傲的成就,这里的居民沉浸在无知的自满之中,他们的阅读作品主要来自英国与欧洲,除了最基本的层面,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与信念。用拉尔夫·爱默生的话来说,美国精神仍未觉醒。
我们的世界
对我来说,美国给我的最令人愉快的印象是它对不同文明的吸收。尽管我在肯尼迪机场还是感受到某种压抑,并在华盛顿一家酒店里遭遇到了种族问题。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华人,你很难真正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甚至还可能遭遇李文和事件。但美国还是提供了别的国家无法比较的宽容。美国人会把法国人送的自由女神像作为自己的标志、它在二战期间对于欧洲难民的接纳、帮助美国人建造原子弹与卫星的人很多来自欧洲与中国,还包括每个人都知道的硅谷。美国的民族自尊心也不那么强烈,他们心安理得地把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莎士比亚当成自己的遗产,就像他们自己的马克·吐温。他们也把花木兰当成自己的动画片主角,即使没有那样亲切。他们对更高级的文明也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在美国学界最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都是那些与欧洲传统更为紧密的人。除了商界与学界,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起到了支配性作用的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都是东欧的难民,奥尔布莱特同样是。
决定一个国家的真正水准,是他们的亚精英层与精英层的大小,《纽约时报》的100万读者,或是《新共和》的10个人订户都属于这个层次。他们的大学与无数的智囊机构都在像政府一样思考着全球化的问题,并进行争论,也在相互抵消。
如果你身在纽约,你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在世界经济论坛召开前夕,迈克·艾略特在《时代》上撰文说,纽约是典型的全球化城市,这里的外国人已经占40%,多种文化使这座城市充满活力。
从这层意义上,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缺乏一个更宽广的胸襟去吸收整个世界的遗产。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依旧不是一个领导性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能力去与美国或者欧洲抗衡,我们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处于弱势,我们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也同样乏善可陈。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即使不为零,也是微乎其微,我们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思想家、作家,甚至连一份亚洲领导性的报纸都没有。
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一段不可能消除、也无需消除的历史负担。从西方照搬新模式也不可行,但是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去学习与实验却是当务之急。老实讲,我们缺乏基本的现代的政治、商业与文化理念。以我们的行业为例,新闻的理念来自西方,而非我们自身的,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依旧在学习在美国媒体中可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比如独立的编辑制、比如新闻写作的基本手法,如果你连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都不了解,你不可能产生什么创新。
况且,这种学习的过程并非令人无法忍受,也不是什么忽略中国国情。总是谈论所谓“中国国情”的人,往往是一群被“意识形态化”的人。我们首先是人,我们有人类的通性,其次才属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
对于这一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阿根廷作家及其传统》中说得极为清楚。他说,认为阿根廷作家必须写作阿根廷特色的作品是愚蠢的。他说,在阿拉伯文化标志的《古兰经》里,根本没有提到过骆驼,因为对于先知默罕默德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去加以突出,只有一个伪造者才会努力突出骆驼。同样地,如果因为拉辛写作古罗马与希腊题材,就认为他不是法国诗人,或是认为英国人莎士比亚不该选择丹麦王子作为主人公,也是极度可笑的。事实上,英国最伟大的两位作家,莎士比亚与乔叟都是处理意大利题材的高手,而在意大利的歌剧中,中国的公主图兰多也可以成为中心人物。
博尔赫斯在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应该把整个宇宙看成我们的遗产,不能因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局限于阿根廷的特色。”我希望,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理解这些。只有我们对自己足够自信,我们才可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吸收别的文化的遗产,本·拉登的信徒才会有此障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要让你觉得因为身处发展中国家而身份卑微,或是产生某种令人厌恶的谄媚心态。对于这一点爱德华·萨义德在驳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说道,从更长的历史范畴看,不同地区的此消彼长是很正常的。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空前繁荣的时候,西方世界正在黑暗与沮丧中不能自拔,这并非自欺欺人或是狂妄自大,而是提醒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是先进还是落后,我们都是更宽阔的历史长河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文明是流动的,我们永远处于彼此学习的状态之中,保持自尊与学习的热情,是我们获得进步的基本素质。
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正身处一个类似于1890~1930年间的美国的状态,它的混乱程度与蕴涵的机会都极度相似。现代美国的模型在那时建立,主要的机构,包括《纽约时报》、《时代》、《纽约客》都是在那时走向成熟的。今天的美国人在享受那两代人的遗产。所以,令我感到激动的依旧是,我们或许无法立刻享受到类似美国今天的物质的便利,却被赋予了写入历史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们记住的,依旧是亨利·卢斯、普利策,而非今天的《时代》杂志的主编。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历史的真正缔造者。
最后,我想以托克维尔一段话作为本章结束语。这段出现在《论美国的民主》序言中的话是如此空洞,今天读起来却仍令人鼓舞,并将继续鼓舞后来者:“我们从哪里能获得比这更大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效仿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它的教育之类的制度,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节。法国的法制,可以而且最好是应当不同于美国的法制,但是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
生活服务
-
 有问题吗@ 2022-09-06 16:05您已点过赞美国给我最愉快的就是能看到零元购等美丽的风景线,和政客们整天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内心无比龌龊。
有问题吗@ 2022-09-06 16:05您已点过赞美国给我最愉快的就是能看到零元购等美丽的风景线,和政客们整天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内心无比龌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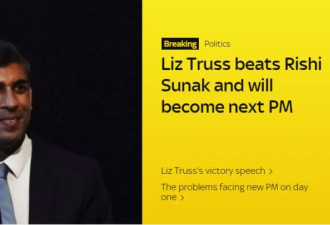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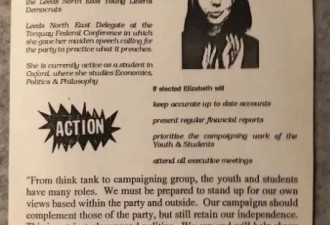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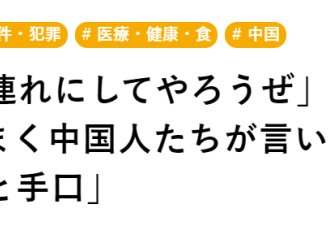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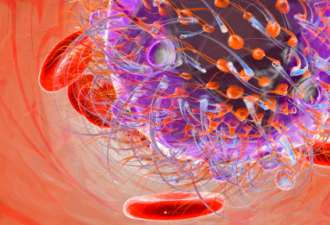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