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胡特: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解析
在洛杉矶当代精神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的分析师训练中,有一门选修课程叫做“社区精神分析”(community psychoanalysis),本质上就是精神分析和社会学联姻之产物。我们在上这门课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科胡特的社会心理学神作——《创造性,魅力,团体心理学:对弗洛伊德自我分析的反思》(Creativeness, Charisma, Group Psychology: Reflections on the Self-Analysis of Freud)这篇论文,其中有一节,名为《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读后回味甚久,遂对这一节做即兴翻译,并与诸君分享:
(以下小标题为译者所取)
1. 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
那么,当具备一定创造力的普通民众,在自己人生的某个阶段极为需要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格,尤其会被他们敬拜为全能的自体客体呢?

我认为,某些自恋型(甚至某些带有偏执特征的自恋型)人格尤其适合这个角色——这些自恋型人格,他们看上去坚如磐石的自信,他们带着某种绝对正确性的观点——在普通民众暂时性的“自体虚弱”(enfeebled self)阶段,尤其适合充当他们的理想化客体,从而满足人们的理想化需要。
这些自恋型人格,一般很少来找精神分析师,从而把他们自己放到精神分析的显微镜下去展示。因为他们拒绝体验虚弱,他们的自尊心极强。他们之所以在需要他们的民众那里,尤其适合扮演被理想化的原始客体角色,是因为他们的自尊是由某种几乎从不间断的心理功能所维系:他们会持续性地评价别人——他们会不断地指出他人人格或行为中的道德缺陷——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丝毫没有羞愧和犹豫。
他们会把自己设定为“向导”、“领袖”以及“神”一般的人物,从而满足人们需要方向,需要被领导,甚至人们对信仰的需要。我们把这种特殊的自恋型人格称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救世主型”(messianic)人格。这两种人格会完完全全地以自己的夸大自体(grandiose self)和理想化的超我(idealized superego)自居。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我们的自体理想(ideals),是一种可以为我们的生活设定方向的完美象征物。当我们接近“自体理想”为我们设定的目标时,我们会体验到一种自恋性的愉悦;当我们离“自体理想”设定的目标距离太远时,我们会体验到一种自恋性挫败。但是,救世主型人格却与此不同——他们已然放弃了用超我的理想来评定自己:在他们的人格系统中,自体和自体理想已经合为一体!
当然,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他们用以维持自尊的这种人格结构,会让他们的性格严重缺乏弹性。从心理健康的长远角度来看,一个人灵活地使用不同的心理功能来维系自己的自尊,总比靠单一地使用评价和发号施令来维持自身僵化的自恋,要来得更加安全。要知道,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的心理平衡,似乎来自于一套“全或无”(all-or-nothing)的逻辑:他们感到要么就要全然坚定,全然有力——要么就是全然躺平或全然毁灭。
但是,我在此仍然要强调,在反思魅力型和救世主型领袖人格时,心理动力学家们切不可过快地抛却中立立场,且过速地做出道德判断。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强度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中某些人的心理状态已接近精神病水平,这毫无疑问。这些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为专断,另一个特点就是对别人的内心世界完全没有共情力——但是,当他们要“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自恋需要时,又能够准确地把捉别人身上哪怕最细微的反应差异。
而且我们需要看到,有一些救世主型人格,他们自体和理想化超我(即自体理想)之间的融合历时虽久,但是这种融合只是部分融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身上的救世主部分和非救世主部分虽能够彼此自洽,但毕竟他们身上的非救世主部分,会让他们不时展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嘲能力(但不是认错的能力)。
另外,我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都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两种类型的自恋人士,在遭遇到严重危机的时代,是会被强烈推崇的。在这种危机之下,谦逊而给人留有余地的人格类型,通常没法胜任领袖位置。
在强烈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中,一个国家会把目光齐刷刷地指向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不光是因为这两种人格有现实手腕和效率;更因为他们身上那种不可置疑的正确性,坚定性和给人带来的确信感,可以满足普罗大众在危机时期的理想化需要,并降低他们的焦虑。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以佐证: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丘吉尔与英国人民在战前、战时以及战后的关系,可以很好的佐证英国民众(包括整个西方世界)在自己面对最大的生存危机(二战)面前所作出的选择。丘吉尔,他所展现出的传奇人格魅力,我相信更多地是来自于其人格中的夸大自体部分,而非理想化超我部分。丘吉尔在战前是不被民众所接受的,但是他在战时的危机之中,却完美地担当了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领袖角色。

英国人民在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在内心中普遍认同了丘吉尔毫不动摇的必胜信念,并进一步透过他认同了自己国家的力量,这种对魅力型领袖的心理认同,帮助人们强化了他们受到削弱的自体,助他们度过了危机。但是在战争胜利结束以后,人们与全能客体的心理融合需要很自然地消退,于是他们很快又选择了其他的非魅力型领袖来代替丘吉尔。
从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普通民众虚弱的自体需要,和国家在面临危机时的群体需要之间的平行关系。在自体虚弱时,或群体面临危机时,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会对将领袖大大地理想化,并对其产生自恋性移情(narcissistic transference,即感觉自己与其产生心理融合)。在危机度过,或者自体得到强化以后,这种移情就会结束。
与救世主型和魅力型人格的人格特征比起来,心理健康处在平均水平普通人,其自我(ego)主要是要实现两大任务。
一、普通人的自我,要应对处于人格深层的夸大自体(grandiose self)释放的压力。也就是说,一个人人格中的夸大自体是有野心有抱负(ambiions)的,这就要求一个人的自我(ego)去帮助实现这些野心和抱负——以一种现实的方式。一个人若要以现实的方式实现自己全能自体的抱负,就不可避免地——会顾及和自己有共情性连结(empathic contact)的——他人的需要和感受。
二、第二个任务,普通人的自我,会在超我(superego)的理想化标准的驱策下,通过施展主动性和控制力,从而让自己的行为接近理想化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会把现实自体和超我标准进行比较,并且承认“心中的完美,和现实总会有些差距”——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在普通人那里,他/她因现实自体和超我理想的靠拢,而获得的自恋性愉悦感总是有限的。也正因为这种有限性,使得普通人在与自己有共情性连结的他人交往时,不会发展出一种绝对的道德和价值上的优越感。在把自己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进行比较时,非救世主型的普通人,会被一种对他人的共情性理解所影响——明白别人和自己一样,无论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成败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不会认为自己的自体纯然完美,而别人的自体绝对腐败。
2. 人格形成原因分析: 弗洛伊德和科胡特
弗洛伊德
那么现在我就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魅力型人格得以维持自己的力量感,就好像他们的真实自体(real self)和原始夸大自体(archaic grandiose self)合二为一一样;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救世主型人格得以保持自己在道德上的绝对正确性,就好像他们的真实自体和超我理想合二为一一样?要知道正是这种谜一般的自我正确感,伟大光荣感,吸引着普通人与他们进行心理融合和崇拜。
他们中的某些人,似乎属于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篇不太相关的文章(1916a,pp. 311-315)中,所描述的那一类型——他把这些人称为“免责人士”(”the exceptions”)。弗洛伊德认为,某些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对别人做了什么无情或不道德的事情,都会在心里给自己自行免责。之所以可以免责,是因为这些人在小时候就遭遇到了不公平的惩罚——因此这些儿时的不公,就成了他们日后对别人无情的“免责铁卷”。

科胡特
在我自己的临床经验中,我也会试着观察这些病人(虽然他们人数并不多),那么现在我也尝试着,提出自己对他们人格形成原因的理解。
我在临床中观察到的这些病人,几乎不会产生有效的内疚感,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几乎不会产生良心上的谴责。但是,他们会对任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现象非常敏感,而且不公平发生以后他们会快速地控诉他人——他们的控诉通常非常具有说服力——因此总能够引发别人的内疚感,而这种在别人身上引发的内疚,通常会使得这些“别人”臣服于他,并且允许他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不认为这些人仅仅只是仗着自己童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来为自己的恶行免责。他们当下行为背后最重要的动力学特征——是一种对他人共情能力的极度缺失:他们既不能理解他人的渴求和愿望,亦不能理解别人的挫败和失望。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自己的渴求,对于自己的挫败的敏感度又极高。
我对他们人格特征形成之理解如下:
这些人在早年经历过严重的自恋损伤(narcissistic injury),其损伤主要来自于其镜映型自体客体(mirroring selfobject)和理想化自体客体(idealizing selfobject)所提供的共情性回应极不稳固,或者不可被预测。
更具体一点:一个孩子可以通过镜映型的自体客体回应(如母亲共情性的、骄傲的笑容),不断积累起自信;也可以在与全能的理想化自体客体身体融合的过程中(如被父亲共情性的——抱起或举高)不断积累起安全感,但是在这些病人的童年时代,他们和这些自体客体的关系通常遭遇到了突然的、不可被预知的打断。
在这种中断性创伤发生以后,这个孩子逐渐内化、整合镜映型及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发展进程也就被打断了——而这个孩子,在新的,非共情性的恶劣环境中要生存下来,就必须靠着某种强大的先天禀赋来维系自己业已破碎的自尊(self-esteem)——他需要用这种带着股狠劲的高自尊来救自己——表现得就好像自己的原始自体客体还在自己身边一样。
因此,当我们在接触这些人的时候,会发现童年的不公平遭遇其实并没有在现实中替他们免罪——实际上他们在心理层面上,根本就没有生活在受到各种外在规则,和内疚感制约的现实世界中——其实,他们当下真正体验到的那个世界,仍旧是那个原始的世界(archaic world)——那个终极自恋性损伤——始发的世界。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对他而言,那是一个他一开始能体验到的欢乐和安全感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把这些欢乐和安全感凭空夺走——就好像在逗他玩(tease)一样。为了应对这个创伤,他变得对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超级共情(superempapathic),并且对那个把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自体客体(如父母)夺走的世界变得异常愤怒——他开始自认为总是正确,表现得就好像被夺走的自体客体,依然在肯定他一样;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完美,并且开始试图全然地控制他人,通过控制他人来调节自己的自尊——能够全然控制时自己的自尊就高,不能全然控制则低,根本不把别人当做有自己权利的,独立的人来看待。;
换句话来说,之前他所遭遇的不公,是突然撤走了他用以维持自身健康自恋的自体客体;那么在他的内心中,这个世界就应该加倍偿还他,尽力满足他现在的一切自恋性需求。

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很多都是具备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两种特质的复合型病人,所以我接下来要进行的分类,可能会有过度细分之嫌疑:那些主要呈现出魅力型力量(charismatic strength)和自我确认感(self-certainty)的魅力型人格——他们通常会伴随着自以为是的自我怜悯,而且会有疑病症状——他们的创伤主要来自于童年时代镜映型自体客体(包括但不限于母亲)的情感撤离;那些救世主型人格特质的形成,则主要来自于对原始理想化自体客体(包括但不限于父亲)情感撤离的巨大失望。
结语:
在之后的论文小节中,科胡特选用了希特勒,和一位名叫Daniel Gottlob Moritz Schreber的德国cult领袖作为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行文仍旧十分精彩,但我已无时间翻译,期待各位自行阅读,和这篇神作各自相遇。
自体心理学用共情方法,进行参与性观察研究,几乎不会站在局外综述理论,实则都是病人主观经验的汇总,和稍加的概念化提炼。
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一时半会看不出这种观察的优势和特点,期待以后多写一点以内部观察为基础的文字,替苍生说人话。
诸君新年愉快,平安顺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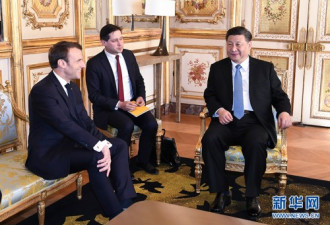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