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润出祖国,在戴高乐机场一呆就是18年




“你说你一直在等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2004年的电影《The Terminal》中,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男主角维克多如此对女主角说。这部感动全球影迷的作品取材自原型人物、曾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生活18年的伊朗男子纳瑟里(Mehran Karimi Nasseri)。今年11月12日,戴高乐机场发言人证实纳瑟里心脏病发作,并在警方及医疗团队紧急抢救之下仍宣告不治,享年76岁。曾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航站楼度过漫长岁月的纳瑟里,在最熟悉的地点结束了他孤独迷茫的一生。
《时光故事》油管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cherrytimestory

戴高乐机场航站楼里独特的旅客
电影《The Terminal》剧情中,男主角维克多的家乡、电影虚构的国家“克拉科齐亚”在他前往美国途中发生政变,他的护照和银行卡都失效了。他无法入境美国、也无法回家,无奈之下,他只能在肯尼迪机场航站楼等待。而这一等,就是9个月。期间,他还邂逅了一位美丽空姐,并对她一见钟情。不过,真实故事远比电影残酷。纳瑟里在机场住了整整18年,既没有遇见空姐的青睐,人生也没有重回正轨,最终独孤离去。
从1988年到2006年,他一直住在机场,成为这里的独特风景线,很多过境旅客会特地找他合影留念。
纳瑟里去世后,机场发言人说,他是机场的“标志性人物”,“整个机场社区都很喜欢他,我们的工作人员多年来尽可能地照顾他,尽管我们更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真正的避难所。”
虽然被困在机场,可纳瑟里依旧保持着体面的生活,衣服永远干净整齐,胡子、头发和指甲从来没有不修边幅的时候。他坚持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用机场赠送的免费牙膏刷牙,同时把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不影响机场秩序。
白天,他会阅读杂志和报纸消磨时间,还会写日记、学习经济学知识。闲暇时分,就在航站楼白色瓷砖地板上走来走去。
晚上,他则等机场商店打烊后,再去卫生间洗衣服,洗完后挂在手提箱把手上,接着拿出枕头、床单、被子,睡在机场红色的长椅上。
多年来,他靠陌生人的善意生存,机场工作人员会给他餐券和法郎,附近餐厅也很照顾他。他早餐经常吃快餐店的鸡蛋和培根羊角面包,晚餐吃鱼三明治。
他的东西不多,6个航空公司的货箱、磨破皮的手提箱和塑料袋就是他的全部财产。里面有一对闹钟、一个电动剃须刀、一面手镜以及一系列剪报和照片,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和信件,以及他的衣服。
在机场待久了,工作人员都认识了他,尽其所能帮助他,朝夕相处下似乎也产生了家人般的情谊。甚至有乘客慕名而来专门来看他。有人想送他食物、衣物,可他都拒绝了,并告诉对方“我不是乞丐”。
他出名后,先是一些当地媒体来采访他。后来,一些更有影响力的制作单位也注意到了他的故事。2000年,导演Alexis Kouros制作了一部关于倒梅君的纪录片——《在戴高乐机场等待戈多》。
2004年,他和英国作家安德鲁·唐金合作写了一本自传《终结者》,在书中,他讲述了自己作为“政治难民、囚犯、放逐者、反叛者、绅士、世界公民、媒体宠儿最主要的是延误乘客的种种身份以及独特、非凡的人生故事。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价为“令人深感不安和才华横溢”。直到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把他的经历搬上了大银幕。


滞留机场,一朝成名
1988年8月,纳瑟里在去往戴高乐机场的途中,丢失了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
他是合法入境的,法国政府不能把他驱逐出去。可因为他无法证明自己是谁,所以不能离开航站大楼,只能待在机场等候区。
电影《The Terminal》大火后,无数记者和摄影师来到戴高乐机场采访纳瑟里,他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一天最多接受过6次采访。
纳瑟里的身世扑朔迷离,对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描述。
纳瑟里1945年出生于伊朗库兹斯坦(Khuzestan),根据他本人自己的说法,是因为“1977年参加针对伊朗国王巴勒维的示威”而遭到伊朗当局驱逐,变成了政治难民。纳瑟里的另一个说法,则是“为了寻找母亲的旅程”,1988年11月,他从伊朗飞往伦敦、柏林及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因始终无法提供受认可的移民文件,都在机场被拒绝入境,最后,他来到法国,从此定居于法国戴高乐机场航站楼。
虽然纳瑟里于1999年取得正式难民身份,但直到2006年才因为就医需求离开机场。自1988年以来,纳瑟里都以“阿弗雷德”(Alfred)自称,他的朋友和机场工作人员也都这么称呼他,对他来说,戴高乐机场已成为他的家。
纳瑟里谈到自己的身世时,有时会给出前后不一的答案。美国伊朗籍艺术家哈米德·拉马尼安(Hamid Rahmanian)曾于2000年到戴高乐机场访问纳瑟里。纳瑟里有时表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妈妈则是一位英国籍护士,也曾拒绝承认自己是伊朗人,并数次声称自己是美国人、加拿大人或比利时人。他曾告诉媒体,说联合国难民署一直在找寻他的父母,以证明他的难民身份,但发言人说这是无稽之谈。
官方资料显示他1945年出生于伊朗,可他又发誓说自己不是伊朗人,而是出生在瑞典的英国公民。他说自己因为参加反对伊朗国王的活动,而遭到流放,可有人研究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习惯了机场生活,不敢离开
起初,纳瑟里住在机场是迫不得已。后来,则是一种主动选择。1999年,他获得了留在法国的权利,对于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他却表示:“我不太确定我想做什么,留在机场还是离开。”有机场人员提到,“他就像一个在监狱里待了多年的囚犯被告知自由了,我不知道他在外面能不能活下来。”
在机场住久了,这里就像他的家一样,他不敢想象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就像桃花源中人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哪怕能回归正常生活,他还是放弃了。
不过,也有媒体猜测,纳瑟利之所以不肯离开,是因为被困十多年,长期的孤独生活让他的神智有些不清醒,心理上被戴高乐机场“收养”了。
机场尊重纳瑟里的个人选择,并尽量让他住得舒服一些。当时,机场所有红色塑胶椅都拿掉了,只有他睡觉的那张留了下来。机场神父和医生每周都会过来探望他,还有些员工有空时会找他聊天。

2006年夏天,纳瑟里病了。因为常年无法见到阳光,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头发日益稀疏,脸颊也凹陷下去。他被送进医院,18年来第一次离开机场。据BBC报道,纳瑟里离开机场后曾进出医院动手术,也使用支付的电影《The Terminal》版税支撑生活数年,之后住进法国无家者收容所中。根据华盛顿邮报,《梦工厂动画》(DreamWorks)也曾支付他数十万美元的电影版税。
2007年病好后,他由法国红十字会机场分部照顾,在机场附近的旅馆里度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一直住在巴黎郊区的一个慈善中心。
或许是预感到自己大限将尽,今年9月中旬,纳瑟里再次返回机场,没过几周就心脏病发作,去世时身上还有几千欧元。去世前几周,他总是静静地坐在同一个地方,张着嘴望向窗外,目光呆滞,看上去没什么精神。
电影《The Terminal》的知名度让纳瑟里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他也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国观众的明信片,他的手推车上收藏了自己被报道的杂志和报纸。长年关注他的身心状况的戴高乐机场首席医生Philippe Bargain认为,这样的关注对纳瑟里并没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发现纳瑟里对于这些关注“乐在其中”,可能让他对于自身处境更加自我合理化;另一方面则是对其身心状况造成更加退缩的影响。
根据医生多年观察,纳瑟里长年滞留于机场、缺少与外面接触的机会,因此常出现精神疲劳的症状,甚至害怕离开机场。
纳瑟里因《The Terminal》成为一位全球知名人物,但媒体记者结束访问、离开机场后,他的处境或许与其他政治难民没有差别。在旅客来来去去的机场里,孤独地寻找自己的身分认同。即使取得难民身分,他仍在生命最后关头回到戴高乐机场,直到离开人世。虽然没有人知道他最终回到机场的原因,但机场角落那张红色塑胶椅上是他最后出现的场所。在最后的时日中,他仍拒绝认定自己是伊朗人、也不愿被称呼本名“梅赫兰.纳瑟里”,而是“阿弗雷德”。
全世界都知道他,大家都来看他,但没人真的了解他。谁也说不清他这一生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在生命最后,他用独有的方式,抵达了《The Terminal》。
《时光故事》油管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cherrytime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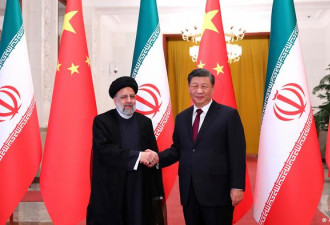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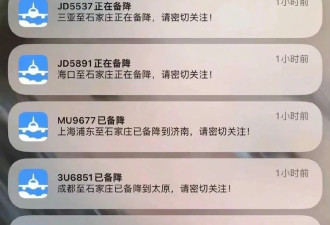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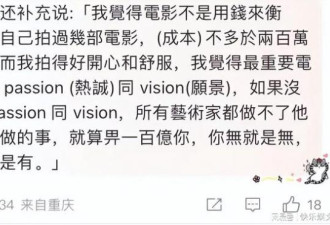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