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网店却被父母送进网戒中心电击

他不知道人生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连续一个月,周齐总是在半夜惊醒。他的手指无意识地颤抖,害怕睁眼就会看到五六个家长,套着白色T恤、黑色束脚裤,再普通不过的衣着,手里握着绑人的绳子,“我会不会再次被抓走?”
就像一个惊恐的孩子,但他已经37岁。2008年,周齐被父母送入临沂网戒中心,他只在里面待了四个月,但之后16年,在网戒中心的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遭受的每一次电击,都反复攫住了他——即使网戒中心早已关停,始作俑者杨永信销声匿迹,父母垂垂老矣,再没有压制他的力量和权力。他的人生由此分成了两半:那一天到来之前的日子,以及之后几乎摧毁一切的痛苦。
所有人的生活都一直向前,只有他被困在原地。一年前,他再次出现在网络上,作为网戒中心的受害者,他报警,联络其他受害者,希望能追究始作俑者的责任,他无法入眠超过四小时,醒来就打开手机,看看是否收到法院有关“起诉杨永信一案”的最新回复,他反复的希望又失望,“这个案究竟立不立呢?”
我在杭州见到了周齐。去年他与所有家人亲戚断联,独自住在郊区的农村,地图上找不到具体的点位,只能导航到附近的小超市,等他来接我。他穿了一身黑,身材瘦削,胡须茂密地攀上脸颊,透着一种长久不见光的憔悴。
我们走进他租住的农民房,靠门的地上摊着一副由几块长条铁架拼凑而成的床骨,上面铺着一床薄薄的褥子——这原本是网上购买的床架,在一条床腿崩坏之后,周齐直接拆掉了四个床腿,“就直接睡地上呗”。白色的瓷砖地面,满是分散的小黑点,他说,这是两天一条烟的后果,擦不干净。他向我展示了一包装盒打火机,粗略看过去还剩十多个,“拼多多上买的,一大盒就几块钱。”

周齐的床©廖宇彬
白墙已经脱了几层皮,碎渣随机掉落,靠窗户的一侧是书桌,摆着这个小屋里或许最值钱的东西,一台电脑。
来到杭州,最初周齐抱着重启人生的愿望。他先去食品厂应聘了装卸工,工作内容是把约100斤的糖叠起来,干了几天被辞了,“老板嫌我力气小”。后来打听租房中介,“没有底薪只有提成”,他直接走了。他还去了保健品公司应聘销售,很像传销,老板给电话号码,他负责加微信推销,听完要求他又离开了。现在周齐每月底还有网贷要还——App上的便捷借款,点一次到账一千,他好奇尽头在哪里,一直点到了15000。他不敢再点了。

周齐的出租屋©廖宇彬
所有的钱都花光之后,周齐开始学习给自己做饭,第一次炒菜时,油和火候没把控好,锅里冒出浓烟,房东惊吓地给他发消息,“后面着火了吗?”
我见到他时,周齐已经好几天没吃一口饭,饿了就喝水,再不济吃一片减肥药——在某网购平台花6元购入,他说效果显著。
周齐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他特别容易困,但很难入眠,有时一天睡个四五次,睡不着的时候,他常常哭泣,不知道人生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她忘记了发生的一切,
只有她的儿子留在了那里
周齐永远难忘第一次被电击的感觉,他被架上黑床,7个人按着身体,嘴里塞进一个木头做的筒状牙套,电极片一挪开,周齐对工作人员说:“你让我自杀吧。”而对方拿着电极片,“现在才电了20秒,还有3600秒。”
往后十六年,恐惧如附骨之疽,只要闭上双眼,他总能想起那双把在头上的手,贴在额间的电极片,电流穿过大脑时那片莹莹的蓝海。
临沂四院全名为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2006年成立“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杨永信担任主任,开启了13号室的电击疗法,他被许多家长奉为救世主。2009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推出《网瘾之戒》,提到网戒中心使用的电休克治疗仪,属于未合规仪器,最高三十多伏的电流通过人体,已是人体能承受的极限。在众多媒体舆论的质疑中,中心据说更换了合规电疗仪器,但从未停止收治“网瘾病人”。直到十年后,临沂市卫计委向新华社回应称,“网戒中心”于2016年8月取消,此后不再收治网瘾人员。

杨永信接受媒体采访
临沂网戒中心邀请家长24小时陪伴,名为“促进沟通”,如今可以想见其中规避风险的用意。周齐记得母亲林佩目送他进入13号室。第一次结束后,他出门直接给林佩跪下,母亲脸上有着惊叹的笑意。第二次,母亲提前买了饭,在门口等他一起吃,周齐试图从母亲眼里挖掘一点心疼,但他没有找到。
除了电击,周齐大多时间都在上课。课程围绕“孝”字设置,包括学习《孝经》、念书和实操并行。周齐在肚子里揣过东西,体验一天做母亲的感觉;也和母亲一起跑过两人三足的游戏;中心不允许父母随意打骂孩子,所有人都在歌颂父母的伟大。出院前三周,中心要求他睡前做两三百个“朝拜”,母亲在旁监督,做完头和膝盖都磕破了。有一次周齐下跪时哭得轻了,母亲举报他“感悟不深”,他又进了13号房。
为什么母亲在自己被电后总是笑?为什么她一点不心疼?后来许多年,周齐一直不能理解,他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直到我们相对而坐的此刻,他垂下头,双手无处安放,最后交叉护住自己的胃。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2021年,林佩罹患阿尔茨海默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丧失所有记忆,她忘记了网戒中心,忘记了发生的一切,只有她的儿子留在了那里。
我就是这么一条狗了
“那会儿我们着急,他老妈在电视上找到了这个临沂的中心,我就打电话去问,儿子爱玩游戏,每天就看电脑,还会打人,你们中心能不能戒?对方说行,那里都是这批人,几个疗程就能戒掉。我问他们有什么办法,他只说有办法,我们又实在没办法管得了他,能出点钱治好,人回到正常的轨道就行,对不对?”
我辗转联系到周齐的父亲周才林。他们一家是浙江余姚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普遍去外地谋生,村里人都做汽车配件生意,周才林和林佩在成都,周齐从小都由爷爷奶奶带大,只有假期时会接过去,但周才林给他的零花钱宽裕,读书也在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直到成都的生意不顺,一家人重聚在余姚的老家。周才林不太记得周齐小时候的事情,等他意识到事情超出了掌控,周齐已经长大了。
“小时候没管着他(周齐),才这样叛逆。”2006年周齐大专辍学,随后两年,周才林没怎么见儿子出过门,每天都待在房间里摆弄电脑,没份正经工作,周才林找遍亲戚朋友咨询,去过各大精神病院询问“儿子有没有心理疾病?”最后得到的答案都是“这一定有网瘾。”
夫妇两人为此想过各种方法,有激烈的也有荒唐的,比如他们带着周齐去求助神婆。早上四点,三人一起出发,神婆是一个普通的、五十多岁的女人,周才林急切地问,“他什么时候会听话不打游戏了?”神婆洒了一把香灰在白开水里,让周齐喝下,告诉他们,孩子慢慢就会好的。但孩子没有“好”,激烈的冲突于是无法避免,林佩曾闯进房间直接下跪,“我求求你不要再玩游戏了”;周才林喝完酒后,菜刀砍向电脑显示屏,裂了一条缝,他指着电脑说,“再玩断绝父子关系!”周齐直接搬出了家,没告诉任何人地址。
一个家庭的裂痕如此深重,似乎已经失去了相互理解的能力。对于周齐来说,他以一个留守儿童的身份长大,父亲不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事,那是因为他并不在场。从中学开始,他就饱受校园霸凌,他发育得比较慢,瘦瘦小小的个子,于是常常挨揍。上铺用指甲划破了他的脸,血珠渗出来,原因是厕所只有一个洗漱池,周齐刷牙时挤了他;他走路慢了点挡住路,同班同学把他推到了墙上,直接掐住他的脖子。所谓“网瘾”,不过是一个内向自卑的小孩见到了全新的世界,“至少游戏里的人不会欺负我。”
但父母不理解这些,他还记得有一次,他拿了10元去网吧,玩了两三小时后回家,父亲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再后来,晾衣杆也打断了好几根。
送他去网戒中心。在当时,这大概是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决定,不过几个月而已,无人能想象它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一生。

©视觉中国
“他父母给我打电话,说周齐网瘾严重,托我叫他来山东,他们再找个理由去临沂,我那会儿哪知道网戒中心什么样?周齐在网络这块儿比我们脑子都好,很早就能赚钱,但可能父母眼里他每天只会玩电脑。我想着去中心待个两三天也无所谓,是不是?人家父母从小认识我,又拜托我了,我不可能拒绝呀?我就喊周齐来看我,没想到关了四个月。”
王磊是周齐三十多年的好友,当年也是他将周齐骗了过去。我通过电话联系上王磊,当年按照周齐父母的嘱咐打完电话后,他并不知道后续,只是过了几天突然接到电话,周齐打来的,“和我说他在网戒中心被电了,很疼。”
他曾去中心看望过周齐,刚踏进门,就看到几个小孩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父母的腿痛哭,“我脑子一懵,不会是找演员来给我们看的吧?”他困惑地看着小孩们撕心裂肺,家长们涕泗横流。王磊看见了混在人群中的周齐,周齐也看到他,眼神闪烁着一点惊讶和迟疑,快速转过头去,王磊意识到,“他不敢过来。”探望结束,王磊再次联系上周齐,是两年之后的事情。
后来他们还是好朋友,周齐没有怪过他,“那个时候他也就二十岁,我父母叫他喊我过去,那时谁不听父母的话呢?”
出来之后,周齐感觉自己脖子上拴了条链子,“我就是这么一条狗了。”早上七八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给父母捏肩按脚,中心有过规定,如果没有遵循中心的生活模式,家长随时能再送他们进去。如果是“二偏”,待遇将完全不同,周齐见过太多反复被父母送进中心的人,同期最高有11次记录,他们很好识别,只能靠墙以军姿站立听课,有时连站四五个小时,有的几乎每天都要被电,饭菜只有白菜豆腐。
在周才林的眼里,儿子从网戒中心出来之后,终于有点正常人的样子了。
我很好奇地问周才林,“他哪里变好了?”周才林没什么犹豫,“最起码出来后跟你说话了啊,也能沟通了。原来话都不说一句的。不过只听话了一年,后面又对着干,就被虚拟世界腐化了,但好歹能生活。”
“你有想过再把他送进去吗?”周齐说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周才林对此感到不解,“他从中心出来已经变好了,还送进去干嘛?又要陪又要钱,有必要吗?”至于那些“送回去”的威胁,“大概就是吓吓他吧,没这个想法。”
我觉得自己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网戒中心把周齐塑造成一个“温驯”的人,但水面之下隐藏着一座火山,常常突然爆发。从中心出来后,周齐时常会体验到这种失控感,他似乎没办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朋友偶尔回消息慢了一点,他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觉得被冒犯了;刷到某个人的朋友圈,他觉得在内涵自己,私信质问对方,发完脾气又会迅速后悔。
面对父母,他常常在恐惧和愤怒的两极间切换。他能一瞬间变得亢奋、暴躁,伤人的脏话脱口而出。周齐有一个小他十五岁的妹妹,不同于在老家留守,妹妹周满从小和父母在成都生活,他们的关系远为融洽。周满记得从网戒中心出来后,哥哥喜怒无常的样子,正常的时候能跟她开开玩笑,脾气上来就扯她的头发。吃饭的时候她最害怕哥哥突然摔碗,拿筷子指着父亲,前者一米八的个头,后者只有一米六,她担心动起手来父亲打不过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周齐有着自己发火的限度,他不敢摔门后离家出走或拒绝联系,“那肯定会把我送回中心。”
2018年,外公去世。周满说哥哥在葬礼上迟到,父母不断打电话才来,结束后在车上他们又吵起来,她帮父母说了两句,周齐狠狠扇了她一巴掌,她的脸颊迅速红肿,她愣住了。
而在周齐的记忆里,那只是又一次失控:回家的路上,母亲说,“周齐你这样子不行啊,要不去工地里搬砖,给别人打工都行?”听到这句话时,正值夏日,他却浑身冒冷汗,头脑开始发晕,仿佛又被扔回刚从网戒中心出来的那两年,他已经三十一了,直接哭了出来,“我觉得自己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十年前,所谓沉迷“网瘾”的时候,周齐其实已经摸索出了赚钱的路径——贩卖游戏点卡。08年时,这是个暴利行业。他开了网店,做了几个月,就能赚一两万。从网戒中心出来后,这成了昨日泡影,他听从父母有个正经工作的意见,陆续打了几份工。比如在卖水暖的店里送货上门,把下水管道搬运到客户家;他去过工厂做速控拧螺丝;他还自己找了份商场的女装销售。
世界缩小到只有父母,他不联系朋友,同学聚会也直接拒绝,“没钱,也不像人样啊。”直到街上偶遇之前跟他一起做淘宝的朋友,对方面露惊讶,“你这一年多哪儿去了?我淘宝赚疯了,得有百万了。”周齐勉强地笑笑,网戒中心他说不出口,“但我真的不甘心。”
烟酒成了麻醉剂。刚出来的两三年,他维持着烟酒不沾的状态,“抽烟是我的罪状,被电过手的。”但后来,两天抽一条,吸一口烟过肺,那种飘飘然的气味顺着喉咙呼出,“就不用再思考了。”他一个人喝酒,目的只有喝醉。劲酒能喝两三瓶,黄酒喝一斤,一天没喝他就难受。抱着几个酒瓶,坐在电脑前,酒就往喉咙里灌,也不尝什么味儿。
“有次我去吃饭,一个路过的服务员都劝我少抽点对身体不好,为什么我的父母从没对我这么说过一句?”
其实离开网戒中心的前几年,他的生活在慢慢重回轨道,一切似乎都在好转,他重开了网店,赚了钱,还能贴补生意不顺的父母(但周才林说没有这回事),他谈了女朋友,买了车还要买房,他已经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忙起来的时候,也会有种错觉,觉得自己就快忘记网戒中心的四个月。

周齐发贴讲述经历
他和前女友打算买房,一个三十多平的单身公寓。母亲和前女友一起去看房,他没去,“我那个时候总觉得,很多事情比如买房,要经过我父母同意的。”但母亲不满意,“这房子不能买啊,太小了,住着多没面子。”回来之后,女友和周齐大吵一架,一周之后,她提了分手,“你多大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听父母的话?”
但后来,周齐还是听从母亲的想法,买了大房子。
从葬礼回去后,周齐在房里躺了三天,没吃一点东西,只喝了几口水,大脑里有种中暑的感觉,特别疼,又特别恨,他感到所有情绪好像终于到了头,无法忍耐又无从诉说,回到最熟悉的互联网,他想写下过去这十年的痛苦,“网戒中心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这种恐惧一直笼罩着我,不敢对自己的爸妈说不,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一切都直转而下了,网店生意从大不如前到入不敷出,他撑不住还贷的压力,又卖掉了房子。还完所有贷款之后,还剩五十多万,他彻底放弃工作和生活,一年之内钱全花光。那些钱究竟怎样花掉的?他说不出来,只是语气有点激动,“你觉得我那时候精神不好能做出什么理智的事吗?”
恨也好,不恨也好,时间都过去了
去年5月,豫章书院案公开一审宣判(编者注:2013-2017年,民办教育机构豫章书院以戒“网瘾”为名,对未成年学员进行非法囚禁、严重体罚,暴力训练。2019年,经学员报警,豫章书院创始人吴军豹等人被批捕。),被告人吴军豹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禁止从事教育相关职业五年。看到判决结果,周齐又感觉重燃希望,他恨杨永信,如果没有杨永信的存在,他认为自己早就能离开父母,“杨永信害了更多人,难道不可以判吗?”他去杭州报警,对方告知要去临沂本地才行。周齐先尝试网络报警,当地公安分局让他联系卫生监管所,他将答复公布在网络上,一小时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联系他,“欢迎你来线下报案。”周齐很高兴,删掉了在所有平台发布的信息。
他鼓足勇气,在朋友的陪同下,前往临沂育才路派出所,做了2次笔录。此后的一年多他没能收到任何回复。周齐也打电话问过,对方告诉他正在调查,在家里等消息就行。
他也想寻找当年的受害者共同发声,在网上发帖后,他收到了一些私信,有一位许诺他,如果能立案能打官司,他就加入。另一位对周齐感到不可思议,“他告诉我不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把中心拉下来”。还有一位似乎从过去完全走出来,已经结婚生子,过上所谓正常人的生活,“他劝我放下执念,可我有正常生活吗?”周齐很愤恨,“父母和杨永信把我的生活毁了”,他无法起诉父母,唯一能对准的只有杨永信,“如果没有他,父母就没有这个工具来控制我。”
比起案件有什么判决的补偿,“我只想要一个结果,是对前面三十多年人生的交代。”但由于时间过去太久、证据链条模糊,立案成为一件困难事。他没钱请律师,自己琢磨在网上申请立案,第一次被驳回是没交起诉状,第二次是起诉状格式不对,文件大小不够,第三次是法官驳回——他走的民事通道,但这算刑事案件,要走刑事通道。

©周齐
他也咨询过一些律师,对方都会问他:“有没有留下当时电击的照片或视频呢?”周齐感觉莫名其妙,“你说奇不奇怪?当时做这些事时会允许留下视频吗?”
周齐很后悔,如果在2018年全网关注时,他勇敢一点,选择去起诉,现在的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周满最近知晓哥哥准备起诉,作为家人她支持维权,这是一件正义的事,“只是我希望他能把矛头对准杨永信,不要杜撰莫须有的事抹黑父母、引导网暴。”
而从法律维度,“时间长,取证难,我觉得胜诉希望不大。”
她无法理解哥哥的冷酷,母亲患阿尔兹海默症住院期间,她在期末考试周,拜托周齐去看护,“照顾期间他一直说要走,一周多后留下‘找个护工吧’就离开,找我妈要护工费,给我发消息抱怨父母。”周满忍无可忍,他们吵了一架,关系自此彻底恶化。
她常常觉得自己非常割裂,一方面想理解哥哥的处境和遭遇,但又无法接受他对父母的咒骂与怨恨。她问周齐,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要把所有失败归咎于父母?为什么始终沉溺于过去不能向前看?周齐发来一串辱骂,把她拉黑了。
周才林并不知晓这件事。他现在开着一家生物燃料的小厂,早上七点出门,中午给工人烧饭,晚上七点回家,同时肩负照顾妻子的责任,周齐的“不务正业”已经成为全家人的心病,林佩即使失去大部分记忆,仍然在见到他时念叨着“没结婚没工作不成器”。周才林只希望周齐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他对儿子的期待没变过,一直都是找个安稳踏实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但从前年开始儿子持续向他要钱,“我知道他生意不行了,房也卖了,我给他付水电房租,也买保险,不求他还挣什么,他来帮帮我工厂的班也行,但他不愿意的。”我向周齐求证,他有些激烈地反问,“他找我借了那么多,我现在要回一点不很正常吗?”
去年周齐到杭州之后,找过周才林要钱付房租,最后一次他没给。后来周齐发了一长段话,“你们总是否定我……我工作生意最好的时候,你们折腾各种事…… 父母会对孩子这样吗?”周才林回了一句,“我们原来真是太溺爱你了。”他们彼此拉黑,再无联系。
“他现在生活不太好。”我尽量委婉,“你觉得他现在这样,是什么问题呢?”周才林没有犹豫,“网络里的虚拟世界啊。”
“周齐到现在仍然介意08年被送到网戒中心这件事,甚至非常恨,您有感觉到吗?”
电话里,周才林停顿了一下,“恨也好,不恨也好,时间都过去了,对不对?”他想了想告诉我,“如果当初没有送进去,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的。网戒中心即使有些方法(比如电击)可能不当,但总体的教育很不错。你看,人还是需要这种洗脑的地方,给大脑带来改变。”







![[集市好物]卫星接收设备, Satellite Dish/Recieve](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35445df1-b3d5-436e-8bc0-2cc888df526b.500x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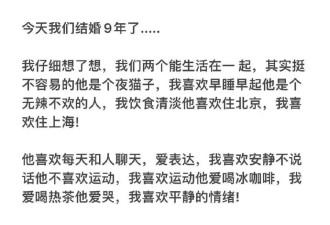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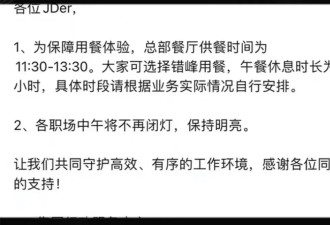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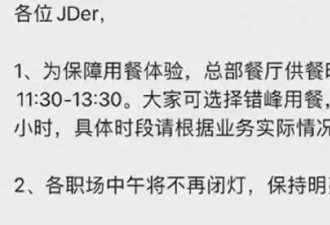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