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危机,曾促使我从体制中逃离
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我看过一些人在四十、五十岁的年龄从体制里出走,他们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彻底改变轨道。这个“体制”不仅仅是指公职,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主流式生活。他们辞职、离婚、移民、重新求学……决定去做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事。因为在生命走向衰老甚至死亡的时候,人总会升起一种紧迫的冲动——他们想真实地活着,他们想去真实的世界,因为他们想去寻找、实践真实的自我。

经济前景暗淡的年代,中国居高不下的考公考编热已成为时代景观。年轻人扎堆去卷体制内工作的原因众所周知——面对竞争激烈、收入缩水、工作难找、社会保障差的现实,只有体制才能提供一个安稳、可预期的“庇护所”。然而,如果这“庇护所”本身就是促成经济问题的因素,又怎么指望其中的人可以独善其身呢?
庞大编制带来的沉重负担
最近,公务员、事业编制“缩编”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也给想要赶上这股潮流的人亮起了红灯。中国广泛存在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编制沉冗、财政供养人员过剩的问题。为支付超比例的政府雇员的工资,地方政府常常面临入不敷出的压力,“借钱”发工资的消息屡见不鲜。沉重的供养负担使得本来就债务高企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无以为继。近几年,国家为了消化地方债务,正在推动一系列财政重整措施,其中一项要求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缩编”。
专家认为,中央对地方债务的介入有助于推动解决顽固的编制沉冗问题,却未必能够为年轻人的考公考编热降温。因为缩编只是意味着“铁饭碗”不再牢固,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体制内工作相对于体制外工作的优越性。”另外,由于大量的扩招,很多年轻人上的大学、学的专业质量堪忧,毕业后在社会上很难有就业机会。
“如果这些大学生在个人层面,在上大学期间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分,也未能掌握实用的技能或获得一定经验,或者一句话,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那么说实在的,用足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的优惠条件去争取考编“上岸”,在目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下仍然不失为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机会成本本来就不是太大。”
个体在有限条件下的选择固然无可厚非。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体制”为何成为了这样的怪物?它圈养着太多没有目标,只求安全的年轻人,不断再生产着他们的无能,荒废着他们的生命,最终自己也膨胀成一个危害全社会健康的肿瘤。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来说,体制的建构(以及参与其建构)都是一个作茧自缚的故事。要从这厚重的茧房里破茧而出,不经历脱胎换骨之痛,恐怕难以获得新生。
体制:当代中国的初始设定
我身边一些自由主义朋友有种很天真的想法,觉得随着国内经济越来越差,社会矛盾凸显,蔓延至身边的灾难变多,现在仍认同体制的人会“被教做人”,他们会被激起反抗,或者至少,有所醒悟。
现实正好相反。在中国的语境下,环境越差,权力对资源的垄断和分配能力就越占主导,个体的自主空间就越小。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就越需要依附权力去获取必要的保障。而这种“自主空间”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空间,精神空间也会缩小。也就是说,恐怕人们不仅不会“醒悟”,反而会更加认同体制。
疫情后的考公考编热多少已能佐证这一点。在笔者小时候,改革开放重启后的90年代,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解放思想”的号召,“下海”才成为全民热潮。
当然,不必嘲笑这些自由主义朋友,这些黄金时代的遗孤。他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们还保有自由的心智。他们总是相信人的能动性——如果遭到压迫,便要去冲撞桎梏,怎么能逆来顺受?所以他们是有能力脱离这片土地的人,不管是在精神还是肉身上。
人们常常把体制形容成“围城”,而体制所制造的“围城”是权力垄断资源的结果。
“改革开放前,中国还在计划经济的时期,中国人都属于特定的单位,并且专属于特定的单位,个人既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也没有独立的经济信用,就连消费也只能按照票证规定的数量和品种购买和分配。那种因为具有多样、不确定和灵活的属性而可以称为“社会”的空间微乎其微。”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教授如是说,他所在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当时参与其编纂的20多位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
现在的年轻人理所当然把改革开放当成中国的“初始设定”,但实际上,体制才是当代中国的初始设定。改革开放后,体制之外出现了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拥有了私人领域;而私人领域孕育了人的独立自主意识;自由人通过自由的联合组成“公民社会”——这些才是新进概念。
而这些新进概念已然“过时”。当国家力量无度扩张,资源分配过多地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那么国家自然会成为最大的剥削者,挤压市场和私人领域的利益,并试图控制社会和个人的方方面面。老百姓只有成为它的一份子,才有渠道分得一杯羹。体制要维持这种特权,自然需要推高其进入门槛,于是,国家每年都制造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奇观,从中遴选出一整个“特权阶级”。
当然,体制并不是中国特产,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有“体制”——政府的行政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大学、军队等系统也相对独立于市场和社会。它们依靠公共财政维持运作,很少受到市场的干预,资源也很少与社会流通。但区别是,这些体制背后的国家力量并不垄断社会资源,体制内的工作也不存在那么强的权力光环。所以体制对人们的吸引力有限,进入的门槛也并不高。毕竟在公权力之外,还有同样壮大的资本市场和公民社会,它们呈现三足鼎立的状态,便得以互相制衡和监督。一个离开了大学或军队的美国人同样面临重新适应社会的落差,但不至于在体制之外就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去生存、发展。
近些年,将自己的痛苦境遇归因于“万恶资本家”的年轻人,或许不能算错。毕竟国家控制的资本也算是资本,党的权贵阶层也会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本家。不是说民营企业家就不会“作恶”,而是应该质问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法律、劳工权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无力应对资本带来的问题,而谁又是能够免于监督的?另外,很多极左或极右的人都缺乏一种分析“语境”的智慧——事物的性质要看其关系、看其比例。权力的问题往往不在于自身的好坏,而在于互相的平衡和制衡。当国家机器的权力过大,资本必然与其苟合,孱弱的民众只能沦为二者收割的韭菜。
对于曾经改革开放盛期的中国来说,去区分体制内外是有意义的,但一个极权化的国家其实不存在体制外的空间。不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企才叫体制,如今的中国就是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巨大“体制”。因为整个社会已经被国家机器牢牢困住,越发没有自主的空间——独立NGO、独立新闻媒体、民间组织、集会等都难以生存,甚至每个人都难以捍卫自己的私人领域和身心自主界限。
当这个体制承诺为社会提供依靠和庇护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正是这个体制给社会造成了困境,也正是它与资本主义的暗面同流合污。
所谓的“上岸”其实会把人溺死
普通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很难找到出路。人们总把考进体制称为“上岸”,仿佛暗示了一劳永逸的解脱和“从此以后”的幸福生活。然而,体制内却又是另一场无望的煎熬,抱怨体制内的工作令人压抑和麻木、令人感觉“浪费生命”的声音同样尖锐。
纵观那些从体制辞职之人的自述,他们最常提到的问题包括:行政化、政治化、官僚化过于严重,和专业无关的事务太多;人变成了螺丝钉,唯领导是从,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和能力;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工作,找不到成就感和意义;低效、平庸的氛围,做多做少都一样,没有发展空间;在体制里也并不轻松,做事不自由又无法掌控自己的时间……
体制内的人需要承受体制的问题,特别是当体制和人——和人的性格、理智、价值观、道德直觉等特质相矛盾的时候,尤其令人痛苦。
一位曾经在上海某大学当老师的作者乔葭兰记录了他教书十年后的辞职经历,这篇文章火爆全网却又被很快封杀。作者称其教学和学术自由受到了太多政治干预,学生也因为大环境的影响而变得急功近利、无法容忍异议。好不容易遇到个别热情求知的学生来面试,却被学校领导歧视、拒之门外。
“近年高校思想控制更深入,每门课大纲和教案重改,必须加入三个以上思政知识点,让人反感,后来发展到为节课都要有思政内容,‘课程思政’由前几年的个别老师申请项目拿经费,发展到百分之百覆盖,每位老师都要把自己的课跟思政联结。
去年有一次课间,突然后门进来一位教务督导老师落座来巡查听课,课下走到讲台与我交谈,问怎么没听到思想政治的内容,我糊弄说您来前刚刚讲过,当时我班上的前几排学生马上应和,帮我糊弄搭腔,心照不宣,相视而笑。”
我对他的经历很有共鸣。因为我曾经也在家乡当大学老师,教建筑设计,后来下定决心辞职出国读书,从此一去不回头。当时学校的政治化并未那么严重,但行政凌驾于教学乃是常态。
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对教学抱有极大热情,因为发现班上的学生普遍基础不好,我和另一个搭课的老师就利用课余时间,费尽心思为他们制定补充教学和练习内容,学生的反响非常好,一些有天赋的孩子进步神速。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因为教授“超出课程大纲”的内容而被另一个班的学生和老师举报到学校,课程被叫停,我们甚至被调查和约谈。
后来,我发现老师连一些基本的自主权都被干涉,比如说给不合格的学生挂科,副院长会打电话来劝:“不要挂太多,分数要给高一点,否则学生成绩不好看,也影响我们系将来过评估。”末了还加上一句:“这也是为了保护你们老师。”有时就连一个普通辅导员,都可以打电话来要求给关系好的学生改分。而那些懂得配合领导的议程,却不管学生的老师,获得了最多的赏识。
但平心而论,比起高校稳定、悠闲的工作氛围,这些小烦恼都不算什么,我很快就习惯了得过且过,也变成了一个会划水、敷衍了事的人。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深陷进怠惰的泥沼里无法自拔。我年纪轻轻就停止了成长,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我陷入了一种慢性的抑郁状态中,日复一日,对未来感到绝望。
让我最困惑的就是,为什么我明明过得非常痛苦,周围的人却还都说好,羡慕我拥有编制和全民默认的“女性最佳职业”,父母也为我的“完美到站”而心满意足。一开始,我也告诫自己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后来,我怀疑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这就是中国中产们从小为孩子所构建的“幸福生活”?简直可笑。
我尝试了各种“自救”,读书、健身、写作、养猫养狗、背包旅行……但这些活动都未能安抚我的焦虑、将我重新激活。我觉悟到,如果我还想继续停留在安全区里,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只敢通过消费去获取消遣,所谓的“自我提升”就是自欺欺人而已。
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我看过一些人在四十、五十岁的年龄从体制里出走,他们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彻底改变轨道。这个“体制”不仅仅是指公职,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主流式生活。他们辞职、离婚、移民、重新求学……决定去做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事。因为在生命走向衰老甚至死亡的时候,人总会升起一种紧迫的冲动——他们想真实地活着,他们想去真实的世界,因为他们想去寻找、实践真实的自我。
只是,当人生已过去大半,出走的成本也变得过大。我很幸运,在三十出头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冲动,并选择相信自己的感受。我听不进所有人的规劝,甚至和爸妈大吵一架,也非离开不可。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任性,但对于我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决定。
家庭往往就是体制的前线
七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离开时的心情仍记忆犹新。如今我已习惯了加拿大的生活,交到一些如家人般的朋友,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生,再也比不上我曾在国内拥有过的一切,但却是我拼尽全力获得的。
在这段旅程中,我曾经意气风发,而后颠沛流离,也有过跌入谷底的时期,历经打击之后再也不复年少轻狂。但回过头看,它堪称一段非凡的英雄之旅,我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和他们带给我的启发,都是曾经身在体制里的自己无法想象的。这一切都让我认识了我,并最终成为了我。我生命中珍贵的东西,也在这个过程里水落石出。
正因为亲自走过了一遭,我更明白要成功脱离体制,以及脱离被体制化的生活是多么困难。要应对自由所伴随的巨大不确定性,除了自身不懈的挣扎,还有赖于很多“特权”和运气。我的父母虽然一开始不同意我的选择,后续却给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在我每次失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借机奚落,也从不旧事重提,只是鼓励我重振旗鼓,去做下一次尝试。但我也不会忘记,是我的“固执己见”重启了人生,我为我当初没有交出自己而骄傲。当我上路的时候,他们因着对我的爱,也不得不随着我学习、成长、调整心态和眼界,然后才渐渐和我走到了一起。
如前所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体制,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老中”,远在我们想要考公考编之前,远在我们进入社会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被体制规训。国家与家庭的一以贯之,意味着家庭往往就是规训的前线。如果父母对体制缺乏反思,那么这些规训都将以亲缘为渠道,以爱为名行之,其效果也超过国家机器。
说到家庭的规训,王路的文章《也值一个屁》令我印象深刻,他讲了自己热爱体育的外甥被迫去考大学,结果考砸的故事。由此指出,中国父母总是传递给孩子一种“输不起”的观念,于是孩子的失败都只能用来证明父母的正确、树立父母的权威。
“这是亲情的胁迫。哪怕是以最不动声色的方式。我见过太多像外甥这样的小孩,如果要学体育、艺术,或者什么,家长会是这样的态度:你非要学,我们也不拦着,家里就是再困难,也要供你,但是有一点,你得好好学,给家里争气。既然给了你机会,你又学不好,以后就啥也别说了。家里安排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输不起’的观念就会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点一点浸透到孩子的少年和整个青春期。越是听话的孩子,越难以承受这种道德和亲情的双重压力。把老老实实按部就班按照家长和老师的安排走下来的人,变成一个充满内疚和负罪感的人。”——当权者剥夺了你自主的信心和对自我的信任,你才会心甘情愿把自己的主导权交给他,让他代替你做判断,因为你相信他比你更清楚,什么对于你来说是好的。
不容忍犯错是一种极权控制。事实上,人人都在犯错,并通过犯错学习,犯错正是一个人校准方向、去伪存真的途径。当社会的容错率太低,个体的试错成本太高,太多人对“走弯路”唯恐避之不及。结果半生过去,连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都不知道,恰恰走入了人生最大的歧路。
你真的脱离了体制吗?
最近给我最大震撼的是三明治的一篇非虚构故事《后悔从体制内辞职,38岁的我重新准备考回去》,作者元琪是一个在社区做社工的女性,她由于受不了领导的压榨和无望的发展前景,38岁时从体制辞职。但在遭遇残酷的社会现实后,她后悔到陷入了抑郁,拼命想再考回体制。
阅读作者反复的精神自戕,以及对“体制”近乎魔怔的执念,都令人无比窒息。在另一篇文章里,她曾经清晰记录了自己辞职的来龙去脉——领导的施压已经威胁到了她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而这只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之前的十多年里,她早就已经厌倦了这份工作,想要寻求事业上更多可能性。因此,离开体制并不是她头脑发热的决定,而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
然而辞职之后,她偶然得知“社工大幅涨了工资”,加上找工作遇挫,内心陡然失衡。她像是完全忘记了自己之前的感受和渴望,彻底推翻了之前的想法,陷入极端的自责和自我否定中,甚至开始抱怨起父母没有及早制止她。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因为不知道游戏规则而提前退场的白痴,我甚至开始恨父母为什么没有在我一开始进入这个单位就告诉我‘进去虽然赚的少,但还会涨,而且能做到退休;可千万不能在快40的时候失业,那样就变成40、50失业人员了。’他们只是说‘你就在这里待着吧’而已,我哪知道待多久?怎么待?为什么待?”
这着实令人惊讶,一个38岁的人不知道真实的社会是怎样的?且仍然依赖父母来为她的人生负责?但转念一想又无从苛责,毕竟她如此崩溃,也是因为在求职时遭遇的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和恶性竞争,这畸形的职场环境对个体的压迫不应被正常化。
作者坦诚地暴露自己的脆弱,需要莫大的勇气,也得以让更多人洞悉到老中式的宿命悲剧是怎么形成的——关于这个体制以如何的奖惩机制在规训人,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人们完全失去了超越体制的能力。
这个从“体制”里出走的人,其实没能逃出体制。如果说在体制里的她还保有身心的真实感受、对体制的反思和抵抗它的能动性的话,通过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和对体制发自内心的重新体认,她已被体制毁灭了。
“我爱老大哥。”——在《1984》的最后,奥威尔早就已经揭示过这种毁灭。
文章最后,元琪写到:“我还特别质疑‘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句话,它是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的一句话,大概也只适用于利用互联网做自媒体的人们吧?——我这样想。因为血淋淋的残酷现实中没有给人生提供成为旷野的充足的客观条件啊!”
体制的可怕之处,在于阉割人的自我,剥夺人的能力,使其陷入一种无能状态。可怕的不是离开了它你就没有保障,而是它已潜移默化塑造了你单薄的价值观,狭隘的视野,对人生、对世界极为贫瘠的想象力,并灌输给你超额的贪婪和恐惧。被它规训后的人难以再去为自己掌舵,也只认得出、只会去追求那些他们通过体制所理解的、熟悉的价值。
在体制内的时候,因为领导的刁难和工作的压力而想放弃,辞职之后被现实当头一棒,又日思夜想体制内的好——一个人并不会因为离开了体制就自动获得成长,她仍然和在体制内时一样,最多懂得怎么趋利避害,却尚未拥有足以掌控自己命运的自由意志。
当体制的泡泡被打破,遭遇幻灭和创伤是多幺正常,但没有能力的人会拼命想回到过去的幻象里,有能力的人则会迅速调整自己的认知去面对现实。相信她很快会意识到,危机的另一面其实是机会,回归真相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咬牙走下去,说不定也能劫后余生,逐渐开辟出新的道路,不断获得更多新知与能力,最终超越体制。
人生的价值并不凭空存在于体制外,也不凭空存在于任何地方,它们都需要通过十二万分的努力,甚至赌上高昂的代价,在实践中创造。正如一个读者在元琪的文章后留言:“‘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只适用于那些决心克服千难万难和内心恐惧,把人生变成旷野的人,你觉得是它就是,你去探索它就广阔。”
我相信社会那么大,总不至于铁板一块,应该到处都有缝隙容留离经叛道之人。尽管在体制外生活的空间会随着环境恶化而越发逼仄,它往往意味着匮乏、清贫、孤独……但对于很多心如明镜的人来说,选择这样的生活是一种道德义务——他们拒绝和体制同流合污。
最后,我想分享一篇喜欢的文章的结尾:“人生就像一场翻山越岭的长途拉力赛,旅途那么长,未知风险那么多,起点高一点低一点,影响的不过是开始的阶段。只要一直跑,到后来会发现那些生来就被赏赐的好处都是浮云,最终还是得靠自己。靠自己的双脚去跑,靠自己的毅力去支撑,还要靠自己强大的心肌去泵动血液。相比那些令人艳羡的资产和社会地位,你的家庭所给予的那些无形的东西更珍贵,比如父母的身传言教,帮你塑造的健全身心,亲情支持,以及从小教会你的独立自强等等……”
当你走出了自己的路,再回过头去看——离开体制,你确实失去了一些“好处”,但是当你的心智早已成长到了更高的境界,不再认同过去的价值,又为什么会为此难过呢?




![[集市好物]Queen床沙发餐桌椅](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641915c6-2135-4dda-ab39-5990c0b031b2.750x75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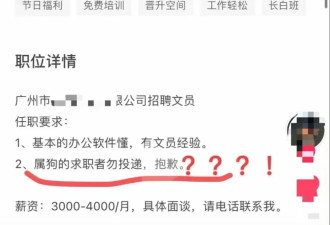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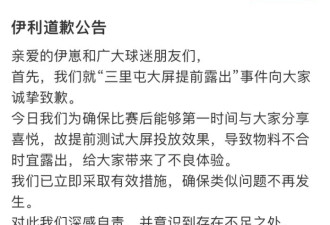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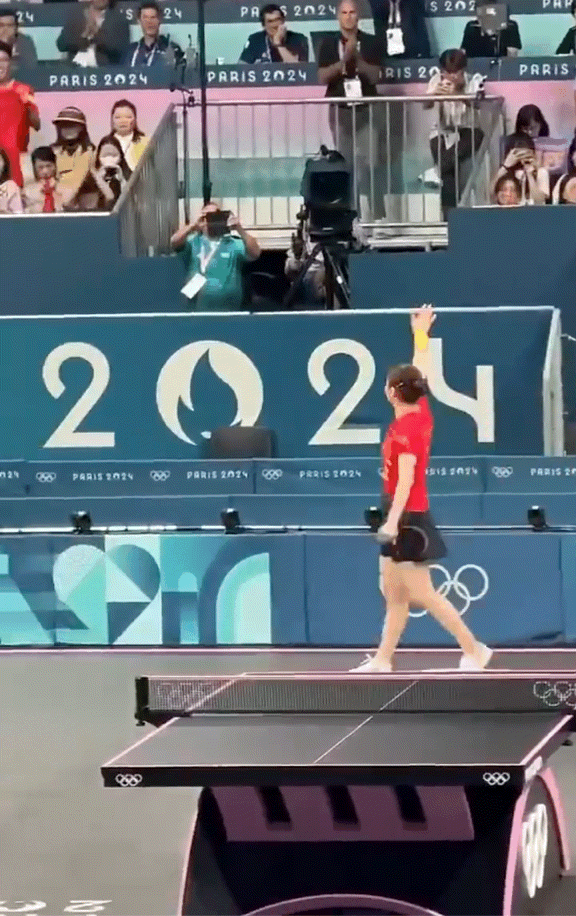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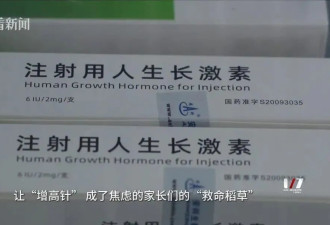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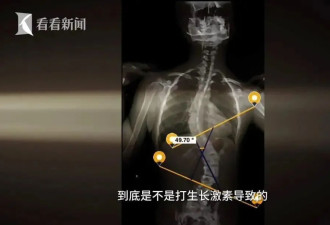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