酗酒的知识分子父亲,打破了我家所有的滤镜

--
我爸是前年去世了,那时候我们仨的关系已经很差了,我妈是要把他所有东西都烧掉,但我抢救出来两本日记。
我还没看过,就等着今天来开盲盒。
月光洒在浅黄的酒杯上。入夜风停了,很静。冰沙肆虐的北方,今晚真好,我呆呆的一个人在工棚旁,在烧烤摊,在电视播放球赛的小饭桌旁,在以后记不起的某个地方。可以举杯了。
夜深了,出去门前307道上的隆隆车声,一切都静下来了。对你的爱和思念分乱剪不断理更乱,唯一可以透过思绪想象得到的是从两端拉呀拉的双手,能最后紧紧握在一起。
其实,没有爱的人做 的那些事,连猪狗都会,那么人呢?在呼唤爱的同时,知道自己的存在吗?
2018 年 4 月 5 号。
爱哲按:
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事物摧毁给人看,那么当原本幸福的家庭逐渐幻灭,就更凸显出生命历程中的悲哀。今天故事的讲述者阿默多年前曾经上过 故事FM 。这次她重来,是想聊聊她的父亲,一个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光彩照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如何陷入酗酒的问题,并将一家三口的关系带入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1-
野性与浪漫:粉红色的父亲和童年
我生长在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矿山,它符合你对东北矿山或者老国企的所有想象。大部分男的都是抽烟、喝酒、打牌。我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就显得特别清新,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做测量的。所以他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就显得彬彬有礼,又有文采。他虽然是一个理科生,但是特别热爱文学,80 年代那些诗歌、文学作品,他张口就来。

■?图 /测量工作中的爸爸
在跟我妈的关系里,我爸非常的浪漫。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其实很少表达爱意。但我爸是随时随地撒狗粮的那种,他会在我面前去亲吻我妈,在中国北方的家庭真的很少见。而且他还经常会给我妈写信、写情书。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吉林搬家搬到辽宁,我们的家当可能没多少,但他们俩的书信就有整整一大箱。
我不是一个男孩,他可能有点觉得可惜。并不是重男轻女的那种,而是因为他天性爱玩儿,如果我是一个男孩的话,我感觉他会带我野的更厉害。尽管我是个女孩儿,小时候他也没有少带我野。比如说在长白山下大雪的时候,他带我去雪地里玩儿,我记得那个时候的雪比我大腿还高,他就直接把我从山坡上往下扔,我就会滚下去。要么就打雪仗,他把我像摊开一个大字一样扔到雪地里,我就掉进雪里找不到了。
他动手能力也特别强,会自己做玩具。我记得有一次跟他逛一个小商品市场,看到一个孔明锁,就是那种非常复杂的木质结构,能够拼在一起的一个益智类玩具,我就很想买一个。他看了几眼,说你不要买,我回去给你做一个。我以为他是随口说说,结果他回家拿出他的木料、锯子、刨刀什么的,真的给我做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

■?图 /老家的照相馆,每年我们家都在这里拍张照片
-2-
狂暴与创伤:美满家庭的 B 面
文艺、浪漫、自由,童年时阿默对爸爸几乎可以说是崇拜,但这或许只是大部分时间下的爸爸,阿默愿意去相信和接受的正常的爸爸。而那个醉酒之后的人,阿默潜意识中从爸爸身上分离开的那个人,实际上很久前就已经存在了。
那个时候我们家是矿上分的房子,因为我爸职称比较高,分了一个还不错的楼房,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走廊,平时走廊就是我玩耍的地方。
我印象特别深。五六岁时,有一次我爸喝完酒回来,我兴高采烈的想去门口迎接他,但是被他一脚从走廊的进门处踢到了尽头。他第二天是完全不记得这个事情的,他还会说我和我妈妈是在胡说八道。
那个时候他俩一直是在为这种事情吵架,每一次我爸喝完酒回来,他们两个都会大吵,然后吵到摔东西。他有时候也会失控,对我妈妈动手,但是第二天只要他醒过来就立刻给我妈揉肩、捏脚,甚至会下跪求她的原谅。到后来,这甚至变成了他们俩的一种相处方式。他们俩就会不停的拉锯、吵架,无限的甜蜜到无限的痛苦,周而复始。
那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回到家看我爸没回家,这意味着他晚上有应酬,出去喝酒了。他回来之后,和我妈又要陷入一个争吵拉锯的循环。
我害怕的是后面的这个过程,我并不是害怕那个喝完酒的我爸。因为等我爸去上班,只剩下我和我妈的时候,我妈又会开始那一套,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都听过的,“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的循环。
我小的时候最怕的可能就是听到这句话。
我平时明明是一个被宠爱的小孩,为什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就变成了一个累赘,或者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当我意识到这句话是不对的时候,我记得我跟我妈说了一句,那你就离吧,不要为了我。
我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妈愣住了,她原来可能会一个像机关枪一样把这一套循环式的话语说完,但突然间我打破了这个循环,她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了。沉默了很久,她就开始指责我没有良心,怎么能说出这种鼓励爸爸妈妈离婚的话呢。
他俩一吵架,我可能就会躲到被子里,或者墙角。不知道怎么我发现自己很喜欢挠头,挠头会让我觉得身体痛了,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所以我挠得很用力,基本上是要把头皮挠出血来的那种,这样一直持续到上大学。
-3-
调停与无力:女儿成年之后
去外地上大学之后,阿默从物理空间上远离了这种揪心的家庭生活,但父母仍然处在这种冰与火一般的循环之中。尤其爸爸后来离开国企去了私企,需要的应酬更多,喝酒频率也更高,而成年了的阿默,也背负了更艰巨的家庭责任。
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情经常会被他俩的电话所左右。比如说我爸,他不喝酒是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他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喝了酒,在饭局上想要向别人炫耀一下他的老姑娘。我有的时候能从他的一个“喂”就判断出来,他喝到几分。我很想跟他好好聊天,但我又知道我不能跟一个喝了酒的他好好聊天,所以我每次接到他的电话都是不耐烦的,我经常第一句话就是,你又喝酒了。然后后面的聊天就不可能正常友好地进行了。
我妈在我上大学到结婚的这段时间跟我通话的频率还蛮高的,但绝大部分都是在讲她和我爸。我后来甚至在想,我是变成了我妈的闺蜜吗?她和我爸的事情也几乎没有好的事情。她好像不太会在跟我爸没有问题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永远都是你爸又喝酒了,你爸又怎么出丑了,你爸又怎么对待我了。我变成了他俩生活里的一个调停者。
我离开东北以后,甚至抗拒回去,我大概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去了。我 2018 年是以旅游为契机去自驾了一圈,但都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在没有告知我爸妈的情况下,我偷偷摸摸的回了一次我长大的那个矿山,我带我老公去了那边一个苏联式的小火车站,非常好看,尖顶的。我对那里印象特别深,但我想不起来为什么印象深了。

■?图 /2017 年回去自驾,经过老家附近的铁轨
走到那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火车站,在我心里是一个粉红泡泡的感觉,我在这里吃过几分钱一个的那种汽水糖,喝过五分钱一瓶的那种汽水。因为有一次我爸喝完酒,我妈带着我沿着铁轨走了一路,我现在在想我妈那个时候是不是要在这条铁轨上结束。但后来她离开了铁轨,带我在这个火车站过了一夜,汽水和汽水塘就是那一夜我所有的回忆。我后来想,如果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那个汽水糖可能就是我最后吃到的美味了。
-4-
挽救与抗拒:父亲的生死线
我爸退休以后,我那个时候美剧也看多了,就意识到我爸可能已经不是个耍酒疯的问题了。他已经是一个酒精成瘾的状态了。比如他早上起来就想喝酒,没酒的时候,他要到处找酒。他一旦喝上,就很难控制自己停下来。当时他体检发现肝硬化就已经有这个征兆了。所以我当时买了大量的书去看这个病,看完之后我给我妈看,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改变他。
我还带我爸看过肝病专科的医生,那个时候是中晚期吧,还有一点点可逆的希望。他从医院出来之后会信誓旦旦地说,哎呀,谢谢女儿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医生。但回到家可能不超过 24 小时,他就又继续开酒了。
我曾经试图给他介绍 AA 戒酒会,但是跟我们的父母也会抗拒心理医生一样,他一听这个东西,就觉得这是扯淡。他觉得我才不要去这种地方,我怎么能跟那些人在一起。他认为那些人是真正的酒鬼,而他不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心情不好,喝一点就会心情好,不要把我跟那些人相提并论。
再后来,他发展地越来越快,已经有精神症状了。酒精成瘾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症状,到最后跟精神分裂有点像。比如说喜怒无常,被害妄想,很难有逻辑地思考问题,他说话已经变得颠三倒四了。

■?图 /爸爸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大脑已经发生病变
当我意识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过,把我爸送到精卫中心的戒瘾门诊。在一次他喝完酒跟我妈的剧烈争吵之后,我妈同意了。后来医生跟我说戒瘾门诊里药物成瘾,毒品成瘾和酒精成瘾的人是在一起的,因为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成瘾。当我跟我妈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妈不行了,我妈说,你怎么能把你爸和吸毒的人关在一起呢。于是这个事情又不了了之了。
所以又陷入了一个循环:我爸不停地喝酒,只要不闯大祸,他们俩自己解决;我爸一闯大祸,我妈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就会从上海开车去苏州。他俩退休后,我把他们俩安顿在苏州了,离上海不是很远,我随时能去。
我现在都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上班又上学,最害怕的就是接到我妈的电话,她一给我打电话一定是我爸这边又出什么事情,有时候看到有两个她的未接来电时,我要深呼吸几下才敢接。
再后来,我成功地把我爸送到戒瘾门诊,那已经是 2020 年疫情期间了。他那个时候的精神症状已经很严重了,会有攻击性,虽然没有上升到肢体暴力,但他可能会骂路人、骂保安、骂邻居,他已经跟我那个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爸爸大相径庭了,你可以把他当做一个精神病人,并且是不讲卫生的污言秽语的精神病人。我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面对这个事情,因为我还是想维持父母的体面形象,在我自己或者是在我身边人的心目中的。但是失败了。
2020 年有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喝完了酒,想要进她的房间强暴她,我就打了 110 。我知道我爸可能并不会真的怎么样,但是因为我妈给我打了这个电话,我只想说这次你听不听我的,我都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所以我就打了 110 , 110 来了之后,也把他成功地送到了精神病院。但那个时候我爸肝硬化已经比较严重了,精神病院是不收的,他们不收肢体上有危险的人,也怕我爸肝硬化大出血在他们医院里死亡,所以他们不想收。
但当时我也从一些医生朋友那里学到一些撒泼打滚的技能,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放他出去,伤害了我妈怎么办?他现在的精神症状你们已经看到了,他如果出去伤害到别人怎么办?
把难题抛回给他们,再加上警察也害怕在疫情封闭下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所以施加了一点压力,我爸就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在精神病院这半年,我爸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酒精。出院的时候,他的肝指标甚至好转了。这个时候我就想给他一点机会,因为我之前联系了上海的一个肝病专家看过我爸的状况。他说这个状况没有可能再逆转的话,就只能进行肝移植了。
因为我爸年纪比较轻,也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单纯就是一个酒精肝硬化,所以给他换肝的话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但在他们的医疗指标评估上最重要的一条是:遵医性。
我爸完全没有。
当时医生对他说,你已经在名单上了,只要你坚持半年不喝酒,后面再有肝源就是优先你的。可出院没有 48 小时,他就又喝上了。当时那个医生是这么跟我说的,你爸来检查的时候,我都闻到酒味儿了。所以这样的遵医性我们也不建议冒这个风险。换句话说,他们也比较珍惜来之不易的肝源,他们肯定会把这个机会留给更愿意生存下去的人。
我记得他在等待肝移植还没出院的时候,我带了一份离婚协议过去。是我替他和我妈拟好的。因为当时我给他俩在苏州买的房子写的是他们俩的名字,我在还贷,想让他俩能在苏州度过一个比较好的晚年。但已经到这个地步,我就给他俩拟了协议,把苏州这个房子卖掉,钱他们俩一人一半,我妈拿着这一半的钱想干嘛干嘛,想去旅游旅游,
想去报辽宁大学就去读大学。另一半给我爸也是,你想干嘛就干嘛,再加上你自己的退休工资,养老是不成问题。我只希望他俩结束,因为他俩当时已经没办法好好说话了,在一个房子里也是分开睡,吃饭都是分开吃。在我看来,你们俩这样强绑在一起,痛苦的人是三个人。
结果他们俩又前所未有地站在了同一阵线,不同意。
肝移植是父亲挽救生命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阿默试图挽救家庭的最后一次尝试。在此之后,阿默也无力干涉父亲的人生了。
失去了肝移植的名额,父亲反复不停地进医院,因为肝硬化到后期会引起肝性脑病,人的意识和记忆都会减退,更危险的是导致内脏出血。
父亲就是在一次内脏大出血中去世的。
我爸走的时候我没有在旁边。因为孩子还小,还要人照顾,后面的事情,都是我老公帮忙处理的。
我给他想象了无数种结局,其实他是按照最好的那种结局离开的。我甚至会想他会不会伤人,然后进监狱,在监狱里离开。所有的剧情都在我脑海里过过了,所以他只是选了一种应该发生的,发生了我也没有害怕、震惊和意外,就是靴子落地了的感觉。
那一刹我可能也没有很伤心,我的伤心可能像坏了的水龙头一样,不停地往下渗。
-5-
回望母亲,回望自己
父亲虽然去世了,但已经深深烙印在家庭成员身上的相处模式,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剥离开。也是在这个时候,阿默好像更加理解了母亲,她的期盼、幻想,还有幻灭与不甘。
我妈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在一个全是男性的环境里面做一份偏技术的工作。在东北下岗潮时,我妈因为年龄的原因就被一刀切强制下岗了,但她下岗之后发现了其他的致富之路,就是教初中生数理化,赚的比矿上多多了。她其实是一个挺有能力的人,如果没有我爸,或者没有在我爸身上倾注太多想象的话,她可能会过得更开心。
我妈对我爸有一个完美的想象,这个想象可能存在于以前给她写信的那个人里,或者在一个琼瑶男主形象里。在那个想象里,这个人不会喝酒,不会暴力地对她。但是明显越来越偏离她的想象之后,她就会越来越生气, 越来越对生活不满意。
甚至到现在我爸去世之后,我妈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再跟她走这个恶性循环了。于是她开始在我的生活里自己创造这个循环。她很想有一个我爸那样的形象,跟她继续吵架,再继续和好,通过这种极端的痛苦和极端的甜蜜。来感受到存在。
最近的一次是我小孩满月的时候,满月体检他没有达标,因为我是母乳喂养,产生了一些喂养困难,我们也在努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妈觉得我解决的不够好,不够努力。她一听到小孩哭就不行,受不了。有一天她又开始指责我喂地不好,然后还想试图以“你小时候怎么样”开头的时候我阻止了她。
我说,妈,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然后那天她突然炸掉了,开始用你能想象到最脏的脏话骂我。那一刹那我也有点懵,我有一对知识分子的父母,然后她在用最脏的脏话骂我,当时我的两个小孩都在我的面前。
我现在说的时候,我都陷入一个解离的状态。我记得当时自己好像飘到了天花板,在看这个房间,这是真的吗?真的发生了吗?
当时我情绪没有很激动,只是不停地在重复“请你立刻离开我家”。她走的时候摔门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我也回了她一句,我也不想要你这样的妈妈。
我妈走了之后,我知道以她的性格肯定会过不久就要给我道歉,然后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过。而我那天的心情就是,我不想要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于是我火速把她拉黑了。
果不其然,过一会儿她给我老公打电话,说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不想听到孩子哭,只是心疼小孩,让我老公转达她对我的歉意。
然后我说我不想听,如果我这次接受了她的歉意,才是真正的在复刻她和我爸之间那个循环。
沿着母亲复刻循环的这种惯性,阿默也好像第一次认清了自己作为女儿,承担的那些原本不属于她的责任,意识到了完美家庭一片片碎裂的过程中,烙印在自己身上的伤痕。
我已经习惯了把自己定位成我爸妈的问题解决者和一切烂摊子的收拾者,直到我跟一个朋友聊起这个事情。她反问我说,你爸是你妈的伴侣,你爸的问题应该是你妈的问题,你为什么老要解决他们俩的问题?她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妈妈是在通过你爸爸来控制你。我才慢慢的去想我跟我妈之间的关系。
的确,我爸是一个话题,甚至是一个工具。因为我妈不给我打电话说你爸又出事儿了的话,我可能都没办法主动回来看她一下,或者主动跟她好好聊一聊。仿佛我爸是我们俩话题里面必须存在的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正常的母女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以有除了爸爸喝酒之外的所有一切有趣的话题,比如聊聊电视剧。
我已经没有办法接受来自她的任何直接的关心和亲昵了,因为我在青春期之前试图向她求助的行为都被无视了。而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你再给我这些东西,我好像不需要了。你期待我给你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可以表演一下,但是我好像演不出来。
我爸去世前一周,我做了一个梦。特别奇怪,在那个梦里我爸好像是一个侏儒,像小孩的身体,圆滚滚的四肢,圆滚滚的屁股,但是长了一个我爸实际年龄的脑袋,在那个梦他说他在等人来看他。
我醒来的时候还跟心理咨询师朋友聊了一下这个画面,然后那个朋友说的确啊,你爸现在的精神状态就是一个怪异的小孩,你只不过把他带入到你的梦里了。
如果说一个完美的丈夫形象在我妈心中破碎了的话,我父母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在我这里破碎了。我小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我学习这么好,从小大家都给我一个这样的滤镜。但现在我觉得,这个滤镜已经碎的特别彻底了。
回看那过去,我觉得有知识或者有文化并不是幸福的保证,去掉那些滤镜之后,其实看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图 /我们一家三口?????




![[集市好物]2016 Kia Soul](https://storage.51yun.ca/auto-car-photos/fc543ce5-f893-4966-8e0c-a8ccb1f0f158.1080x81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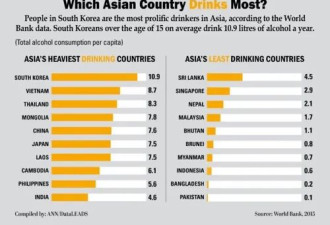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