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凡母亲——荧幕之外的奥黛丽·赫本

赫本和宠物朋友玩耍,罗马市郊拉魏格纳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女演员。她以其独特的气质、优雅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成为好莱坞的标志性人物,凭借电影《罗马假日》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在《蒂凡尼的早餐》中的经典造型也深入人心。但在电影事业之外,赫本还有许多不被人了解的身份。
本期内容将通过赫本的小儿子卢卡·多蒂(Luca Doty)的视角,了解这位传奇巨星从未展现给公众的一面。

赫本在比弗利山庄威尔夏大道公寓
我一直不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小时候经常有记者纠缠不休,总问我关于她的事情,我有时会恼怒地回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是多蒂太太。”他们哄堂大笑。
在6岁小孩的眼中,不管他母亲是芭蕾名伶、科学家、女演员,抑或就只是单纯的母亲,都没什么不同。他只要知道父母能发挥所长,各尽本分,那就够了。
何况我的精神科医生爸爸有趣得多。爸爸在家时总是众人注意力的中心,尤其是妈妈结束她的电影生涯,专心相夫教子之后。
当然,我们依旧会去洛杉矶旅行,但对我来说,迪士尼乐园的灯光比好莱坞的灿烂得多。在瑞士度过一个重要的新年后,我学会了跟着玛丽·波平斯(《欢乐满人间》女主角,朱莉·安德鲁斯饰)吹口哨。
1976年,妈妈出演《罗宾汉与玛丽安》一片,这是我出生后她首度复出,我在拍片现场玩得很开心,但完全是因为“詹姆斯·邦德”(即007男主角,初代由肖恩·康纳利饰)就在她身旁。
妈妈依旧是我的平凡母亲,当然,她很可爱,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是年龄的问题,也和时代有关。
那时大家并不常谈起她——妈妈已经息影多年,而大家对她的个人崇拜尚未开始。
我的朋友第一次到我们家来玩时总是很好奇,因为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他们的父母对赫本的印象——透过她拍的电影和他们所读的杂志。然而只要朋友们认识她之后,所有的尴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赫本和卢卡·多蒂在格施塔德
在我成长期间,一切大概是这个情况。她演《罗马假日》(1953)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奖座,就放在我们瑞士小村庄特洛什纳的家“和平之邸”游戏房的书架上,和其他纪念品一起塞在书堆里。
这些纪念品包括好几匹色彩缤纷的瑞典小马,迄今我还十分珍惜地保存着。母亲选了表彰她人道贡献奖的奖座放在客厅,因为最终她发现它们对她的意义更重大。
她这辈子一直未能如愿好好读书上学,所以我记得当布朗大学在1992年颁发荣誉学位给她时,她非常自豪地对我说:“你敢相信吗,他们颁发学位给我,给像我这样没有好好受教育的人?”
她这种对自己身为“明星”的态度,也来自于她对电影的态度,以及对银幕上自己的看法。她自幼梦想成为古典芭蕾舞星,为了接受这方面的训练,遵循了这种艺术所要求的严格纪律。
她参加知名的玛丽·兰伯特芭蕾舞校招生试镜并被录取之后,由荷兰赴伦敦。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可能成功,对她来说,这一刻十分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耽误了她的舞蹈训练,这一缺失永难弥补。其他舞者在技术上至少领先她五年。“她们有比较好的食物和住所。”她曾难过地说。
妈妈认命地接受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古典芭蕾明星的事实,但在身为演员的生涯中,她以同样艰苦卓绝的精神,遵循她认为在任何领域成功唯一的途径:早点起床准备当天的工作。
她这辈子一直维持这样的习惯,即使息影之后,先当全职妈妈,接着又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依然一以贯之。

赫本在索马里执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务
妈妈从不认为自己是伟大的明星。她对我说过的唯一和工作有关的八卦,是有些演员同事可以彻夜狂欢,次日早晨只要化点妆,再来一杯提神饮料,就能表演得无懈可击。
她说她有时甚至得把他们拖下床,就像对我爸爸那样,爸爸曾承认:“要不是你妈妈逼我淋浴,灌我喝咖啡,我可能永远当不上教授。”
我不会指明她说的那些狂欢的明星是谁,但她调皮的描述包含了诚挚的赞赏:“我永远不敢像他们那样做。”这并非惺惺作态,我记得她接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信那天的激动。
多年前,我们在罗马的电影院观赏《E.T.外星人》,妈妈感动极了,她捏着我的手对我轻声说:“卢卡,这人是个天才。”
如今那位天才请她在戏中演一个角色。我问她要演哪个角色,她答道:“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真的想要我参演吗?”
她飞到蒙大拿州,在《直到永远》(1989)一片中饰演天使哈普——这是她最后一次演电影。或许我该让她多跟我谈谈那次经历。
那时我19岁,也是斯皮尔伯格迷,但妈妈和我谈的多半是我的考试、我第一次和心仪的女生坐过山车,以及其他日常琐事。我们经常谈到她的过去,但并不是关于她的电影。
在谈话中,她经常回忆儿时,关于她所经历的战争和我们家的历史故事。她去世前最后几年——通常是早餐时分——会吐露真情,这对她并不容易。我该多和她聊聊,但青少年很难想象母亲会在短短四年间就离你而去,也不了解这世上会有这么多她永远不能告诉你的事。
所以我对当时那位前“多蒂太太”的印象,在她走了之后没有多大改变。当母亲的癌症病情显然已无法控制之时,我们家人聚在瑞士,在她挚爱的和平之邸过圣诞节。
妈妈和她的伴侣罗伯特·沃德斯以及我哥哥肖恩·费勒一起从洛杉矶回家,我从米兰过去,而不久后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阿斯特丽德则从巴黎赶来。
母亲的挚友多丽丝就住在附近。一连几周,我们的生活都围绕着母亲打转,希望以药物缓减她的疼痛。
然后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了电影,因为肖恩劝我:“你该放松几小时。要是发生什么事,我们会打电话联系你的。”

赫本和罗伯特·沃德斯,与他们的杰克·罗素梗犬在和平之邸
我在洛桑黑暗的影院里接到了那通电话。妈妈走了。我一直很不理性地相信,他们让我去看电影是为了保护我,让我在她最艰难的那一刻走远一点,就像大人有事要谈时,打发孩子去花园里玩一样。
接下来一切都变了。她不在人世了。摄影记者包围了和平之邸,等他们终于消失之后,我的母亲才终于和众人眼里的奥黛丽·赫本合而为一。
等我回到当时的工作地点米兰时,她的脸孔在每一个报摊朝外看着我。我只能在摆脱“赫本之子”这沉重的身份时,才能悼念我心里那个平凡的母亲。
我逐渐明白,我得和那除了我之外人人皆知的偶像妥协,因为尽管在成长的岁月中,我知道母亲很有名气,但其实并不清楚她的受欢迎程度。
同样地,常有人问我有没有时间了解奥黛丽,他们以为我是和他们一样远的距离认识她,仿佛我母亲一直远远地定格在一连串黑白影片的剧照里。
其实,我最早的记忆渲染着1970年代柯达或宝丽来照片的色彩,就像老旧的家庭相册。当时母亲的照片几乎已经完全从杂志封面消失了。1967年,《丽人行》和《盲女惊魂记》上映后,她宣告息影。
自拍《罗马假日》以来已近15年,若从她开始芭蕾舞者的训练来算,更已将近30年,此时她将近40岁,在这之前从未休息过。
记者对她这么早就息影大为惊讶,而她解释说:“有些人认为我放弃事业是为家庭所做的重大牺牲,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接着她又描述自己做“家庭主妇”的新生活:“如果有人认为这生活枯燥乏味,那很可悲。但你不能光是买下公寓,摆设家具,然后置之不理。重要的是你挑选的花朵,你播放的音乐,你等待的笑容。我希望它欢欣愉快,是这混沌世界的避风港。我不希望我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家来,看到的是一个烦躁的女人。我们的时代已经够让人心烦了,不是吗?”
她的话就说到这里,其他的我要用我自己的话来讲。这只是我对这个故事诠释的版本,是我与母亲在一起体验的回忆,以及这些年来我对她的所有了解。
她拒绝了传奇文学经纪人欧文·保罗·“快手”·拉扎尔的提案,并决定永远不写回忆录。妈妈告诉我不会读到她的亲笔传记那天,我问她为什么。
她含蓄地答道:“卢基诺,这样我就得把全部事实讲出来,不能只说美好的事,可是我不想说别人的坏话。”
这本我构思为“厨房餐桌上的传记”的书,起源于一个破旧的笔记本。我的朋友艾莉希亚在我家厨房瞥见一本尘封的活页夹。她把它从架上取下来时,一些页面散落出来,有些写得密密麻麻,附了剪贴和笔记。其中许多记述的是令人印象深刻、雄心勃勃的美食,步骤复杂,却从没有在我们的餐桌上出现过。因为在厨房,就像在人生中一样,我母亲逐渐解放自己,摆脱一切不必要的累赘,只留下对她真正重要的东西。而那些就是你会在接下来的篇章里看到的食谱——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故事。
本书描绘的不是水晶蛋之类的菜色——传记作家告诉我们——她在少女时代可以精心做出这道经典法式开胃菜,这里更忠实地刻画她家常的一面:她旅行时带在行李箱里的意大利面,和好友共度下午时光时大吃的冰激凌,以及她从自己深爱的花园中变出的各种可食之物。而在本书中,也记录了她于星海熠熠发光前的人生轨迹,以及我所知的塑造她之成为她的人格和个性的事件。
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去了一个小女孩所重视的一切。她失去了家,父亲失踪,亲戚遭枪杀或被驱逐出境,而且她时时冒着风险,因为她在鞋子里藏着的要传递给反抗军的信息,很可能会让某人消失。除了青草和白煮郁金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她苟延残喘,瘦得只剩皮包骨,要不是盟军带来的几条巧克力棒,差点撑不过去。
本书有一张她在荷兰解放后几个月拍摄的照片捕捉到了那个时刻,照片只有一行简单说明:战后第一次填饱肚子。接着她就生病了,因为她的肠胃已经不习惯食物了。
我母亲撑过了那些时日,她认为自己能生存下来是上天的恩赐,不能浪费。她勤奋工作,要夺回她所失去的:家庭、家人,以及厨房的温暖所营造的安全感。她的一生中,努力工作的本能不断地鞭策她,在她作为明星的那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岁月之外,她开启通往新快乐的门:她的家。如果说她有什么秘密,那就在家里。一切相互呼应。







![[集市好物]2024AudiS5雪胎和rim](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5153775e-68b9-4bbb-bd4f-e32afd8ecf0b.1080x144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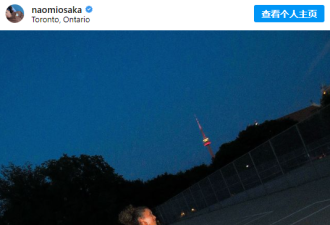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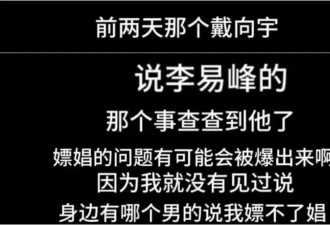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