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引导人民” 南京中学生反内卷呐喊引关注
徐全(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新闻评论人)评论文章:最近,“自由”成了两岸的共同关键词。在中国大陆,江苏南京的一名17岁中学生为了反对学校假期补课、争取放假权利,以“反内卷、要自由”为宗旨,成立了“南京中学生反卷联盟”,迅即汇聚了全南京的众多重点中学学子,其联盟成立宣言更是写上“自由引导人民”的口号,惊动了学校、家长、当然还有警察关切。
在台湾,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区桂芝老师说:中国传统中也有自由,例如庄子的《逍遥游》。区老师的言论引起台湾内部的蓝绿、统独甚至中国大陆方面的舆论回响。台湾区老师的谆谆教诲和南京中学生的奔放,都是冲著“自由”去的。
其实,“自由”一语从出现、到被赋予今时今日的意义,和西学东渐、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文明开化热潮密不可分。
今年恰逢清日甲午战争130周年,那场硝烟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臣民国家无法战胜国民国家。抚今追昔,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或中华民族,并不在于武力、国土、人口,而在于人民的自由、社会的民主和年轻人的活力。南京的这场反卷联盟热潮,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一直都在。
“自由”一词源自日本 乃西学东渐产物
庄子固然在《逍遥游》中提倡精神绝对自主,但庄子的自由,和近世以来直到今人所理解的自由内涵——亦即个人不被群体侵犯,有著重大差异。南京中学生反卷联盟在其成立文告中明白表示:他们不仅反对剥夺放假自由,在假期中强制补课,更需要开放、开明的教育。可见,南京中学生对自由的理解,恐怕比台湾区老师还更准确一点。
伴随基督宗教和通商在东亚的扩展,西学东渐从17世纪开始渐渐影响中日两国。早期中国获取西方资讯的地点是澳门,后来是广州。而日本则是长崎。到了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时代,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均有深厚的民族忧患意识,开始对西方学术思想进行系统化翻译和研读。特别是中国方面,晚清在洋务自强运动中,设立京师同文馆翻译西方著作。而日本则将西学称为“兰学”(日本的西学由荷兰人带入),在明治维新催动下,亦如饥似渴地学习列强文化。中日同时展开翻译浪潮,一派欣欣向荣。

南京一名中学生为了反对学校假期补课,以“反内卷、要自由”为宗旨,成立了“南京中学生反卷联盟”,迅即汇聚了全南京的众多重点中学学子,联盟宣言写上“自由引导人民”的口号,惊动了学校、家长、和警察。(图:微信)
然而,在如何翻译西方学术概念上,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却有重大分别。晚晴中国的大儒、国学大师严复,就很执著于从中国古代文学、文字、经典出发,对西方术语进行精准表述,很是追求形式美感和信、达、雅的汉语美学。但日本方面的学者们则认为机器大工业时代,文字应当力求简约明了,因此对传统汉语的形式主义元素进行了取舍,较为寻求方便与美感的结合。这两种各有特色。
举例而言,晚清中国京师同文馆的大儒们,将Economics翻译为“计学”、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将Metaphysics翻译为“玄学”。但日本方面走了另外一条路,他们将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将Sociology翻译为“社会学”;将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中日两国哪一种翻译更具生命力从而影响后世、流传至今,答案已不言自明。
至于最近台湾区桂芝老师、舆论和思想界争论不休的“自由”一词,更是翻译史中的经典案例。当初晚清国学大师严复将liberty翻译为“群己权界”,意思是说:所谓liberty,其实就是个人与群体的边界。这个翻译方式非常形象、非常具体和准确。但同时期的日本翻译界更直接,他们将liberty翻译为“自由”。从此,“自由”一词,在中、日、韩、越等汉字儒家文化圈,开始流行并发扬光大;而严复的“群己权界”,则被当作经典供奉起来,却未能成为大众和学术界的日常用语。
日制汉语渐流行 晚清中国保守派抵制失败
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洪流中,传统汉语文化、文学、文字的主动权,逐渐从中国移转到了日本。因为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社会演变和民众生活的产物,任何语言文字都是活的,而非死的,所以一直坚持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晚晴国学大儒,并未能够让汉语变得更活、更有生命力,哪怕在学习西方思想的过程中,他们也输给了日本同行。透过翻译和学习西方思想,日语中大量的和制汉语(也就是日本制造、翻译的汉字词,也称日制汉语)词汇,成为了西方语言和汉语的桥梁。这不仅让日本走向了近代化和文明开化,也深深影响了中国。
具体地说,和制汉语从名词、动词、到形容词,几乎是无所不包。“促进”、“浪漫”、“革命”、“教育”、“演出”、“宗教”、“民主”、“哲学”、“警察”、“会谈”、“文学”、“手续”等等……至于意识形态的各种主义和思想,更是来自和制汉语;理工、医学类词汇就更不用说了。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华人,不论是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只要一张嘴说话,就会有几个词是和制汉语。
当年晚清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纷纷使用和制汉语来进行日常表达。这群在当时的人看来颇为“数典忘祖”的留学生们,不仅在日本如此,回到中国更是将和制汉语大力推广,认为其简便、好用。至于晚清中国的京师同文馆的翻译成果,已经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这种现象引起晚清改革名臣张之洞的强烈不满。他向清廷呈文,要求在中国禁绝“日本名词”。结果,他的幕僚、国学大师辜鸿铭提醒:“名词”一语,也是和制汉语。最后张之洞以“日本土话”作为和制汉语的代称,提交了奏章。但毫无疑问是无用的。和制汉语,最终成为了现代汉语中文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连“国学”一词本身,亦来自日本。
甲午之败肇于翻译之败 翻译之败乃革新之败
清日两国经过各自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学习,然后就进入了工业化的改革。而甲午战争是对各自改革成果的检验。今年系甲午战争130周年,中国大陆官方、学界、民间举行了众多纪念活动。中共海军方面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文《【甲午战争130周年】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过去!》:“国耻犹痛,狼烟仍在。甲午海战的悲歌深刻印证一个铁律: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国强则海权强,国弱则海权弱。”在今年7月25日,中国大陆海军方面和政府机关、学校师生在当年的战地旅顺举行仪式,向甲午旅顺大屠杀的万忠墓献花致哀。众多海军舰艇则在海上举行祭奠和宣誓仪式,表达决心和意志。
不过,甲午战争值得思考的,不仅仅是民族爱国主义。历史上,甲午战争最后阶段,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向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发出了史上最为有名的劝降电,其文称: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如伊东祐亨所言,默守陈规、食古不化,是战败之因。甲午之败,非败于军备,而是从翻译西学开始,清国就已经败了。当丁汝昌自杀殉国后,搭载他灵柩的清军“康济号”运兵船行驶海上时,伊东祐亨下令日本军舰鸣放吊丧礼炮。日本海军元老胜海舟听闻丁汝昌自杀,写下悼念文:
“二月十七日,闻旧知清国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之报,我深感君之心中果决无私亦嘉从容,不误其死期,嗟叹数时,做芜诗慰其幽魂。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心血溅渤海,双美照青史。”
反倒是清国朝廷,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丁汝昌,下令剥夺其荣誉、侮辱其棺木。清国北洋水师和当时的日本海军,双方将领许多系英国留学同窗、更系好友。双方打上战场,私交与国族的纠葛,可想而知。但甲午之败,绝非败于军备,而是败于制度、败于文化、败于思想。当时的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已经开国会、制宪法、立政党,人民已经是国民。晚清中国,则是太后乾纲独断、官场腐败,百姓皆为臣民。一个臣民国家,如何能战胜一个国民国家?
未来——倾听年轻人的声音
所以甲午战败后的中国人,没有痛恨日本,也没有袭击日本人学校、没有抵制日货、没有跑去日本做有违公德之事,知识分子也没有大搞国学。战败后的中国人,选择去日本留学,学习新知识;年轻的光绪皇帝甚至想聘请伊藤博文担任清政府改革顾问。那时,中日关系反而进入史上最好的“黄金十年”时期。当中国的改革者们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遭到保守派追杀、迫害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紧急运作,将梁启超等人用日本军舰救走。按今日之标准,梁启超绝对被视为“勾结境外势力”、“汉奸”。
内卷的本质是机会的稀缺,对地大物博的国家而言,机会稀缺是不公平造就的。如果真的要捍卫、发扬、传承中华文化,就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创新突破,否则结局就和19世纪清国翻译西学的结局一样——彻底被淘汰。难道今日中国人反思甲午,只局限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层面吗?当然不是。南京学生的反卷联盟,他们争取、期待的,就是一种合乎人性、制度公平、可以发挥个人创造力、尊重个体差异的美好教育。他们对美好教育的向往,又何尝不是对一个文明、自由和包容的中国的期盼?诚如胡适先生所说:争取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南京反卷联盟的学子们,真正做到了。虽然这个联盟在警察压力下解散了,但他们在反内卷中展现的创意和智慧,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希望。
这种希望在华夏大地遍地都是。一篇由当代中国中学生写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行: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让美国羡慕我们的民主;能够让德国羡慕我们的科学;能够让日本羡慕我们人民的财富;能够让新加坡羡慕我们年轻人的创造力……”
生活服务
-
 日坏球报@ 08-16 16:56您已点过赞中国人都站起来了,只有台蛙和轮胎还跪着
日坏球报@ 08-16 16:56您已点过赞中国人都站起来了,只有台蛙和轮胎还跪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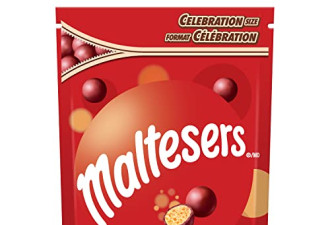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