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辞职卖房,我带自闭症孩子回了东北农村
我曾在少女时代就勾勒未来孩子的画像:他会对生活充满热爱并勇敢善良,内心温暖不卑不亢,当然最重要的一点,长的好看,随妈。
我想给他讲一朵花开的故事,讲毛毛虫如何蜕变成蝴蝶,讲幼年的我躺在院中凉席数星星的美妙夜晚。山川湖海,春来为花忙,夏日捕鸣蝉,叶落识秋意,寒冬去打一场雪仗。我想把人生体验一一讲给他。
但命运似乎擅长搅弄无常。幻想因那张诊断书戛然而止。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小男孩。

人生上半场,艰难的抉择
西安的初春,又一个安抚完孩子爆哭的深夜。我与先生躺在床上,吊着重重的黑眼圈,各自长吁一口气。
这样的情节,近来每天都在上演。
小维确诊重度孤独症,是在两岁那年。
在北大六医院,小维在被诊断的一系列流程中,无法回应大夫的任何问题,无法配合任何指令,一张百分之八十打了叉叉的测评,是对他的审判,也是对我们的。
刚过了年的北京还是很冷,那天阴天,雾蒙蒙的,我们站在医院的门口,四目相对,不知如何说,不知从何说,孩子还一旁咿咿呀呀蹦蹦跳跳,他依然那么开心可爱,但那刻,他发出的声音和动作都变得怪异无比,像尖刀直戳我的心。
天也不知什么时候黑的,但北京的夜景真美,我们在出租车上第一次看到了庄严肃穆的天安门。
我曾幻想过带长大后的他去很多城市,他会像十万个为什么缠着我问这问那,我还设想应该如何解答,他会在回程后和他的好朋友分享这一路的旅途风光。但是那次的北京之旅,和我设想的显然不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先生提议,去看天安门和故宫,来一回,总是要去看下的。
天安门和故宫门前排起很长很长的队,我们领着孩子站在队伍里,有那一瞬间,恍惚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们只不过和其他人一样,是带着孩子来旅游的年轻夫妇:先生背着双肩包,孩子骑在他脖子上,我拿着身份证和门票,给孩子掖了掖衣角。
我们有说有笑,看起来和旁人也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我的心里像长了刺,时不时总会被扎痛。
真正漫长的干预之路,是在离京之后。
确诊后,在机构干预的两年多里,小维的技能虽然有所提升,但情绪和睡眠已然到了崩溃边缘,我们的身心也在日复一日的干预与对未来的焦虑中疲惫不堪,仿佛身处隧道之中,深邃幽暗,不知何时得见天光。
小维的睡眠障碍由来已久,从婴儿期的频繁夜醒,到两岁时的入睡困难,再到三岁时每晚凌晨一点无理由地突然醒来,玩到清晨六点入睡;现在四岁,这样的情况越发严重,每晚睡前爆哭一个小时,怎么安抚都没用,只能等他精疲力尽再沉沉睡去。
这四年,我见过凌晨一点两点,三四五六点的夜空,幽深,静谧,就和今晚一样。
沉思半晌,先生终于开口,“我们把房子卖了,我们回老家吧”。
说完,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我猜他想说这话很久了。
从大学到毕业、结婚生子,这十余年,我们的青春都留在这座城市。这里有我的师友,同事,我们亲手打造的小家,还有曾经怀揣的梦想。
我先生老家在辽宁省丹东市周边的一个小乡村,他说:“我想让儿子回归自然,但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在自由和爱的环境中做自然的情景干预。”
我也开始复盘。我出生在山东的县城,妥妥的小镇做题家,从小被教育读书高于一切,靠着父母的托举,才能来到大都市。
“回到农村”,无疑和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追求相悖,说实话,我心里挺没底的。

东北农村,接纳了我们
从决定卖房,到办完手续、交接离职,再到将最后一箱行李装进长长的物流车,也就短短三个月时间。
整整72个包裹,是我们在这个城市停留十多年的印记。那些读书时肆意快活的青春,职场的嘉奖,结婚后育儿的幸福,医院里确诊单的绝望,随着72个包裹被邮政面包车一车一车拉走。
我们和这个小家留了一张最后的合影,我摘了一片树叶夹在书里,算是与过去做告别。

在回到老家之前,我也从未在东北长久生活过,只在结婚宴请和春节短暂停留,所以印象里只有深冬回村的不佳体验,加之我自幼听父辈们对老东北“蛮荒”、“极寒”的描述,导致我对东北的认知只剩下一个狭隘的“冷”字。
我们自驾回了一趟山东我的娘家,再从山东沿海岸线北上,在8月抵达辽宁。
经过蜿蜒曲折的山路,映入眼帘的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潺潺流淌的溪水,清透的蓝天和大朵的白云。只那一瞬,我对充满未知的生活不再恐慌,反倒有点期待了。
小维很兴奋,他从车窗探出头去,目不转睛地欣赏陌生又美好的景色。我心想,我们的决定也许是对的。
到了家门,小维的爷爷奶奶等候多时,热腾腾的饭菜备好,先生迫不及待,没来及说几句话便坐下大快朵颐。一桌子全是他爱吃的东北家乡菜——酸菜炖排骨,土豆炖豆角,茄子辣椒包,小鸡炖粉条……
当时我们赶上了夏天的尾巴,简单安顿下来后,便每天带孩子去户外撒野。

从城市的快车道急转弯,我们驶入一个新的车道,不拥挤,缓慢的,没有加塞和路怒,只安静享受自己的旅途,也让我们渐渐慢下来。
以前在城市,带孩子接触自然要开车走很远的路,现在出了家门便是大山,再走几步,是潺潺的河水。山上流下的水,冰冰凉凉,孩子喜欢挽起裤腿在水里跳,溅起的大水花让他开怀大笑。
我捡起一些小石头拿在手里,他跑过来找我要:“妈妈,石头。”
四岁的他仍然仅限于简单的需求表达,称谓加名词。动机,是练习口语的最好机会,我便想方设法在这些动机中去触发他主动沟通。
我说:“扔!”
他模仿我:“扔”,接着把石头扔进水里。
“妈妈来扔个大的,一二三,扔!”大石头溅起的大水花,让他开心的跳起来。
他喜欢模仿动画片小猪佩奇里的场景,只不过以往在城市里,可以模仿的自然场景不多。
《小猪佩奇》有一集《宿营》说的是佩奇全家在外宿营过夜、捡树枝点篝火的情节,这回,我们一起到山上,他主动提出想法:“妈妈,捡树枝。”
我陪他一起捡了树枝后,他再次提要求:“点火。”
我找到一块安全的空地,把树枝堆在一起点燃,小火苗上蹿下跳,他兴奋地围着小火堆跑啊跳啊,仿佛置身在熟悉的动画场景中。
玩够了回家,奶奶已经做好了饭。有白天在地里摘的豆角,架子上结的黄瓜,山上挖的各类野菜,我们三个人如饿虎扑食,一吃一大碗。
东北农村蔬菜瓜果长势旺盛,这个季节,白菜、生菜、辣椒、茼蒿,茄子、土豆、番茄、豆角,菜园里种的菜,怎么吃都吃不完。
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农民对土地有如此深的感情,土地是一切生命的起源,是自然馈赠的宝藏,是治愈心灵的良药。
由于我们卖掉了房子,有一定的积蓄,所以并不慌着去工作。
东北独有的松弛,让我和我先生慢慢减缓了焦虑,小维脸上的笑容明显增多了。我们都在感叹自然神奇的治愈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努力学习干预知识,给予孩子科学的帮助。
也许是白天玩累了,小维晚上闹腾的次数和间隔都在减少。看着他熟睡的样子,我忍不住感慨:“真好,一切都在好起来。”

在自然的魔法里重生
很快暑假结束,九月份开学,我们便找了镇上的幼儿园去做融合,这也是我们回到农村的目的之一。
镇上一共三家幼儿园,在我提出陪读的要求后,前两家都婉拒了。
第三家幼儿园,园长是个信仰基督的老太太,她戴个眼镜,很温和,说话轻声细语。我们去的时候,是个周末,她正在厨房做饭。
和城市的幼儿园不同,这个幼儿园在她的家里,或者说,她的家就是幼儿园。
一个东北镇上特有的小院儿,连接的三间房子便是大中小三个班级,中间是厨房和她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张大炕。幼儿园共有五十几个孩子,已开设二十余年。
我介绍了小维的情况,老太太表示理解与惋惜,二话不说立刻接受了我们的陪读要求。我便成为幼儿园“陪读”妈妈,每天和孩子一起上下学。
小班的小朋友对我的到来感到好奇,时常转头看我,撞上我的目光,他便立刻转过头去,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会跑来问我:“你是他的妈妈吗?”
“不是,我是学校的老师。”为了便于孩子接受,我撒了个小谎。
“那你为什么陪他一起上学?他不会说话吗?”
“他会说话,只是不擅长交朋友,他需要一些帮助。你愿意帮助他,做他的朋友吗?”
小朋友一个个雀跃地回答:“我愿意!”
这里的老师也极好相处。东北人特有的大嗓门,热情,爱笑,对孩子格外包容,她会在吃午饭时招呼我,“妹啊,一起吃啊。”
我觉得不适合表现出饥肠辘辘的样子,于是拒绝,老师便把大酸菜包子硬塞到我手里——嗯,果然美味。
上午和孩子一起在幼儿园,下午我们就出去撒欢。山野草地,反正有的是地方玩儿,我们骑着奶奶的小摩托车,在两边满是苞谷地的乡间小道上穿梭,那条路上,洒下一路阳光,也洒下我们仨的笑声。
广场上有人在跳广场舞,音乐穿透云霄“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我们就跟在后面胡乱扭动,笑作一团。跳完我会在广场上练滑板,孩子骑他的平衡车,先生加入一群打篮球的初中生队伍里。

我们带着吃食去树林里野餐,为孩子准备好小桶和铲子,他认真挖土,我们吃得不亦乐乎,爬到山顶上可以眺望整个山村,一览众山小时,会觉得人如此渺小,那些苦难就真的好像不那么难了。
天黑前,我们往回走,农村没有路灯,但好在月光很亮,很多时候犹如白昼。苞米杆子上有闪闪荧火,那是飞舞的萤火虫,与夜空中的繁星辉映。
“我们小时候,会捉住许多萤火虫,装进瓶子里,就成了一盏明灯,照亮漆黑的山路。”先生说。
在这个美好的秋夜,我恍惚觉得,确诊那天的慌乱失序、夜醒爆哭的幼童、对未来的焦虑绝望,已经远得就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事。

东北的雪,治愈了睡眠障碍
冬天来临,我们期待已久的第一场雪终于下了。
早晨起来看到院子里和远处山上的厚厚积雪,连绵覆盖在大地上——下雪了!
老师在群里发了停课消息。我把早早就准备好的棉鞋,棉袜,棉手套,棉帽子,都拿了出来,这下它们终于派上了用场。
匆忙吃几口早饭,我们带着小维上山了。松柏枝头挂满雪,一抖落一身,漫山遍野的雪像是误入童话森林。

孩子被白茫茫的一片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蹦跳着对我说:“妈妈,堆雪人!”
现在,他已经会说简短的句子了,于是不停指挥我们:“做雪人的身体!做雪人的头!捡树枝做胳膊!石头做眼睛!胡萝卜做鼻子!”
“可是,我们没有胡萝卜怎么办呢?”在游戏的同时,我也引导他思考解决问题,那怎么办呢?回家取吧!
他连跑带骨碌下了山,我在后面吆喝,“慢点,慢点!”
到了家,找到奶奶,小维说:“奶奶,我要胡萝卜!”奶奶问:“你要胡萝卜干什么?”他回答:“做雪人的鼻子!”
拿着胡萝卜他又匆忙爬上山,给雪人安上鼻子,拿石头做嘴巴,再把妈妈的帽子给雪人戴上,完成!他心满意足地笑了。
大河里结满了冰,爷爷动手给他制作小冰车,用废弃的木板和铁片,再挂上一根麻绳,冰车就完成了。
我们在冰面上滑行,我一个不留神,结结实实跌倒在冰面上,一阵哀嚎,“啊,好疼啊!”
小维见状,跑过来给我揉了揉屁股。在三年前,我从未奢望有一天他能共情我的疼痛,而那天,他却懂得了心疼我。
我疼得想哭,但又笑出声来。
没人能懂我那一刻的心情,这样一个普通孩子的共情举动,发生在谱系障碍儿童身上,是多么的难得,也没人知道,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珍贵。
冬天的夜晚,比西北来的更早一些,四点多,晚饭还没进肚,外头就已漆黑一片。
神奇的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的睡眠障碍却意外得到了解决。夜里八点他就开始哈欠连天,跟我说:“我想睡觉。”
我引导他自己洗漱,在床上读一会儿绘本,听几首儿歌,九点就入睡了。自那以后,他再也没夜醒过了。
改变的不止小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被这寂静的夜晚包裹着,连窗外偶起的风声也让人无比心安。

人生下半场,换一种活法
小维开始有了很多爱好,喜欢画画,最喜欢画花、房子和小兔子,这些都是小猪佩奇里的场景。他还喜欢捏粘土,捏成各种水果、雪人和披萨,捏好的披萨假装放进烤箱里去烤。
他喜欢听歌,我买了一架电子琴,我弹简单的曲目,他唱歌,节奏感居然还不错。他学会了唱《拔萝卜》《数鸭子》《上学歌》《小星星》《玛丽有只小羊羔》。
他开始学着在超市买东西,学着写字,也已经能帮我们干些家务活了。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浅尝到那份为人父母该有的乐趣。
如果说,回农村前的机构密集干预让小维逐渐有了“人样儿”,那回农村后的自然亲密养育则让他有了“人味儿”。现在,小维的情绪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我与先生在干预孩子的过程中,也治愈自己。孩子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却让我们尝试了人生的更多可能。
我学会了烘焙,美食拥有治愈的力量;我热爱画画和摄影,这让我始终保持对美的感知;我们一起游泳,爬山,运动,让身体保持健康充满元气;我们阅读,旅行,去思考体味不同的风土人情。
生命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车、房、名利、前途,还有健康,快乐,接纳一切发生的勇气和坦然,面对苦难时的淡定和从容。

为帮更多迷茫的家庭找到方向,我先生在线上也做家庭干预指导@蜗牛快跑,我会在小红书上分享我们的故事@方圆与小维,用文字为同行的父母带去微薄的力量。
2024年夏天,当我在深夜的书桌前写下了这篇文章,早已从四年前拿到诊断的痛苦中抽离,终于能坦然地将这段故事付诸纸笔。
是的,我有一个自闭症小孩。我用了四年,来完成这个肯定句。
时隔四年,若有时光机,我想穿过岁月,去抱抱那个曾站在北大六院门口,在冷风中啜泣迷茫的自己与我先生,告诉他们:现在的我们都很好,别着急,慢慢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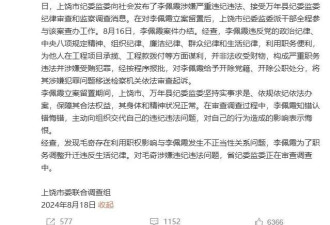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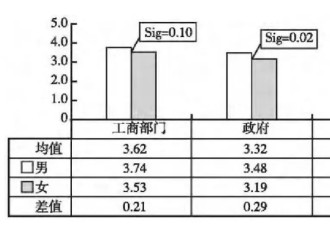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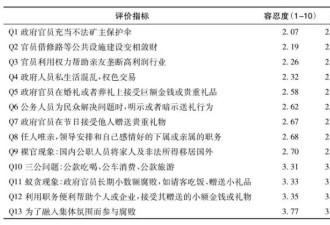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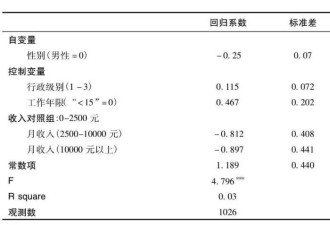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