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几乎停滞 西线未开工
海水西调:现实离科幻有多远?
“海水西调”的科幻式设想,令局内人尴尬、局外人围观。然而关于大调水的新争论却再次揭示自然的定律:在当前水资源的开发过度和利用低效的双重背景下,脆弱的中国水系上再容不得任何违背规律的动土
许多水资源专家在被问到“海水西调”和“引渤入疆”时,都面露难色。
在这群专家中,有大胆者直言,这种科幻式的想象丢弃了对自然和科学最基本的敬畏;有谨慎者称,这是一个只能论证其“不可行性”的调水项目。
然而这样一个“不可行的”的疯狂设想,却拥有一个史诗般的思路:
从源头天津附近的渤海口凿洞,让海水通过8米口径的玻璃钢管横穿海拔1200米的内蒙古高原,跋涉5000公里,流入河西走廊疏勒河自东向西的天然河道,再灌入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布泊,并填满拥有地球上第二大沙漠的塔里木盆地,最终在中国最大的地区形成人造的雨水循环。
如今,在遭遇了同“通天大运河”“凿山引暖流”相似的全盘否定之后,这项源于一名国土资源部机关退休干部的“大胆构想”却未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作为引发跨流域调水工程新一回合讨论的引子,它理应提醒主张大兴水利的人士们更多。
“只论证不可行性”
自1999年“海水西调构想”首次被退休干部陈昌礼发表在权威杂志至今,已满10年,但是这份对调水工程多年的执着并没有为陈昌礼赢回最终的肯定。
这位年过古稀的国土资源部原地质矿产部勘查技术司干部,自从1955年在新疆工作期间看到“沙进人退”的危机后,便致力于研究解决西北干旱的办法,直至退休。
今年11月24日恰逢陈老先生八十岁大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要在这一天再发表一篇文章,回应近期工程院院士们的质疑,并“回顾海水西调这十年的进展”。
“我相信,我的构想在20年内可以获得共识。”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国土资源部退休后,陈昌礼被中国地质大学返聘为教授。1999年至2004年,他发表了6篇关于“海水西调构想”的论文,有关“构想”的材料还曾作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学习汇报报给了党支部。这一举动多少令国土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局的工作人员尴尬。他们只得在给老人的回信中,委婉表达“对于这种构想的可行性……不敢妄加评论”,但对“一名老科技工作者退休多年后仍对理想孜孜以求,仍关心社会、民生的可贵精神……深为敬佩”。
“既然南水北调可以建,那成本更低的海水西调就可以建。”陈先老生表示。这句话如今已失去意义,但它还是印证了一个老人和他的大胆构想在体制内一起走过的曲折路径。这一路,国内学界既是这个构想的起点,也成为了它的终点。
2001年10月,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以专题报告形式刊登了陈昌礼的论文:《海水西调与我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根治》,并在封面刊登了陈老先生绘制的“海水西调”走向图。
9年之后,11月16日,同样是来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在传闻是“被迫”举行的工程院记者会上,彻底否定了这一构想。
一名与会的泰斗级水利专家在匿名的前提下果决地表示,“海水西调,只能论证其不可行性,而不是可行性。”在场的另一位中国工程院权威同时强调, “不需要用工程院的尊严来讨论这个问题。”
此言一出,媒体立即将陈昌礼先生的构想与引雅鲁藏布江调水北京的“大西线调水”和“从喜马拉雅山凿洞引印度洋暖湿气流”相提并论。事实上,有关 “海水西调”的提案也曾被提交到水利部,但随后以“盐水失衡”的理由遭退。
然而,作为仍然支持“海水西调”方面的人士,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秘书长张宝印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质疑,应该到了立项之后再解决。
“(他们)质疑调水调那么多,所需能源从哪儿来,产生的效益会多大,盐碱化问题能否解决…… 这些问题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这位年迈的秘书长表示。“谁来解决?谁需要去解决?只有在实用部门真正立项了,那是需要解决(的时候)。”
这些想法都源于美好的愿望:“有水了就是人间天堂,没水就是戈壁沙漠。海水过去填满新疆一系列湖通过蒸发形成降水,改善气候条件,不仅新疆、内蒙古能得到改善,华北地区也都能得到改善。另外,将来大规模调来的水,沿线都可以用,可以发展多种养殖业、海水种植业。”
对于海水西调的支持者来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海水西送工程”便是他们眼中“引渤入疆”的样板。虽然负责工程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泓元海水淡化公司坚称“项目已批准立项”,并前期开工,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获知,目前尚无关于海水西送工程立项的决定。
和陈昌礼不谋而合的海水西调设想的另一位专家,西安交通大学生态环境与现代农业工程中心霍有光教授通过计算认为,利用新疆现有的东高西低的地理条件及现有河道,海水在引入新疆后,可形成自流,还能对冲前期的投入成本。
“海水西调工程如果按照一方水1元钱计算,从渤海调一方水到新疆的成本只要7块钱,比南水北调的20多块便宜数倍。”他说。
但在科学面前,这些美好的愿望被逐一驳斥。
在工程院召开的记者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原主任李泽椿院士表示:“我和我的同事讨论(海水西调),大家都不想讨论,因为它忽视了大气物理上的最基础的原则,不是有了水气就能下雨。”
在他身旁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原副主任宁远研究员直言,无论是管线展设、工程造价还是终极水的配送,这个题目都“没法想象”,只属于“科幻题材”。话音刚落,记者席间响起一片解脱式的笑声。
在长期关注水利史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看来,海水西调等荒诞设想之所以有传播空间,或许源于当下国内水资源开发过度的客观现实。
“动土”的规律
中国的水资源研究者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边是近千年来形成的河网水系,一边是当前中国水利史无前例的高速建设。
据新华社去年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利建设的累计投资已超过9545亿元,为改革开放前的17倍。而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会议上,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表示,中国的水利建设进入了大规模建设的高峰期。
他透露,2008年和2009年是国内水利投入最大、在建项目最多的两年,也是水利保障能力提升最快、水利惠及民生效果最明显的两年。他还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水利建设还将迎来历史高峰期。
目前,中国不仅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枢纽和多座巨型水库,还在分段推进包括南水北调在内的多个跨流域调水工程。
然而,包括水利水电权威潘家铮院士在内的多名学者均曾指出,中国水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对水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费—— 并存。
潘家铮院士曾指出,在工农业和城市用水上,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用水效率的惊人低下。比如,在北方地区,黄河水资源利用率已超过67%,而海河更是高达90%,均远超合理程度。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引发了湖泊干涸、河流断流、地下水超采和河口及干旱地区生态恶化等一些列问题。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仅为先进国家的一半,全国工业单位产值用水量却是先进国家的5到10 倍。多数城市的自来水管网的漏失率还维持在20%的高位。
“不少水利专家主张水利开发,计划在所有流域都搞工程,结果是许多地方环境形势相对混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表示。
多年参与重大调水工程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目前水资源的科学利用率低是事实,但是判断水资源开发过度,还为时尚早。
“从水能利用来看,我国的已开发量占可开发量的比例还不足一半,还有可以开发的地方。从水量利用来说,虽然大流域上的工程已经具备调节水量的能力,但目前中小流域,如经常旱涝交替的湘江,就还是需要蓄水能力充足的项目。”沈院士说。
他同时强调,面对每项跨流域调水工程,都要从水文、环境上进行细致研究、勘察和调查。“没有科学数据,没有深入分析,工程不能轻易动。”
中国的水资源专家们十分清楚,如果跨流域调水工程范围内有许多污染源,不采取措施就会调配出遭污染的水,从而引发咸水倒灌,水质恶化,破坏河口及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
前苏联就曾建有15项大型调水工程,其经验可谓中国的前车之鉴。
当时,前苏联“北水南调”的年调水量达480多亿立方米,是今日中国的数倍。但是最终因为调水引起源头河流水量减少,使沿途水域无机盐总量、矿化度、生物性堆积物增加,导致生态灾难。
除生态环境等因素之外,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复杂水系,也让调水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如何顺应自然赋予的脉络进行水利布局,是当下调水工程师们需要面对的课题。
“秦汉以来,黄河、淮河流域的工程都失效了。京杭大运河真正有经济价值的只有淮阴至杭州段,济宁以北的河道长年干涸。”邹逸麟教授指出。他还曾指出,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时期最大的“南水北调”,也违背了自然条件。由于其流域地势中间高,两头低,通过泰山山脉时完全通过水闸人工抬升水位才能通航。
与京杭大运河不同,中国古代还有两项极为成功的水利工程:连接湘漓两水的灵渠;分流岷江的都江堰。在邹逸麟教授看来,这两项工程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它们都并非以主观调水为目的。“这两项工程本身都不是水少水多的问题,而是如何控制水量,都是顺应自然状况而建造的。”
相比之下,关中地区最早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虽然曾在战国末年就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用以灌溉关中平原,但数百年前就不复存在了。1949年后,郑国渠又经历了三次修护,如今依然滴水不进,渠首只剩了几块孤单的名牌。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专家周魁一教授经研究发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在降水量没有大幅改变、水利工程能力逐渐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水患灾害不减反增。他认为,这说明社会因素对灾损程度同样有着巨大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对自然应该有适当的避让和尊重,确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重视历史积累的治水观念,应当成为水利规划和水利建设者的追求。重拾古代整体、综合、辨证科学思维的中国智慧,不失一个明智的选择。”2007年8月,周教授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中如此总结。
“难”水北调
距离“通天大运河”的争议已过去12年,但在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眼中,仍有不少人对当年那个“只嫌其小,不嫌其大”的南水北调“大西线”设想念念不忘。
1998年,由13名军队和部委人士提议的“大西线”建议书形成。这项一鸣惊人的方案设想从穿越国境的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三线同时取水,导入黄河,并在五年内完工。由于这一设想过于“前卫”,一直被坊间称为“通天大运河”,有关它的争议直至时任水利部长汪恕诚以“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 的理由否决,才算落幕。
“大西线,也就是‘藏水北调’。这个设想我们早就持否定态度,最近也不怎么说了,但是还有人对此耿耿于怀。”沈院士告诉记者。
当前国内水利水电研究者已经达成基本共识:调水工程的距离越长、规模越大,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就越复杂。
沈国舫院士认为,南水北调工程进度被拖慢,即是如此。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规模空前的跨流域调水项目,其工程东线的主要问题是沿途的水质污染。而已“迟到”四年的工程中线,也因为涉及到庞大的移民工程,并纠结于调水沿途缺水省份的补偿和分配问题,几乎停滞不前。
即便在“拨正方向”后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了八年之后,原规划中拟从长江上游干支流调水入黄河上游的工程西线,至今仍未开工建设。
沈国舫院士表示,学界并不反对西线的建设,但其复杂性要求专家们继续研究:一旦西线开始调水,用何种方法穿越当地的庞大山脉,以及作为调出地区的四川省,自然环境会受何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学者对逐步实施中的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沿途区域环境、气候负面影响的分析,并不少见。当然,这些负面效应也曾在南水北调开工建设前的环评报告中,也都占有重要篇幅。
今年1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地理科学进展》发表了一篇报告,其中说明:相比调水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负影响”处于强烈或明显的状态,并存在调水实施后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报告称,南水北调对有关流域水质、土质、社会生产和水生生物的影响幅度上限均超过了40%。
早在2001年,西安理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三位水资源专家就联合发表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气候的影响研究》,报告指出:由于调水量规模过大,汉江稀释自净能力下降,因此发生浮游藻类爆发性生长繁衍的可能性增大。此外,汉江缺水还将引发航道水深减小,河沙淤积。
专家似乎不幸言中。据近期媒体报道,汉江流域藻类爆发形成的“水华”现象,在调水建设后开始变得频繁。
对于已经开工的东线,结果似乎也不乐观。
2006年,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发布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概要》,该研究所曾参与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这份报告指出,东线工程对沿线的生态环境、土壤、地下水资源已造成相当的破坏,若南水北调及沿线截污导流工程的运行调度过程中,上游治污不彻底,还有可能发生干线水质迅速恶化,使局部水域发生“死鱼”等水污染事件。
对于这些报告的结论,沈国舫表示,南水北调肯定有负面效应,但在专家眼中还是“利多弊少”。“这和三峡工程有利有弊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所有人只看其中的‘弊’,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
沈院士还强调,有关报告是否科学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立场。“有的研究实际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各省有各省的利益,有利害冲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则认为,即便南水北调工程依设计完工,如果各地区用水总量不能减少,调水工程也很难实现灌溉北方的目标。
而目前,国务院对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方针,已被广泛解读为“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
曾参与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部分环境学者曾建议中国参考美国跨流域调水立法的做法,每建一个调水工程,都设计一套相应的具体法案,在完善调用的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同时,监督调水工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正是严格的法律程序让美国当前的任何一个调水项目都面临公众的投票和监督。比如,长达450多公里的拉斯韦加斯调水工程,经过四年的争论,始终未获通过。
而相比之下,我国拟发布的《南水北调用水管理条例》自2006年被首次提起后,既没有再次公开讨论,也没有推动立法。
沈国舫院士认为,造成立法停滞不前的原因是调水问题的复杂性,“要看一个项目究竟是适合全国立法,还是区域立法。”
邹逸麟教授则认为,要解决当前中国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看调水政策的出发点。“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际作用都是有限度的。任何调水工程都应该是顺应自然,而不是违背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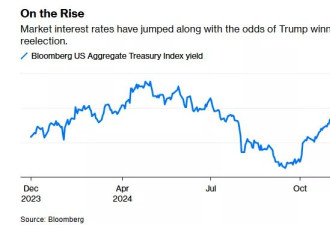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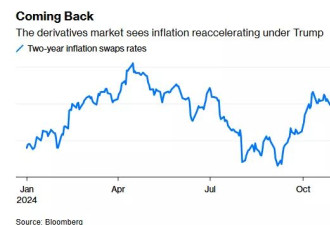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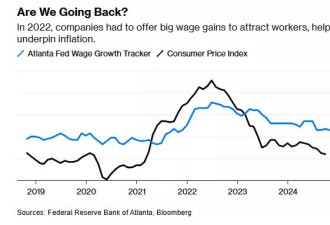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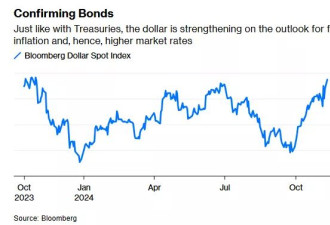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