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表达:去阶级化同性恋的现代演进
早在1936年,当共产主义同志决定拒绝他这个“同志”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抱有好感的伊舍伍德就意识到自己要与之保持距离。他清楚地意识到,共产主义许诺的平等自由里面没有同性恋解放事业的位置,你们在谈论自由,这是否包括我们在内?
八千里路云和月,今天的同性恋知识分子还会和工人阶级相会吗?怕是难了。因为今天同性恋的中产化早已经将这一身份的革命性稀释殆尽,成为后现代社会人们有权自由表达的表象,而同性恋身份政治也从最初的激进变得日趋多元,平权的概念依旧存在,阶级的观念却已经从同性恋中被移除。
今天主流的同性恋电影体现了这种去阶级化特征。我们可以发现,阶级这个因素在今天的同志主题电影里已经被大大弱化了。譬如根据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卡罗尔》(Carol)里,百货商店售货员特芮丝和贵妇卡罗尔之间的爱情,更多地被处理成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情欲叙事,像舒婷《致橡树》中那句经典诗句一般,“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亦如作家黄昱宁敏锐地注意到的,在小说里,特芮丝从卡罗尔的话语中辨认出“高雅的欧洲口音”,这一点成了她扔下男友与卡罗尔私奔的潜在原因。而卡罗尔口音中挥之不去的“欧洲性”,不仅成功地从文化层面收服了特芮丝,更在阶级流动层面如风卷残云般包裹了她。
这段爱情对特芮丝的真正意义,不仅是逃离性别秩序、父权秩序,还是告别苍白的青春期,迎来日常生活的革命,更是她茫茫黑夜里的最高光明。但这种阶级差距的叙事,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展现。
同样,在白先勇的《孽子》里,底层流浪儿阿凤爱上贵族龙子,并被后者手刃于刀下。插在阿凤心上的那把匕首,对于阿凤来说,那不是伤口,那是解药。阿凤从泥潭一般的黑暗王国中找到了永恒的光明,这束光明只有豪门府第里的龙子能带给他。
作为这个世界同性恋内部阶级洗牌重组的见证者,经历过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蜜月期,再到后来分道扬镳之后,伊舍伍德最终还是告别了早年的左翼立场。1952年,伊舍伍德与海因茨(Heinz Neddermeyer)在柏林重逢。此时海因茨已经结婚生子,并且给自己儿子取名克里斯蒂安,显然有着纪念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德之意。但时过境迁,与陈年往事一同逝去的,或许还有伊舍伍德对于工人阶级的浪漫想像吧。尘归尘,土归土,就像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单身男人》里那个对坐读书的经典画面一样,最终和他走完后半生的是和他门当户对的阶级兄弟。
回顾过去这种同性恋内部阶级融合的可能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要美化这段看似革命性的历史。对于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我们也需要重新追问,这种革命性本身是不是也具有它的历史特殊性?它的失落是不是也肇因于其自身的悖论?
显然,上流社会的同性恋知识分子对于工人阶级的这种想像,确实更多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浪漫化。一旦这种浪漫化遭遇到这个问题,便原形毕露,即如果工人阶级跻身于中产阶级,同性恋知识分子还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欲望对象吗?伊舍伍德的朋友卡尔告诉他,工人阶级同性恋天生就有一种获得教育的渴望,好让自己跻身中产阶级,到时候他们也会习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趣味。
但当时的伊舍伍德似乎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天真地拒绝相信,难道一个工人阶级男孩受了教育就一定要获得布尔乔亚(bourgeoisie)气息吗?如果他的本性要让他成为一个女王,他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工人阶级式的女王呢?
而历史告诉我们,不染上布尔乔亚气息的工人阶级同性恋无法存在,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同性恋者本身永远无法与自身的阶级身份一刀两断,一旦革命浪潮过去,这个阶级身份所附带的印记会重新降临,那时他们会挥挥衣袖告别革命,与自己的阶级兄弟重新结成同盟。




![[集市好物]闲置破壁机](https://storage.51yun.ca/market-product-photos/6d4a4c18-ab22-40f7-b3d3-0ffd77725c0e.750x100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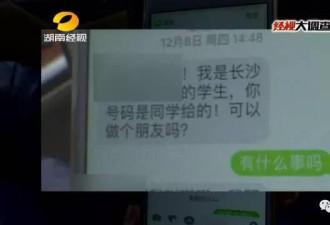



















网友评论